開(kāi)在記憶里的花朵
尤楚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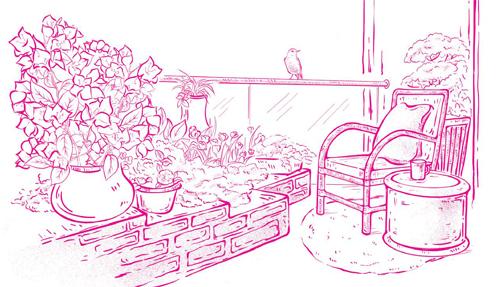
我的生活中也將永存那一幕鮮妍,經(jīng)久不褪,引導(dǎo)我以彼之精神,生己之花朵。
十年前的那個(gè)晚冬,姥爺將那一小株九重葛買(mǎi)回老房子時(shí),它還沒(méi)有我的手臂長(zhǎng)。翠嫩的枝條小而細(xì),迎著風(fēng),顫巍巍的好像下一秒就要被折斷,但它卻硬是撐過(guò)了扎根的第一年,在第二年初秋擠出了幾粒紫紅,不過(guò),比起對(duì)面陽(yáng)臺(tái)的大紅大紫,仍然顯得格外蕭索——那是鄰居前不久剛移栽的一大叢成花,好不熱鬧。
“這花其實(shí)春天種能開(kāi)得最早,就像對(duì)門(mén)那家那樣。”姥爺精心侍弄著新放的九重葛,對(duì)我道:“春天種,枝子一落土就能開(kāi)花。但我不是想它開(kāi)得早,開(kāi)得早,不出幾年就謝了。”他直起身來(lái)為喜攀緣的花蔓搭了個(gè)小支架,好好端詳了一番那仍舊弱嫩的枝干,又看看鄰居家的花團(tuán)錦簇,輕嘆一聲。
“要想讓我們家的花開(kāi)得好,就得秋冬種,慢慢扎根。”
從前我并不了解九重葛經(jīng)歷那些深秋嚴(yán)冬的必要性,只是安安靜靜傾聽(tīng)姥爺所言。但第二年開(kāi)春,怒放的九重葛絕對(duì)在我幼年的認(rèn)知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大盆枝蔓從支架上流淌出粉紅或艷紫的花,似傾玉瓶而灑瓊漿。不同于第一年過(guò)早開(kāi)放的瘦弱樣,它伸展出一片春光爛漫。綠葉結(jié)實(shí)地支撐著碩大的瓣,將其托上天臺(tái)的圍墻,迎風(fēng)而舞,盡顯妖嬈。
鄰居家比我們?cè)缫苼?lái)半年的花卻沒(méi)能頂住這個(gè)冬天,開(kāi)春時(shí)枯死了。
接下來(lái)幾年中,家里事情多了不少。我的足部手術(shù),我們家的移居,新的起點(diǎn)和新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