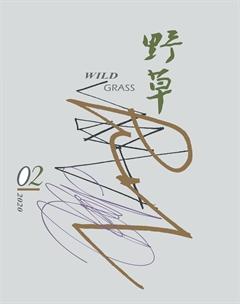“不滿(mǎn)”與“自滿(mǎn)”
王士強(qiáng)
馬敘是一位純粹的詩(shī)人。在詩(shī)歌寫(xiě)作者們忙于“趕場(chǎng)”“出鏡”的時(shí)代,馬敘是自外于這一潮流的,他不混“圈子”、不跑“場(chǎng)子”,幾乎是單槍匹馬、踽踽獨(dú)行地進(jìn)行著他的創(chuàng)作,頗有獨(dú)行俠的風(fēng)范。他的“名氣”并沒(méi)有特別大,也沒(méi)有那么“著名”,不過(guò),他同時(shí)也獲得了更大、更獨(dú)立的個(gè)人空間,他的寫(xiě)作是純粹的、自由的、超功利的。而這些,無(wú)疑是更切近詩(shī)歌創(chuàng)作之本義的,也是純正的創(chuàng)作所應(yīng)該堅(jiān)持的。由此,他的寫(xiě)作也達(dá)到了較高的水準(zhǔn),具有非同一般的格局與境界。
馬敘與生活之間的關(guān)系主要的不是對(duì)抗性的,他更多的是疏離、松弛、自然、無(wú)可無(wú)不可。如他在詩(shī)歌《我就是在湖邊隨便走走》中所寫(xiě):“冬來(lái)了,我獨(dú)自走在鄱陽(yáng)湖邊。/我就是隨便在湖邊走走/——一如我對(duì)生活的平淡態(tài)度。//在湖面開(kāi)闊處,我看到了一只/與我近似狀態(tài)的水鳥(niǎo)。/我感覺(jué)它是在向我問(wèn)安。”這里面似乎有一些消極、頹廢的情緒,但讀到最后,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其實(shí)并不是消極、頹廢,而是超脫、達(dá)觀、自然:“當(dāng)然,只有我明白/它之所以如此平靜,因?yàn)樗宄刂?——令人驚異的事物就藏在明天湖邊的某一處。”這種“平靜”是有內(nèi)容的,它的根基是愛(ài)和期待而非其他,“令人驚異的事物”是重要的,它是一種強(qiáng)大的力量,雖然并未在場(chǎng)卻是一種結(jié)構(gòu)性的存在,這實(shí)際上也是一種更為高遠(yuǎn)、更值得追求的一種存在,它是馬敘詩(shī)歌冷淡、枯瘦的外表之下的熱力之源,他的詩(shī)在冷的外表之下其實(shí)是熱的,是有愛(ài)的,只不過(guò)表達(dá)的方式更為曲折、隱晦而已。馬敘的詩(shī)往往透過(guò)現(xiàn)象看本質(zhì),他長(zhǎng)于做“減法”,《在馬致遠(yuǎn)故里》中便將這種“減法”做到了極致,寫(xiě)在馬致遠(yuǎn)故里所見(jiàn):“刪去一個(gè)元朝/刪去一個(gè)滄州/刪去一個(gè)東光/刪去一個(gè)于橋/刪去一個(gè)馬祠堂村//剩下一座/上鎖的馬氏祠堂/這一刻,祠堂也在被刪去”,而在所有這些都刪去之后,“剩下一個(gè)/馬致遠(yuǎn)//唉,孤孤單單的馬致遠(yuǎn)”。這樣的不停“刪去”的過(guò)程相當(dāng)于去蕪存菁、去偽存真,從另外的角度看其實(shí)也是在做加法,凸顯出了馬致遠(yuǎn)的價(jià)值和重要性。實(shí)際上,詩(shī)中所羅列的一個(gè)個(gè)被“刪去”的都是歷史中的過(guò)眼煙云,一切都轉(zhuǎn)瞬即逝風(fēng)流云散了,留下的是真正有價(jià)值、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所以,詩(shī)中最后所喟嘆的“孤孤單單的馬致遠(yuǎn)”實(shí)際上又并不“孤單”,因?yàn)樗┰搅藲v史的迷霧和時(shí)空,而與無(wú)限的讀者、與“無(wú)限的少數(shù)人”進(jìn)行對(duì)話、交流,活在人們的心里,獲得了真正長(zhǎng)久的生命。這樣的詩(shī)在馬敘的作品中頗具典型性,他往往以這樣冷色調(diào)的敘述傳達(dá)他的熱愛(ài)、堅(jiān)持與立場(chǎng)。
馬敘有著自己的態(tài)度立場(chǎng),有著內(nèi)在的鋒芒,他對(duì)世界有著厭棄與反對(duì),他的內(nèi)心也充滿(mǎn)著矛盾、沮喪、孤獨(dú)、挫敗,包含著明顯的現(xiàn)代性體驗(yàn),他并不是一個(gè)逃避式、后退式的復(fù)古主義者、古典主義者,而是立足當(dāng)代、面對(duì)當(dāng)代問(wèn)題的寫(xiě)作者。《無(wú)事,就反對(duì)春天》中,他寫(xiě)了諸多種的“反對(duì)”:“反對(duì)春天,明確點(diǎn),不含糊/首先反對(duì)自己/吃飽喝足地反對(duì)/旗幟鮮明地反對(duì)/漠然,無(wú)感,不走動(dòng),不歡喜”,詩(shī)中繼續(xù)寫(xiě),“接著是板凳反對(duì)椅子/空氣反對(duì)房屋/或再?gòu)拿枘∫粔K石頭開(kāi)始/——它巨大、堅(jiān)硬,頑固、無(wú)知/它輕易反對(duì)高山流水//還有一幫狂野的孩子/齊刷刷地反對(duì)大人/世界才看到他們/就已經(jīng)被徹底反對(duì)”,有不同事物之間的互相反對(duì),有后輩對(duì)長(zhǎng)輩的反對(duì)等,詩(shī)的最后:
在這些日子
無(wú)事,就反對(duì)春天吧
直至反對(duì)整個(gè)世界
直至春天反對(duì)春天
直至世界反對(duì)世界
這里面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寫(xiě)出了事物內(nèi)部的自我“反對(duì)”,“春天反對(duì)春天”“世界反對(duì)世界”,自然,“我”也是反對(duì)“我”的。這樣的反對(duì)并不是一種簡(jiǎn)單的否定性向度,而更多的是道出了事物的常態(tài)和本質(zhì),這首詩(shī)以形象的方式呈示了一種極具普遍性和概括性的狀態(tài),也揭示了詩(shī)人馬敘與世界關(guān)系的一種基本狀態(tài)。這樣的狀態(tài)既是向外的,也是向內(nèi)的、指向自身的,他的詩(shī)中有著對(duì)于自我內(nèi)心的直視,比如他說(shuō)“如果在雨天/我就是一桶濕垃圾/被沮喪、欲望、善惡/攪和在一起//無(wú)序,混亂,分也分不開(kāi)”(《你帶來(lái)了剩余的一切》),是對(duì)個(gè)體內(nèi)心之幽深、混沌、窘困狀態(tài)的袒呈。在另外一首詩(shī)中,他站在數(shù)百萬(wàn)人口城市的街頭,卻如入荒野,如入無(wú)人之境,此時(shí),“只有一個(gè)人/——一個(gè)/自私、浪蕩、無(wú)知、孤獨(dú)的我”(《獨(dú)自走在保定大街上》),這同樣是對(duì)自我的反對(duì),寫(xiě)出了個(gè)體內(nèi)部、不為人知甚至頗為不堪的另一面。這是對(duì)自我的反思與逼視,呈現(xiàn)的是更為復(fù)雜、曖昧、具有異質(zhì)性卻又包容含混的現(xiàn)代主體,他是反烏托邦、反理想主義的,卻又是真正立足于現(xiàn)實(shí)、具有現(xiàn)代性,同時(shí)也深具理想性的。正是由于這種反烏托邦而又具有理想主義特征的書(shū)寫(xiě),使得他的作品能夠直面現(xiàn)實(shí)的污濁與破敗,直面人生的庸常與不堪,卻又不失“光”的照拂和慰藉。馬敘的用詞可謂大膽、葷素不忌,比如“朝霞如狗屎,就要爛在天邊、山上”(《致朝霞》),“這么好的天氣。路上的那個(gè)/走肉/趕著另外的一個(gè)走肉”(《好天氣》),“觀花是一個(gè)小概率事件/某一天,連性生活都沒(méi)有了時(shí)/去觀一次花”“多日后的一天,醒來(lái)/晨勃/隱約聞到桂花的香味自窗口悄然而至”(《有一天去觀桂花》),“他坐著,大腹便便,飽餐一頓/——吃粗話,吃性欲,吃藝術(shù),吃虛偽,吃歡笑,吃饑餓。//他用這些照亮肝、心、胰腺、肺、大腸、陽(yáng)具。/他有時(shí)拉出語(yǔ)言,涂在大地上。”其中的一些用詞和表述幾乎讓人瞠目結(jié)舌。不過(guò),如果對(duì)某些“敏感詞語(yǔ)”脫敏,以平常心視之,而不以某種狹窄的詩(shī)意標(biāo)準(zhǔn)來(lái)看待的話,又會(huì)發(fā)現(xiàn)其中除了表達(dá)的別致之外,確有深意存焉,如此的書(shū)寫(xiě)擴(kuò)展和豐富著詩(shī)意的邊界和內(nèi)涵。這里面包含了馬敘的獨(dú)特的詩(shī)學(xué),同時(shí)與老莊的“道在屎溺”有著共通之處,更是深具現(xiàn)代性特征的。
最能正面體現(xiàn)馬敘價(jià)值立場(chǎng)和美學(xué)觀念的是《紀(jì)念》,這首詩(shī)是寫(xiě)給被譽(yù)為“俄羅斯的良心”著名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其中寫(xiě)了索爾仁尼琴所處的時(shí)代,也寫(xiě)了作者自己的時(shí)代和作者自己。其時(shí),索爾仁尼琴去世已經(jīng)有一段時(shí)間,“這個(gè)時(shí)候,索爾仁尼琴/我來(lái)想起你,如一份世俗早點(diǎn)懷念龐大的暗夜。//我盡量不想身邊的人,/他們?cè)?jīng)在我的文字里出現(xiàn)過(guò)消失過(guò)。/現(xiàn)在,他們?cè)谠俅蜗А?這樣,我可以離你更近一些。”這是“我”向一個(gè)偉大靈魂的致敬和靠近,也是兩個(gè)靈魂之間的一次深度交流。索爾仁尼琴身上獨(dú)立不倚、剛正不阿的品格,以及因受難與不屈而具有的道義力量等,都是作者所心儀和仰視的,故而,他說(shu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