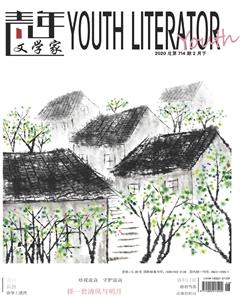憶小城
魏欣琦
傍晚濟南的天突然變了,夜風裝扮好登上劇場,呼嘯而唱。他甩起巨大的斗篷,卷起一大把一大把的葉子,在地面打著旋兒。我坐于圖書館一角,突然很想念我的小城,那個我度過懵懂與年少的小城。
小時候總是對周遭的事沒有概念,但小城的名字在爸媽強力要求記住下印在我的腦海里。兒時的小城,意味著校門口賣糖的小賣鋪,嚼著糖果回家的路,樓下與小伙伴玩耍胡鬧的小花園……步之所及的那點小小天地。歲數太小,沒有離家,我總不會閑來沒事便想它。但從那時起,甚至更早,都成為我日后瘋狂的思念小城的養料。小城,我記得它所有的模樣。
白天的小城最有城市的樣子,各色各樣的店鋪裝扮著它,從頭到尾。有些店鋪常年放著最流行的音樂,一年中換了一首又一首。我最喜歡站在路的一面,看行人穿過馬路,再各自散開。紅紅綠綠的衣服,像煙花,又像被獅子驚擾四散開的動物群。我和朋友有一家常去的米線店,店主總會在下午陪他的兒子寫作業。小朋友第一次問我問題的時候,我總是記得很清楚,因為那天店主免了我們的飲料錢。那天下午,我的心也像是被淋了一杯冰鎮橘子汽水,碳酸氣泡破裂后在小小心房跳躍著快樂。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晚上十點過后的小城是旁人不輕易見到的,像其他城市一樣,會有忽明忽滅的霓虹燈光。但我總覺得那燈光泛了黃,蒙上早時候放映電影的白色幕布,一幀一幀播放著時間的掠影。下晚自習那陣最為喧鬧,到處充滿著呼嘯而過的青澀聲音。喧囂過后,便是更荒涼的荒涼。燈光投射下成片的黑影子,路上偶爾飄過幾張發剩的傳單。如果你住在靠近鬧街的房子里,午夜夢回,會聽到醉漢的囈語,他們甚至會親切地問候你的祖宗。
我一直固執地認為,城市小有小的好處,吃東西有常去的幾家店,玩樂有混熟的地點,甚至于有些陰森的夜,你都覺得別有一番風味。
在寫下這寫文字的前幾天,我在食堂吃了排骨,感覺那是人間美味。很奇怪,在家時,媽媽也經常給我做排骨,我總是皺著眉頭,充滿抱怨。回去在朋友圈夸贊食堂排骨的美味,姐姐給我評論“你在家怎么不愛吃”,我的心仿佛路上被踢起的小石子,猛地翻滾幾下,激起揚塵。因為之前常吃媽媽做的排骨,所以習慣了吧。人就是這樣,對于吃不到嘴的葡萄,也可能覺得分外的甜。也許我不是想念排骨,而是想念做排骨的人。
常有人問起我的家鄉,我回答后總有人大悟:“我知道那里!聊齋故里!”我對這個稱呼總顯得生疏,因為蒲松齡和他的聊齋其實跟我沒多大干系,我雖也以此為榮,但“聊齋故里”并不是我第一印象的小城。我的小城總是有我最親愛的人,是我曾經去過待過留下過記憶的地方,干凈敞亮也好,嘈雜臟亂也罷。是呀,我所謂的想家,并不是想念小城的骨架,而是我記憶中的溫與冷,暖與寒,一切將骨架上添上血肉的東西。我突然明白,一個地方的好壞與否并不是看表面,而是看人賦予了它多少意義。
我終究要離家。現在還記得離開時最后一次朝小城遠望,它站在原地,風霜已浸透臉龐。如今我離開小城不算久,也不算遠,但時常想念。總會在夢中搭上回鄉的火車,伴著綿延的汽笛,一百里,兩百里,漸漸歸去。
傍晚濟南的天突然變了,夜風裝扮好登上劇場,呼嘯而唱。我總覺得這風可以爬過山去到我的小城,順便將我的思念帶去。手機突然震動,媽媽微信給我發了新消息:“食堂沒有排骨?周六出去吃一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