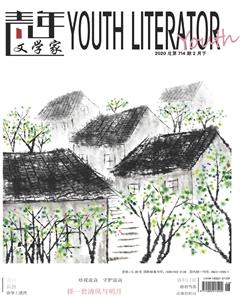地方理論視域下的《還鄉(xiāng)》解讀
趙新蘭
摘? 要:托馬斯·哈代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位偉大的作家,《還鄉(xiāng)》是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文章運用勞倫斯·布伊爾的地方理論探討了人類文明與自然在“地方”上的對立,以及小說中男女主人公對“地方”態(tài)度的對立。鑒于此,哈代呼吁人類改變現(xiàn)有的狀態(tài),與自然和諧相處,并希望人們轉變對自然的態(tài)度,能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實現(xiàn)人類文明與自然在“地方”上的統(tǒng)一。
關鍵詞:托馬斯·哈代;《還鄉(xiāng)》;地方理論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06--02
一、引言
托馬斯·哈代(1840-1928)是維多利亞時代一位偉大且多產(chǎn)的作家。《還鄉(xiāng)》是他著名的威塞克斯小說系列中的其中一本,也是一本典型的“性格與環(huán)境”小說。《還鄉(xiāng)》以埃格頓荒原為背景,描述了克林和游苔莎等五位青年男女的不同命運,反映出在19世紀工業(yè)文明的侵蝕下的鄉(xiāng)村及鄉(xiāng)村生活的變化。本文運用勞倫斯·布伊爾的地方理論分析這本小說,揭示人與自然在地方上的對立,以及人與人對“地方”態(tài)度的對立,并提出如何能實現(xiàn)人與自然,人與人在地方上的統(tǒng)一。
地方是地理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其最基本的含義指由人或物占據(jù)的部分地理空間。約翰·阿格紐將地方簡化成三種主要含義:“一、作地方講—是地球表面的某個地點。二、作地方意識講—是人們對地方的主觀感受,包括地方在個人和團體中的作用。三、作場所講—是人們的日常活動和交往的背景和場所。”[1]
然而,在環(huán)境批評領域,地方一直處于被忽略的地位,直到勞倫斯·布伊爾提出地方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環(huán)境批評的三大理論基礎之一。在《環(huán)境想象:梭羅、自然寫作和美國文化的構成》一書中,布伊爾提出地方“應當被重視并應當成為環(huán)境想象的中心理論之一”[2]。地方是一個很難界定但富有價值含義的概念,小到一個點,大到整個地球,都可以看作地方,如沙發(fā)上的某個小點、房子、小鎮(zhèn)、城市甚至整個地球。地方“同時具有三種含義:環(huán)境的物質性,社會觀念或建構,個體的影響或依附”[3]。
二、人類文明與自然在“地方”上的對立
小說《還鄉(xiāng)》里有兩個非常明顯的地方,一個是象征著自然的埃格頓荒原,另一個就是象征著人類文明的巴黎。
埃格頓荒原“能以一種奇特的寬厚親善面目,重上愛它的人心頭。劃過繁茂的平川坦野,笑容可掬, [……]暮色和埃格頓荒原的景色相結合,演變出一種不怒而威,不虛張聲勢而感人深遠的局面”[4](p4)。埃格頓荒原的偉大榮光要在黃昏中才能發(fā)現(xiàn)。“沒有在這個時辰到過荒原的人,就不能說了解荒原”[5](p3)。荒原四周的山巒都有其和藹可親的一面。埃格頓荒原就是自然的代表,正如約翰·派克在《怎樣研究托馬斯哈代的小說》中說道:“你發(fā)現(xiàn)的第一件事就是埃格頓荒原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自然。”[6]
而巴黎,“時尚界的中心和旋渦”[7](p121),在那里有金燦燦的買賣,奢侈的生活,還有杜伊勒利宮、盧浮宮、凡爾賽宮、楓丹白露、圣·克盧等,這些都是游苔莎向往的地方。小說中對巴黎的描寫都是通過人物的對話展示出來的。在埃格頓荒原的居民心里,巴黎是一個“迷人的地方。豪華的商店櫥窗,熱鬧的鼓樂聲”[8](p191),與埃格頓荒原形成鮮明的對比,這是個典型的以人類為中心的工業(yè)文明城市。
哈代對這兩個地方的描述不難看出這兩個地方實質上象征著人類與自然。小說中在描寫埃格頓荒原時說到“文明是它的死敵”[9](p6),這能讓人感覺到自然與人類的強烈對立。即使“一個人穿著顏色和樣式都摩登的服裝,跑到荒原,總顯得有些格格不入”[10](p6)。這種鮮明的沖突躍然紙上。工業(yè)文明的迅速擴張使得埃格頓荒原越發(fā)的和以人類為中心的城市,如巴黎,對立起來。
三、人與人對“地方”態(tài)度的對立
小說里男女主人公在對待埃格頓荒原和巴黎有著不同的態(tài)度。克林·約布賴特,《還鄉(xiāng)》中的男主人公,從小在埃格頓荒原長大,心中一直都對其熱愛不已。“他就是荒原的作品。他第一次張開眼睛就看到荒原了,最初的記憶和荒原的模樣渾然一體,連對生活的判斷都帶荒原的顏色。[……]他心目中的社會無非就是一批出沒荒原的人罷了。”[11](p193-194)。長大后,他在巴黎的一家大型鉆石商鋪當經(jīng)理, 生活十分富足。但是,趁著回鄉(xiāng)之際,他決定不再去巴黎。對他而言,巴黎是一個商業(yè)城市,他從事的工作是最無聊、最虛榮的女性化工作,他討厭這份工作。在他心底,埃格頓荒原才是他真正的靈魂歸宿。最終,他回到埃格頓荒原,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希望在這地方建一所學校,做一些對家鄉(xiāng)有意義的事情,造福桑梓。他的決定和思想都很有超前性。“對鄉(xiāng)村世界的人強調文化生活有可能領先于奢侈生活,當然是說真話,不過,這種嘗試可就打亂了人們一直習以為常的事理次序了。”[12](p193)
而女主人公游苔莎卻一直渴望能離開這個令她討厭的地方-埃格頓荒原。“身居荒原卻不研究荒原的意義,[……]荒原微妙的美,游苔莎并未領略,[……],荒原的環(huán)境,[……],叫桀驁不馴的女人憂郁不合群。”[13](p76)在她看來,埃格頓荒原就是她的冥土。她出生于海濱勝地蓓蕾嘴,即使現(xiàn)在和外公住在埃格頓荒原,她的腦子里仍然會有各種海濱廣場的浪漫回憶;而她的身上也可以找到那種不屬于荒原的尊貴的儀態(tài)。她住在荒原,感覺自己像被流放一樣,她渴望離開這里。與克林的婚姻,也有希望能和克林一起回到巴黎的企圖在里面,但是克林要留在埃格頓荒原生活的決定讓她對克林非常失望。最后,游苔莎決定和她的舊情人懷爾狄夫離開這里。一個暴風雨的晚上,他們兩人雙雙淹死在沙德洼水堰下面的一個圓形大潭里。游苔莎畢生都在追尋回到“文明”社會,回到她覺得最迷人的城市-巴黎,但是最終卻失敗了。
克林和游苔莎兩人對待埃格頓荒原和巴黎的態(tài)度是截然不同的,雙方都渴望“還鄉(xiāng)”,對待“地方”的不同態(tài)度,就是他們的對立所在,也注定了他們的婚姻悲劇。克林的回歸象征著他從奢侈的生活回歸到真正的鄉(xiāng)村生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意味著他從割斷人與自然的工業(yè)化生活回歸到重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生活。而游苔莎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違背自然就會受到懲罰。她對埃格頓荒原充滿了恨意,一直想割斷與自然的聯(lián)系,想回到人類文明的中心城市生活。然而,她最終也沒有回去。D.H.勞倫斯認為《還鄉(xiāng)》一書中主要控制因素在于埃格頓荒原[14],這種自然的力量。“埃格頓荒原保持了一千年的不變,[……],而埃格頓荒原象征的自然力量似乎在觀察和默默地注視著人類命運的變遷”[15]。由此可見,還鄉(xiāng)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從字面上看,克林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游苔莎想回到她的家鄉(xiāng);另一方面,從隱含意義看,這意味著從文明回到自然,重建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還鄉(xiāng)》中,這個關鍵詞‘鄉(xiāng)不僅僅是描寫克林,也是[……]對游苔莎簡潔而諷刺的描述。此外,‘鄉(xiāng)也標志著事件發(fā)生的地方的重大意義: 埃格頓荒原”[16]。
四、尊重自然,實現(xiàn)人與自然在“地方”上的統(tǒng)一
托馬斯·哈代是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代表人物。這個時期,英國進入了工業(yè)社會。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也越來越趨于緊張。在哈代看來,人類要征服自然是枉然的,他很懷疑工業(yè)革命的成果本身。“滄海易容,田野變遷,江河、村落、人物,全有變化,唯有埃格頓荒原一成不變”[17](p6),要想讓人類和自然和諧相處,那就是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實現(xiàn)人與自然在“地方”上的統(tǒng)一。
埃格頓荒原在哈代的眼中,是一塊“和人性完全融洽的地方”[18](p5),就像小說中的克林一樣,他更愿意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在鄉(xiāng)下建學校,甚至想對埃格頓荒原的人們宣講“可以不必經(jīng)過發(fā)家致富的過程,便能一步到達心澄神明的全知境界”[19](p167)。雖然埃格頓荒原的居民們認為巴黎是一個富裕奢侈的地方,但是他們卻仍然熱愛自己腳下的這片荒原。
工業(yè)革命的迅速發(fā)展,讓城市越來越工業(yè)化,這潮流也影響到了英國的鄉(xiāng)村。在工業(yè)文明迅速擴張的時候,自然的破壞是無法避免的,即使是埃格頓荒原,也開始受到影響。小說中的紅土販,是古老傳統(tǒng)的代表,但是他最后也放棄了販賣紅土。但哈代一直堅信向自然回歸的那一天近在咫尺,希望能順應自然規(guī)律,實現(xiàn)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五、小結
托馬斯·哈代的《還鄉(xiāng)》雖然是講了五位青年男女的不同命運,但是在描述的時候卻能反映很多的問題。“地方”所象征的人類文明與自然的對立,人與人對“地方”的態(tài)度造成的對立,甚至是悲劇,都反映在這本書里面。
在哈代看來,要想實現(xiàn)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相處,就需要尊重自然,認同自然,實現(xiàn)地方的統(tǒng)一。克林的回歸就展示了人與自然的共存,而游苔莎的悲劇意味著違反自然,認為人類是世界的中心,就會遭到自然的懲罰。只有對“地方”的認同,才能真正地的從意識上及行動上實現(xiàn)地方的統(tǒng)一。
參考文獻:
[1]薩拉·L·霍洛韋,斯蒂芬·P·賴斯,吉爾·瓦倫丁編. 當代地理學要義—概念、思維與方法 [M].黃潤華,孫穎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8: 134.
[2]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M].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2.
[3]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Imagination [M].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63.
[4][5][7][8][9][10][11][12][13][17][18][19]Thomas Hardy,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M]. London: Penguin English Library, 2012.
[6]John Peck, How to Study a Thomas Hardy Novel [M].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7: 22.
[14]Scott Russell Sanders, Speaking a Word for Nature [A]. Ed.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Fromn. The Ecocriticism Readers [C].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182.
[15]Chen Jia,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3[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431.
[16]Jakob Lothe, "Variants on genre: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TheHand of Ethelberta"[A]. Ed. Dale Kram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Hardy [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3: 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