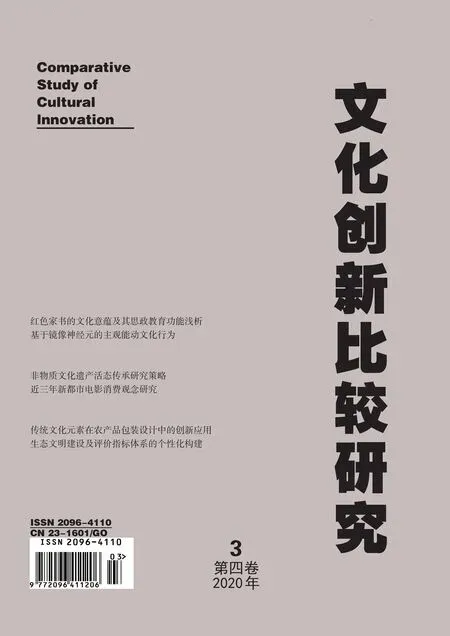中華傳統嬰幼兒照護理念的時代啟示
湯二子
(南京審計大學經濟學院,江蘇南京 211815)
1 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高瞻遠矚地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要求“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人的身體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嬰幼兒時期的身體健康程度。人在嬰幼兒時期所得到的照護及健康保障服務完全不取決于自身,而是決定于監護人的意愿與能力及社會所能提供的服務。這種看似帶有某些矛盾意蘊的關系——在夯實身體健康基礎最重要的嬰幼兒時期,自身卻無法做出任何有效決策——意味著社會應該充分調動各種資源,確保嬰幼兒所接受的照護服務有利于維持長期身體健康的宗旨。李克強總理在2019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以非常務實的態度提出諸如“加快兒童藥物研發”、“抓好傳染病、地方病、青少年近視防治”、“加強婦幼保健服務”等涉及嬰幼兒的照護與社會醫療服務等內容的國家政策取向。2019年5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專門下發了《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9)15號)文件,強調嬰幼兒照護服務屬于生命全周期服務管理的重要內容,要求充分調動社會力量,滿足人民群眾對嬰幼兒照護服務的需求,促進嬰幼兒健康成長。
相對于古代中國來說,新時代中國的經濟狀況與社會環境處在完全不同的位置,但是作為個體的人的成長軌跡并未因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而出現變化。無論古今中外,人都會處在“妊娠中-嬰幼兒-兒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這一人生軌跡中,從而都會有嬰幼兒照護這一環節。因此,中國古代所形成的有關嬰幼兒照護方面的思想理念,如果在新時代依然可以發揮積極的借鑒作用,就應該讓其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充分發揮余熱。同時,文化基因的繼承性決定了民眾行為的延續性,中國古代所形成的某些照護嬰幼兒方面的消極觀念也要引起警示,因為其仍有在當代出現的可能性。
為了理解中華傳統嬰幼兒照護理念,應該從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中去探尋、梳理與整合。為了使其對新時代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提供借鑒或警示意義,必須立足于新時代中國的實際情況。
2 傳統理念
在古代中國,統治者希望擁有更多人口以增強國家力量,據此來應對戰亂與外敵入侵的風險,這從《戰國策》等傳統著作的大量描述中就可知曉。“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四十二章》),人口繁衍如同萬物一樣,需要陰陽結合才行。嬰幼兒照護屬于生命全周期中的內容,而懷孕與妊娠過程是否順利卻是嬰幼兒身體健康與否以及能否容易照護的基礎。中醫學發現女子14周歲(二七)就可懷孕,即“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沖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而男子16周歲(二八)就可生育,即“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陰陽和,故能有子”(《黃帝內經?上古天真論篇》)。在人口激勵下,古代統治者從法律上規定墮胎要受到相當嚴重的刑罰,如“墮胎者,準律未成形像杖一百,墮胎者徒三年”(《洗冤集錄?小兒尸并胞胎》)。某些社會福利政策如“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管子?入國》),對于重新組合殘破家庭和繁衍更多人口也很有意義。缺乏必要的避孕措施以及禁止墮胎等社會政策能為提高人口增長發揮積極作用,但古代贊許甚至要求早婚早育卻對嬰幼兒照護產生不利影響。現代統計醫學發現女性在24-29歲之間生育有利于嬰兒健康[1],同時初次生育年齡過早比如在20歲之前會增加母親老年時的死亡風險[2]。嬰幼兒因為早育使其體質相對較差,再加上落后的醫療條件,使得古代中國嬰幼兒的死亡率處在很高位置。男女結合成家是古代大事,如“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孟子?滕文公下》),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孟子?離婁上》)決策機制下,個體家庭會將生育子女特別是兒子當作女性婚后的首要責任,因為“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列子?天瑞》)。過高的夭折風險使得家庭以多生育子女來規避,降低了原本就很稀缺的可用于照護嬰幼兒的家庭資源,進一步增加嬰幼兒死亡風險,更加刺激家庭多生育子女,步入惡性循環之中。“君子以飲食宴樂”(《周易?需?象》)以及“多財,民好食”(《墨子?號令》),嬰幼兒必要的物質生活資料保障是古代照護服務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在古代嬰幼兒照護中,母親發揮的角色是至關重要的。古代慈母形象通過詩句“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游子吟》)可貼切地領悟出來。母親為了養育子女,承擔了非常繁重的家庭勞動責任,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詩經?國風?邶風?凱風》)所描寫的一位母親為了七個子女含辛茹苦勞作的畫面。然而,古代也有些母親并不十分照護自己的孩子,比如后稷的母親姜嫄出于好奇踩在巨人腳印上而懷孕,她不希望孩子出生,但最后孩子還是生了下來。姜嫄把這個孩子“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接著送到樹林里,伐木人給孩子照護,再扔到寒冰之上,飛鳥為這個孩子曲翼遮掩,“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列女傳?母儀傳?棄母姜嫄》)。再比如春秋時期的武姜在生鄭莊公的時候受到驚嚇,“遂惡之”(《左傳?隱公元年》)。嬰幼兒幾乎完全不具備生活自理能力,如果監護人特別是母親不喜愛這個孩子,那么該孩子所受到的照護服務將是極為惡劣的。人都趨利避害,即“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無擇也”(《商君書?君臣第二十三》),所以社會要從激勵機制與道德層面形成慈愛氛圍,以求有利于嬰幼兒的照護發展,如“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所言,從道德上要求應對幼者慈愛是禮的基本要求之一。孟子呼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希望統治者致力于形成尊重老人與愛護孩子的社會整體氛圍。在慈愛的道德品質激勵下,人類會在遭受危險之時優先考慮照護包括嬰幼兒在內的老弱病殘,即“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強武猛衛其外”(《潛夫論?實邊第二十四》)。
古代中國始終將人格與道德方面的培養作為教育宗旨,“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篇第十七》),人性原本相近而人生軌跡卻相去甚遠。盡管“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于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質也”(《人物志?九征第一》),古代教育家還是認為人們在教育等日常行為上的差異是其人生道路不同的主要原因。“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列子?仲尼》),古代照護與養育子女的最終回報就是為己養老。照護嬰幼兒的成本以及較高的夭折風險,使得古代家庭對于嬰幼兒成長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期盼他們能夠成長為社會所需要的人并能按照道義要求為自己盡到養老義務。在“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新書?禮》)之中,“孝”與“敬”都是對身份較為幼小的人來要求的,使年齡較長者如父母或兄長對嬰幼兒時期的子女或弟弟提出道義要求以培養其道德品質。從“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荀子?非相》)看出嬰幼兒長大后不肯侍奉長者被當作是一大不祥之事。學習是嬰幼兒修煉道德的主要方式,如“人生十年曰幼,學”(《禮記?曲禮上第一》)。其實,古代帝王之家在嬰幼兒出生之前的妊娠階段就已開始給予教育即所謂的胎教,要求妃子懷孕三個月之后住在專門的房間中,不該看的東西不準去看,胡言亂語的話不要去聽,所聽音樂與日常飲食都有嚴格要求,即“圣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顏氏家訓?教子第二》)。“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者奉長者之手”(《禮記?曲禮上第一》),要求大人在教育幼子時應該要有正確的示范,不允許欺騙幼子;幼子與孩童不要穿裘皮衣服與裙裳,站立時姿勢應該端正,不能歪頭側耳聽人說話;長者拉著幼童行走時,幼童應該要雙手捧著大人的手。幼童自小接受嚴格的教育約束,不能讓其放縱,對未來成長有極大好處。壞的習慣一旦養成,再去對其管制約束,即使用鞭子把他抽打死,也難以用父母的威信改變孩子的行為,最終這些孩子成為道德敗壞之人,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為敗德”(《顏氏家訓?教子第二》)。古代圣賢反對父母過分溺愛子女,認為溺愛不是優質照護嬰幼兒,反而會促使嬰幼兒養成壞習慣而影響未來的成長與發展。在物質資料非常匱乏的年代,溺愛嬰幼兒的父母可能會通過大量哺乳人奶以求照護好嬰幼兒,“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癇”(《潛夫論?忠貴第十一》),過量的哺乳卻會引起嬰幼兒患癲癇病的風險。
3 時代啟示
古代中國所形成的嬰幼兒照護方面的一些理念,對新時代來說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比如自小甚至從胎兒開始就要重視嬰幼兒教育,切記不能過分溺愛嬰幼兒等。當然,也有一些理念對新時代來說沒有什么參考價值,比如通過早育來增加人口數量,這既不符合當代的人口戰略,同時早育所出生的嬰幼兒體質也較差,不利于嬰幼兒的照護服務。一些理念在新時代的嬰幼兒照護中必須予以徹底掃除,比如家庭將更多資源集中于偏愛的孩子身上,從而稀釋了其他嬰幼兒所應得到的照護資源等,從古代就已形成的重男輕女取向[3]是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古代在嬰幼兒照護方面想更多地發揮社會力量來參與,可能會受到一些倫理教條的約束,比如單身母親所撫養的嬰幼兒,原本想幫助其照護的人可能會因為一些道德壓力而放棄,比如“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禮記?坊記第三十》),這些教條也應引起警示。
在當代中國,物質資源越來越豐富,嬰幼兒所得到的照護服務質量遠遠超過古代,首要表現在嬰幼兒的死亡率上。把2016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樣本數據所提供的嬰幼兒死亡率信息[4]整合并繪制在表1中。盡管“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列子?力命》),但不同類別嬰幼兒死亡率的差異還是能夠反映出一些社會狀況的,其中最明顯一條就是鄉村嬰幼兒死亡率相對高于城市與鎮。如果可以相信更優質的嬰幼兒照護能夠帶來更加健康的嬰幼兒體質及其所伴隨的更低嬰幼兒死亡率的話,那么表1就能從側面反映出當代嬰幼兒照護方面的資源分布并不均衡,鄉村應該要低于城鎮,這是新時代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所應重點解決的問題。

表1 中國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3歲以下嬰幼兒死亡率(‰)
嬰幼兒自身對其所能得到的照護服務,幾乎不存在任何辯護與發聲的力量,這需要社會形成良好的照護嬰幼兒的氛圍。政府部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充分調動社會各種資源,協助個體家庭對嬰幼兒提供更加優質的照護服務,這有利于健康中國戰略目標的實現。中華傳統嬰幼兒照護理念強調了優質照護服務并不意味著過分溺愛嬰幼兒,對嬰幼兒必要的教育與行為約束同樣是現代照護服務的組成部分。
4 結論
從中華傳統文化典籍中梳理出有關嬰幼兒照護方面的傳統理念,其中的積極部分可對新時代嬰幼兒照護服務的發展提供借鑒,其中的消極理念可為新時代嬰幼兒照護服務的發展提供警示,以求徹底掃除自古就已形成的阻礙嬰幼兒健康發展的藩籬,讓嬰幼兒得到優質可靠的照護服務,使其在生命全周期中的身體健康以及道德素養能有一個良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