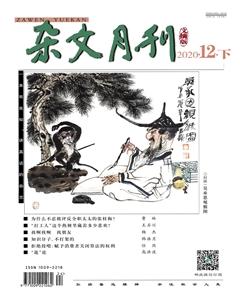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2020-04-18 07:31:31劉曰建
雜文月刊(選刊版) 2020年12期
劉曰建
《雜文月刊》2020年10月下《輿論場何時變得如此刻薄了?》一文問得好!專門學醫的醫學院學生臨危救人,被指責沒有行醫資格證,“刻薄”到極致,更可惡的是竟有6.1萬的點贊。“刻薄”者占據道德制高點,不顧他人處于性命攸關的時刻,而是單純祭起行醫資格證的“大旗”,很能迷惑人,6.1萬點贊者,不能說他們沒腦子,起碼沒用腦子。如果臨危救人必須行醫資格證,就只能聽律師的話,老人跌倒,路人病倒,你只需打兩個電話110、120,他們很快就能趕到,見死不救卻“無懈可擊”。
輿論場“刻薄”的危害是他不做好事,對別人做好事卻求全責備,敗壞社會扶危濟困、見義勇為的良好風氣。輿論場“刻薄”不是新事物,百年前的1920年,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國務總理的熊希齡,不滿政治環境,辭任歸隱,捐出全部家私,在北京創建香山慈幼院,庇佑了孤貧兒童,收養孤兒超過6000名。他剖白初心:“我在北京修了幾條工賑的馬路,約有三百多里。有一處系與外國慈善家合辦的,修好了交與地方官去接管。那時天津的報紙,忽然謂我賣路與外人。你想社會事還能辦嗎?所以我很悲觀。我只縮小范圍,辦我的慈幼院。”佐證“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