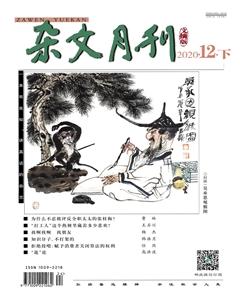街邊的小報亭
陳中奇
樓下十字路口邊有一個小報亭,因為經常路過,所以還記得起。
街邊的小報亭很小,大致只有容一個人在里面轉身、外能存放點雜物的空間。沒有留意它外形具體是什么樣子,好像有些是郵筒一樣的圓筒型,有些是四四方方箱柜型,頂部蓋著一個蘑菇頂,遮風擋雨,顯得有些簡陋。齊腰開個窗,架個小窗臺,上面擺些雜七雜八的書籍雜志,窗框邊靠著一個豎起的小木板格子,飲料只有幾種,一般就放在旁邊加擺的泡沫箱子里。有些勤快的攤主,會順帶賣早餐,打包好的豆漿、包子,數量有限。
小報亭看上去有些孤零零,幾乎被人無視,偶爾有路過的人順便買個打火機,或者一瓶水之類的。
昨天去吃酸菜魚,路過一家小報亭,我見窗臺角上一溜地擺著《人民文學》《十月》《當代》幾本雜志。女攤主聽說要買,趕緊用抹布拭凈浮塵,遞了過來。我一時興起,便各樣買了一本。女攤主還優惠了一塊錢,說兩三個月每樣才能賣一兩本,有點不敢進貨,今天碰到有人買,她都喜形于色了。
聽著這話接過書來的那一刻,我的心里不免灰了一下。回來,躺在床上翻書,真是一件少有的愜意之事,比吃一頓酸菜魚酸爽多了。其實這種層級的期刊,好多文章寫得真是用心,寫得真是刻骨的好,只是認真讀的人太少。晚上臨睡前再次翻開,不知不覺看到凌晨兩三點,《十月》上有一篇《飛發》差不多讀完了。
也許只有我這種“老土”的人還記得買一兩本文學雜志作為消遣,反正買書的時候,我幾乎從來沒碰到身邊顧客有感興趣的。所以經常也被老婆“罵”,說在城市里生活了幾十年,還是融入不進城市生活,還是一身的“土味”,以為自己是個“小文青”。我想了一想,不知道錯在哪里,罵因何在。
與圖書館的藏書相比,街邊的期刊如新鮮上桌的熱菜,曾經,我還真專門去過小報亭買期刊,仿佛生活中的一種儀式感,不過都已經間隔經年了。
生活總是這樣,留一點點小愛好,不太深也不淺的樣子,不管別人是否喜歡,自得其樂就好。
離蕭天薦自《遼沈晚報》2020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