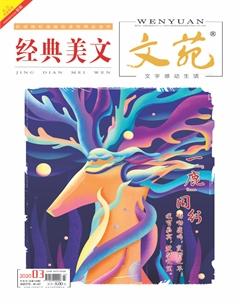注意文章中的詩意
馬蒞,中學語文高級教師、黑龍江省“十五”期間教育科研先進個人。其科研成果兩次獲中國教育協會和中央教育研究所“全國中小學思想道德教育優秀科研成果展覽”一等獎。曾在《人民日報》《黑龍江日報》《中國少年報》《教師報》《教育時報》等刊發表散文60余篇,著有散文集《石頭有語》。
詩意是一種理解和了悟,一種震撼或者解脫,一種痛苦或者愉悅,一種感嘆或者釋放;也是一種釋然與迷惘,更是一種心心相印的理解與一唱三嘆的欣賞。詩意的棲居不是說環境如何富有詩意,而是說棲居者內心自有詩意。倘若棲居者心中自有詩意,那么他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便也都富有詩意了。
汪建中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大地上的棲居者,所以他所見到的大地上的種種生命、種種景象以及由此產生的思考都充滿了詩意,他的《大地的翅膀》就是這樣一篇文章。
《大地的翅膀》寫的是前往北極的斑頭雁。文章一開頭,作者就在“斑頭雁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是他們年復一年的遷徙”這句話里,把那些確實“讓人難以忘懷的”、充滿詩意的景象再現給大家。
他滿懷深情地贊頌那些斑頭雁從各個居住地前往北極,又從北極圈向各自最初出發的地方往回飛的英雄壯舉。“就這樣,他們年復一年,一代接一代,從不間斷,在大地的上空往返,在歲月的流轉間來去……”他就這樣一唱三嘆地贊美著。把浩蕩的詩情、無邊的震撼都留給了讀者。仿佛我們也在那風雨、雷電、橙色和血色中和斑頭雁一起飛行,一起沐浴著詩的激情。
這萬里長征一樣的偉大飛行,最終的目標只是北極的“巴掌大的一塊陸地”。到了這里,“它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休息,就是美美地睡上一覺,把艱難與險阻的折磨、雷電與風雨的創痛、長途飛翔的勞累、生與死的噩夢全都退還給海洋,緊緊地依偎著同伴,趴在地上,閉上眼睛,把頭插進翅膀里,進入一個甜美的夢鄉。但是,它們在次日的黎明時分醒來后,發現有不少同伴已經死去,死在到達陸地之后,死在一個溫馨而久違了的睡夢里。看見同伴死了,斑頭雁們十分悲傷,一只只站起來,昂著頭,竭盡全力伸長脖子,使勁拍打著翅膀,沖著血色的天空,‘嘎嘎嘎地狂叫不止……”
讀到這里,已經夠讓人震撼無言了。此時,人們一定會想到元好問的《雁丘詞》,想到“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想到“君應有語,渺萬里層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誰去……”,甚至我們的眼前出現的已經不是什么大雁,而是屈原筆下的國殤勇士。
是啊,這些犧牲在物種發展、種群壯大的戰場上的偉大鳥兒,和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犧牲在戰場上的人類戰士有什么兩樣?大地的翅膀后邊就是大地之殤。
作者寫到這里還不肯停下筆來,又對這些犧牲的鳥兒再一次進行血淚描寫:“那些死去的斑頭雁靜靜地躺在陰冷的夕陽里,身上的羽毛被寒風吹起,一顫一顫的。而風的聲音,是那樣輕微、低迷而又空寂,似在哀述,又似在哭泣。此情此景,尤為凄涼,叫人一看就禁不住淚光迷離,整個心靈有一種再也找不到歸路的凄然與蒼茫……”
讀到這里,我知道了作家為什么要在翅膀前面冠以“大地”。他這是在以大地的名義對鳥兒進行一次祭奠。在這里,作者以他極其飽滿的感情,極其蒼涼而沉郁的筆觸,把我們淹沒在極其悲壯而又寥廓的詩意之中。其實,這些偉大的鳥兒,是恐龍們的后裔,是比人類更久遠的生命,他們是更值得尊重的。
胡弦的作品《白菜在歌唱》,也是這樣詩意蕩漾的好文章。
從一開始,作者就像寫詩一樣,一往情深地歌唱著大白菜。開頭,“秋后的菜園里,往往剩到最后的,就是一棵棵大白菜,這是要陪我們越冬的菜”,一開始就把大白菜從后臺推上了前臺。
接著,作者寫兒時的心事:“就是在冬天的時候,家有一窖白菜,梁上掛有豬肉,白菜燉豬肉,圍著火爐熱騰騰地吃……”讀到這里,讓我們不能不想到“紅泥小火爐”了。
作者用本地“拉魂腔”的調調,仿佛行吟詩人一般,邊走邊唱似的來寫白菜的生長。“白菜本是鋪開來長的,它寬大的葉片像巨大的花瓣一樣張開,只有白菜的生長最像開花,看著大白菜一天一天長大,人是歡喜的。那層層疊疊的葉片,像精致的花邊,像無憂無慮的心,像不知煩惱的青春,像歌聲……”
作者寫白菜走進城市,不寫它如何被擺上貨架或走上餐桌,而是一如既往地歌頌著它的心事,它的靈魂。“從夏到秋,多少白菜運進了城市,這濃眉大眼的菜,這一身清香的菜,這一層層裹著密密波浪的菜,它的心事,是它蕩漾在細致的葉綠素里的魂。”
這里雖然是寫白菜,但有關白菜的吃法用途,卻著墨甚少,而是去寫它們的精神世界了。
直到結尾,作者還用一剎二剎的方式,用“我知道”“我還知道”來寫白菜“都有一顆金黃、柔嫩的心”,“所有的白菜,都已把自己抱成了晶瑩的翡翠”。
然后依然情不能已,淋漓酣暢地寫下去:“在深秋在鄉下,只要田野里還有沒被收走的白菜,那些夜晚就是難眠的夜晚,在炊煙裊裊的傍晚或清冷的月光下,打開窗子是陣陣秋風,打開秋風是白菜的歌聲,而在那歌聲的深處,有時你會遇到一縷鋒利的涼意。
“那是一脈流長了很久的涼意,仿佛是命運又仿佛是美德,在你不經意間對它有所了悟的時候,它會輕輕刺在你滾燙的血液中。”
讀這樣詩情蕩漾的文章,不僅讓人知某事、識某理,還在作者的引領下,在微醺和沉醉中,有所了悟。
詩意是一種情感,一種氣質,一種激情。有了這種內在,寫什么文章都會有詩意在蕩漾。如毛澤東那些明白如話的文章,甚至是政論文和新聞,如《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金三十萬,昨日過長江》……
文學的最終功用,是在陶醉與了悟中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