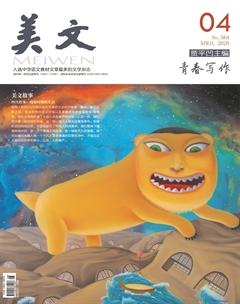與春天同在
范宇
2月3日的時鐘指針走過凌晨0時的分界線,我仍像往日一樣,背靠著床屏,在筆記本電腦上整理著關(guān)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采訪資料,加班寫著一篇篇來自防控疫情斗爭第一線的新聞稿件。身旁的妻子和兩歲半的女兒伊伊已經(jīng)熟睡,從她們安詳?shù)哪樕希夷軌蚋惺艿綒q月的平靜與生命的堅韌。
對我們這個生長在蓉城的普通家庭而言,這是立春前夕的一個日常深夜。
0時5分,我的筆記本電腦突然顫抖起來,伴隨著一起顫抖的還有一旁的衣柜門、玻璃窗和頭上的吊燈。我感到一頭的眩暈。“地震!”我趕緊連著被子一同抱起伊伊往門外跑,同時高聲叫醒熟睡中的妻子。妻子還沒回過神時,大地的顫抖已經(jīng)結(jié)束,伊伊在我懷中仍然安詳?shù)厮;蛟S,在伊伊的夢鄉(xiāng)里,有爸爸媽媽的世界從來都是春風暖陽、百花綻放。那么,就繼續(xù)睡吧!無論是大地的顫抖,還是病毒的肆虐,我和妻子都會盡最大的努力為她構(gòu)筑一張嚴密的防護網(wǎng),希望她如同春天里萬紫千紅的花一樣,盛開在最美好的年華。
這時的微信朋友圈是清一色的關(guān)于地震的消息或感觸,還有一個個抖機靈的段子流傳開來。近幾年,常常在網(wǎng)絡(luò)上看到對于四川人而言“五級震不醒,六級不起床”的段子,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自我寬慰。無論經(jīng)歷過多少,當?shù)貏由綋u時,生命的本能仍然促使我們向著生的方向拼命奔跑。每一個段子都是一次歷練,每一個感觸都是一次成長,人生就是在一個個段子中消解恐慌,在一個個感觸中抵御荒蕪,最終收獲的是對生命的敬畏、對歲月的珍重。
“成都市青白江區(qū)發(fā)生5.1級地震。”這是近年來地震離我最近的一次,也是震感最強烈的一次,仿佛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緒拉回到12年前的5月12日下午2時28分。這對每一個四川人而言,都是一段難以忘記的疼痛史,深深鐫刻在我們的心門之上。彼時,我正在老家小鎮(zhèn)上念高中,平生尚未經(jīng)歷過大災大難,對生死的概念仍然停留在身邊親人的離世中。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令山河搖晃,我搖搖晃晃地跟著疏散的大部隊來到學校操場,心里只感到一陣陣未知的恐懼。所有的通訊都中斷了,完全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接下來將會發(fā)生什么。后來,通訊逐步恢復,老師告訴大家汶川發(fā)生了大地震,一個個實時更新的傷亡數(shù)字和失蹤人數(shù),讓我第一次對無法抗拒的災難有了較為深刻的感知。
生命的脆弱和堅強同在,災難的疼痛與感動同行,逆流而上的人們并非不懂得珍惜生命,而是他們早已明悟:總要有人站在一線與天崩地裂斗爭,人類的生存史和文明史才有可能在一次次大災大難中續(xù)寫。那一年,我偷偷躲在被窩里哭了好幾場,既為離開的人們,也為逆行的人們。那一年,我承認是我心智成長最快的一年,開始慢慢探尋生命的意義,逐漸懂得歲月的無常和生命的偉大。
一個個春天的陽光如約灑向這片古老的大地,一朵朵嬌艷的鮮花不期盛開在生命的年輪里,一縷縷心中的陰霾慢慢散去,沉淀的是一次次生命的禮贊和對生活的感悟。2015年5月,綿陽市舉辦“百家黨報總編重走災區(qū)綿陽看創(chuàng)新”活動,我有幸跟隨時任資陽日報社副總編輯的王斌一同前往參加。這期間,我首次來到汶川地震的重災區(qū)北川,歷經(jīng)7年浴火重生的北川新縣城和作為廢墟遺址保留的北川老縣城,在陽光下形成鮮明的對比,一邊是歷史的記錄,一邊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記錄是為了銘記,創(chuàng)造是為了重生。兩個縣城就像是兩個生命的對話,一個代表過去,一個代表現(xiàn)在和未來。當我們站在山頭回望時,難免會有些疼痛的憂傷,可更多的卻是生命話語間留下的種種人生選項與可能。
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對話,最能洗滌人世間的種種雜蕪與污垢,晾曬出最本原的人生價值和最本真的天地情感。
在地震留下的廢墟之上,我發(fā)現(xiàn)另一對生命之間的對話。有一位姓成的母親,每年都會來到這里悼念在地震中喪生的孩子,把想對孩子說的話寫在一條條橫幅上,讓它在風吹日曬中與廢墟成為共情的永恒。我去時,這位母親已在廢墟之上掛了六條橫幅,橫幅之上寫滿她的思念,也映襯著她面對生活的勇氣。她來到這里,或許更為告訴孩子,在人間,媽媽會好好過。我將這個故事鐫刻成一篇散文《第六條橫幅》,這么多年過去了,似乎仍被這個故事感染著、啟示著——
面對防不勝防的大災大難時,被悲傷與疼痛裹挾在所難免,被大愛無疆與同舟共濟的潮水包圍無可回避,但作為一股涓涓細流匯聚成抵抗災難的洪流同時,也應(yīng)該在云淡風輕時從茫茫人群中鉆出來,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一個個具體的生命個體上。余秋雨說:“個體生命的完整性、連貫性會構(gòu)成一種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個小點都指向著整體價值。”我深以為然,當一個個生命個體的星星之火點亮人性之光時,整個世界都會充滿光明。不妨把宏大的敘事回歸到對個體生命的詮釋,或許你不經(jīng)意間的某個善意回眸,對某個生命就是一次開悟,菩薩低眉亦不過如此。
慈善的目光總能與生命對視,不忍的內(nèi)心總能與天地對話。
時光恍惚間回到眼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啟動之初,我便以一名記者的身份,記錄著這座與武漢隔著1300余公里的城市防控疫情的某些截面,刻畫著不同人群共同面對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的某些片段。山川相連,風月同天,我感動于這座城市盡心竭力支援湖北及武漢的一次次果斷行動;山河無恙,共盼春來,我也感動于這座城市齊心協(xié)力與疫情戰(zhàn)斗的團結(jié)精神;草木蔓發(fā),春山可望,我更感動于確診病例樂觀向上與病魔頑強斗爭的精神……在疫情防控一線,我記錄著、感動著、期盼著,希望春暖大地時,這座城市的每個人都與春天同在,將大好的春光攬入胸懷,一起放飛生命的希望。
晉某某是我所在縣城里第一例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者。他從武漢獨自驅(qū)車回到家鄉(xiāng),不久便因身體不適,收治在縣城里唯一成都市定點收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感染者的醫(yī)療機構(gòu)。他回到老家后,便獨自將自己隔離起來,沒與任何人密切接觸,包括其家人。直到身體感到異常,被定點醫(yī)療機構(gòu)收治。盡管如此,關(guān)于他的流言蜚語像肆虐的風一樣,在市民群眾的微信群、QQ群里到處亂竄了一陣。深深的憂慮情緒爬上一個個生命個體的額頭,成為這座城市的集體隱憂。
謠言止于智者,更止于現(xiàn)實。當晉某某治愈出院時,釋放出一個強有力的抗擊疫情的積極信號,它被一個個生命個體吸收轉(zhuǎn)化后,最終成為這座城市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的堅定信心。集體與個體,就像一座山與一棵棵樹的關(guān)系,當高山巋然不動時,作為生命個體的樹就有了櫛風沐雨的堅韌與向陽生長的樂觀。隱憂與信心之間,是生命之湖應(yīng)對外界變化掀起的波瀾,只有我們更加篤定生命的力量,波瀾才不會層疊成摧毀堤岸的滔天巨浪。
篤定生命的力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當?shù)弥晃还嗜艘蛎芮薪佑|過確診病例而集中隔離醫(yī)學觀察時,心頭也難免掠過一絲隱憂。“滄海橫流,但愿保重”,我?guī)е鴰追謸脑谒奈⑿排笥讶ψ钚乱粭l信息下面寫下如此評論,她卻十分樂觀地回復道:“待春暖花開時,我與春天同在。”再無多言,我卻能夠強烈地感受到她內(nèi)心的那份篤定,以及篤定生命的磅礴力量。
我被這樣的力量深深感染著。
她是一名護士,也是第一批寫下請戰(zhàn)書,要求到防控疫情斗爭第一線戰(zhàn)斗的醫(yī)護人員之一。在我的同學和朋友中,有不少分散在各地各醫(yī)院的醫(yī)護人員,從他們的微信朋友圈里,我看到了一份份按著紅手印的請戰(zhàn)書,也看到了一個個生命個體逆行的勇氣。他們從來都不承認自己是“最美的逆行者”,只認為在平凡的崗位上就應(yīng)該有一份平凡的堅守,而這樣的堅守何嘗不是生命的力量呢?他們或許不會成為歷史的銘記者,卻一定會成為歷史的共同書寫者,為許許多多的后世人寫就生命價值取向的生動范本。
立春一過,陽光就明媚地傾瀉在萬物生長的大地上,往常熙熙攘攘的街上仍然沒有幾個人,我的那位故人也還沒有解除醫(yī)學觀察,但我相信她以及這座城市的所有人,此時此刻都與春天同在。
伊伊隔著玻璃窗,向著春天的陽光,笑了。
而我和妻子,看著與春天同在的伊伊,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