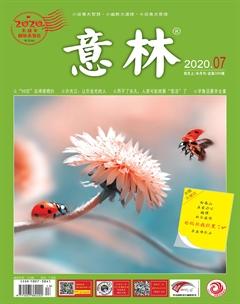君子知“怕”
朋友是個小心謹慎的人。晚上睡覺他一定會關掉煤氣,怕發生泄漏;上街絕對遵守交通規則,怕出現意外。工作中,他遵章守紀、秉公辦事,怕一不留神成為階下囚。
我非常贊賞朋友的做法,因為他知“怕”。其實,小到個人,大到國家,不都應該心存畏懼嗎?
個人應該懂得畏懼。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命就是老天爺賜予的命運;大人是指有地位、有號召力的人;圣人之言,是指古往今來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所發表的言論。孔子所說的“君子三畏”是否適用于今天的社會生活,我們姑且不去討論,但對于他“人要知畏懼”的主張,我雙手贊成。在現代社會,我覺得人應該“怕”的至少有兩種:一是應該“怕”法律,就是要遵守基本的法律與規章制度,用古人的話說,叫“畏法度”;二是應該“怕”道德,也就是那些雖不違法,但明顯違背社會道德、會被人戳脊梁骨的事絕對不做。那些因為圖一己之欲、逞一時之快而無視法律和道德的人,當他們為自己的“無所畏懼”痛悔不已的時候,不也正是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嗎?
不僅個人要學會知道“怕”,一個國家也是如此。許多國家都經歷過苦難和挫折,人民曾經深受其害,國家的文明進程也大大受挫。1845年,一種卵菌登陸愛爾蘭島,使得全島土豆減少三分之一,災荒一直持續到1852年。這場大饑荒使愛爾蘭人口銳減20%至25%。愛爾蘭人沒有忘記這場苦難,他們在首都街頭豎起了大型的紀念雕塑,其中一組饑民的群像栩栩如生,那哭天喊地的表情時刻提醒人們不能忘記歷史。在羅斯康芒郡的一座莊園里設立有大饑荒博物館,里面有關于這場饑荒的最完整的收藏。愛爾蘭的史學家和文學藝術家更沒有忘記這場大饑荒,關于這場饑荒的著作、論文、文藝作品如潮噴涌。生活是公正的,像愛爾蘭這樣知“怕”的國家,在災難來臨的時候往往有備無患,因而幸運地躲避了后來一些災難性的意外事件。
中國人一向諱言“怕”,在一些人看來,說自己“怕”,就等于承認自己怯懦,其實這完全是誤解。一個人知道必要的“怕”,他才可能去做好人、善人,去做君子;一個國家知道必要的“怕”,它才會將各種社會規則和保障體系設計得很完備,使之成為全體公民溫暖、快樂的命運共同體。
(本文入選2019年四川省廣安市中考題,文章有刪減)
游宇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在省級以上報刊發表作品700萬字,作品已連續20年進入全國性權威文學年選。
意林:文章入選中考現代文閱讀后,是否會把入選作為創作方向?
游宇明:我想不會。寫作本質上是一種靈魂的旅行,靈魂走到哪里,寫作就跟到哪里。我的文章進入中考試題和高考模擬試題數十次了,我對這些很有平常心。在我看來,入中考題也好,進各種教材也罷,都是讀者的一種選擇,而不應成為作家創作時的考量。作家應該奉行“好作品主義”,其余的則不宜想太多。
意林:您認為文章引起讀者共鳴的原因是什么?
游宇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少數人變得特別趨利,屢屢逾越操守和規則的紅線,不知敬畏,此文抓住一個“怕”字做文章,讀者也許覺得我說出了他們想說的話。
意林:經常在報紙雜志上看到您發表的文章,請問您如何選擇寫作素材?
游宇明:作家選擇怎樣的寫作素材,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視野,一是興趣。視野指的是他看到了什么,興趣指的是他喜歡什么。我是農村出身,又常常旅游,所以寫鄉村、山水、人生感觸的東西很多。我在湖南人文科技學院任教,上課之余酷愛讀書,因此,我的作品有相當數量的歷史隨筆、雜文。一句話,寫作必須寫自己熟悉的或感興趣的東西,才會顯出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