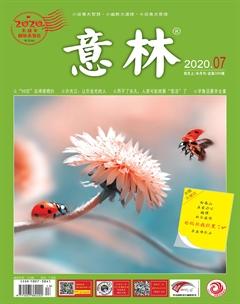我們不能打敗時間,但臘肉可以
暮易
寒風盈窗,葉枯草黃,蕭瑟天地間唯余一群鳥聲在嘰嘰啾啾,歡悅不寧,家鄉又到了忙腌臘的時節。房檐上裊裊出一縷青煙,很好聞,我愛那種柴火炊煮的濃郁氣息,一種萬物明媚的自然風光,恬靜沉著,每個人誠心虔敬交給蒼茫大地,交給質樸生活的樣子。
隆重年節到來之前,家家宰豬腌肉,一頓熱騰騰喜洋洋的殺豬飯少不了。殺豬飯的歡笑鬧嚷退去,奶奶會安坐在小凳上,不疾不徐靜靜地用棕葉穿肉。二百余斤的豬肉,幾十塊寶貝,春夏秋冬,是一年到頭的犒賞慰勞。鄉里離集市頗遠,費腳力,鮮肉不常吃,以臘肉臘腸款客饗朋,是村人能給的尊貴禮遇。夏天曬得干燥的花椒,麻烈襲人,碾成粉加鹽小火炒香,凈肉一條條均勻抹上椒鹽,只憑一雙經驗厚重的手拿捏揉搓的分寸,入缸腌制幾天,靜候佳容。
灌香腸別有風趣。肥瘦比例,香料佐料配搭,全現功力。川味的重麻且濃香,麻辣的突其平衡,麻感辣感雙重迸發,廣味的就甜膩些,小孩甚喜。不嫌厭煩的慈母總是心思周到,各樣俱備,老少照顧。洗腸、灌肉、捆扎,行云流水,一氣呵成。
追隨爺爺奶奶幫襯熏臘肉香腸,躥上跳下,是孩童獨特的娛樂消遣。上山砍來松柏枝,摘一摞朱紅的蜜橘,果肉吃畢余下橘皮,等待激動振奮的熏肉。吊干水分的腌肉,鹽分入里椒香浸透,風過的香腸微微發皺,進入熏制環節。肉條掛在火炕上,底下的松柏枝本是鮮柴,不生旺火,只搖曳起細細的白煙,加一些黃豆秸根,時不時喧鬧出嗶嗶剝剝的響聲,橙黃的橘皮盡可堆疊在旁,借著余燼噴薄出植物特有的甜香,各類自然風物的加持,一塊醇香迷人的臘肉方成氣候。

臘肉吃法紛繁,不拘一格,但凡有它的身影,粗茶淡飯也會陡然變得華貴生動。
從灶上取下的臘肉,皺縮枯萎,以淘米水洗凈,燉煮得宜,美艷重返。不同于鮮肉的粉紅,臘肉在鹽和時間的催化下,如明艷胭脂般滋生出一種嫣紅的貴氣,肥肉不再是直楞的素白,瑩潔通透,如薄冰靈光。煮熟切片擺盤,一定是一桌子菜肴里的紅玫瑰,讓人愛不釋口。隆盛一點的場合,主人講究地捯飭出幾個干盤子,風豬肝、臘豬耳、臘豬心、香腸、臘肉一應在場,品相優美,下酒佐食,饞人得很。有了臘味,日子才叫有聲有色,殷實豐裕。
炒臘肉是不必有多高超的廚藝的,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嬌娘和大廚制來的也并無二致。蒜苗或青椒咸菜,濃淡相宜,乃炒臘肉的佳侶。熬煮一鍋豌豆臘排骨湯、土豆臘肉湯,皆能舒心御寒。
臘肉香腸切細丁炒飯,臘肉的油脂將每一粒米飯裹緊,油光汪汪,抓人心胃,勾人口舌。近可香口,遠可解愁。臘肉耐儲,隨吃隨煮,遠行的旅人亦可大快朵頤。年年離鄉返城,母親的叮囑和各種臘貨非塞得冰箱滿滿當當才肯作罷,故鄉遙遠嗎?記不清的時候,吃一塊臘肉,它就在那里顯山露水了。
在顏色暗沉的冬天,臘味跳躍著一團團綺麗火苗,著實喜人,內心的孤寂無常瞬間被泯滅。它是冰箱里的常客,不時會出現在餐桌哄抬氣氛,為味蕾最忠實的守護者,看似笨拙土氣,實則熱忱深情。臘肉是細水長流的食物,細細涓涓,不經意間就鐫刻進了滄桑半生。它又毫不做作虛矯,既無高明的技法噱頭,亦無繁雜的佐料亂舞,肉加鹽,交給時間,就是最偉大的食物哲學。
四季流轉,在家鄉人的眼里,臘肉已成為他們心底最強烈的味覺印記。再奢靡的珍饈美饌,也抵不過一塊臘肉賦予他們的柴米油鹽的滿足和歲月靜好的喜悅。冬入深處,生命歸于沉寂,月色清明,無所謂蕭條,因為吃過臘肉,很快就要春暖花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