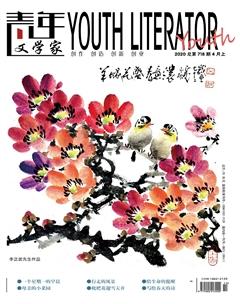從黃桷埡出發的人
吳景婭

從前,山下到黃桷埡,只能去爬黃葛古道,一爬小半天。那古道真古,始于唐,興于宋元,鼎盛于明清……那古道旁植有黃葛樹,大大小小,各蔭一方天地,一棵隱匿在另一棵的身后,隨古道婉約、長高,綠意通天,伸入無限的迷離;那石板路上的石板也都是幾百歲高齡的老家伙了。人們把它們重重疊疊彼此鑲嵌,一塊墊著另一塊的背脊骨,它們也毫無怨懟,老老實實地順了自己的命,任千萬腳千萬次地踩在它們的身體上,踩出泛著青色的光溜溜的肌膚。
有些石板上也留有深深淺淺的馬蹄印。可以想見擅長爬山的川地馬登這樣陡峭的坡地也是不易,要使出拼命的勁來。于是一路烙下的這些馬蹄印,個個皆辛苦,猶如一枚枚的勛章,在一路頒發。
三毛說,她沒想到的是父親會采用騎馬這種交通方式,去山里的律所上班……會不會也包括了去山下美豐銀行大樓上班的時候?當律師的父親是那樣文弱。
這個在我聽來也像是個神話。騎馬上山還容易。下山,那些幾百歲的青石板多少長了些苔癬。如果再遇上雨霖霖,泥濘處,會不會馬失前蹄?還有,當年接近海棠渡那一帶是馬尾松林遮天蔽日。大暑天走著,也有森森陰冷氣偷襲背脊。如果是霧氣沉沉的冬季呢,重慶冬季總比夏季長啊!
父親即使順暢地下了山,他的馬會栓在海棠渡的哪里?坐船過江爬上陡峭的石梯坎后,從望龍門到打銅街,他是徒步還是坐車?在美豐大樓這座當時重慶最高最時髦的標志性大樓里,父親又是在怎么個廢寢忘食地仔細做事?
三毛好想知道這一切。她總覺得父親在這片土地上的故事像一堆剛剛燃盡的炭火,尚有余溫。但,能清楚告訴她的人好像已沒有了。短促的幾十年卻是朝花夕拾,變了人間。
她說,兒時,睡在黃桷埡的老院子里,總聽得到那匹馬嗒嗒走路時的聲響,它們的輕與重,讓她一下便能判斷出父親離得有多遠;是已在九宮廟的老黃葛樹下歇腳,還是邁入了他們繆家院子的后門。踢嗒聲近了,便是她的節日;遠了,她的小胸膛里便裝滿憂傷。
我后來才知道,那時以馬代步在山上山下奔波求生的還不只有三毛的父親,大畫家傅抱石也算一個。傅氏當時住在歌樂山,要下到沙坪壩的中央大學來講課,坐不起轎子時,也會選擇騎馬而行。那個年代像三毛父親陳嗣慶這樣的中國精英男士,哪怕在抗戰大后方的重慶,也活得很不容易。左肩總想以一己之長來報忠國家,右肩還得擔負一家大小的生命安危和柴米油鹽……他們是中國歷史上最累的那一撥男人。
差不多快三十年前,我和三毛坐在重慶飯店,頻頻隔窗去眺望對街的那幢當年的美豐銀行大樓,以此來向一位辛苦又偉大的父親致敬!
這是我和三毛的第一次見面,在重慶寒色漸現的深秋。我坐在三毛身邊,就像坐在自己的夢里面,見著一個穿花布裙的女子影影綽綽從撒哈拉沙漠、西班牙的橄欖樹林、秘魯的馬丘比馬古城走過來,嘆著氣,千山萬水的。
怎么可能呢,這個照亮過我生命的女子,竟與我咫尺之隔?!
她人很疲憊了,不停地咳嗽。身體的衰弱仿佛在拖累她的靈魂。好在,她的聲音實在年輕,讓人不敢相信那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清亮,溫暖,迷人。那是第一時間里會激發你去接近并呵護它主人的聲音。
我們的話題從一對耳環談起。
那天,我把自己打扮得很“三毛”, 渾身叮叮當當,戴了紅紅綠綠夸張的藏式耳環和首飾。其實,這已是我多年的著裝風格了,帶著對都市精致規范的不屑,仿佛隨時都會叮叮當當踏上陌生之旅去流浪。
而“流浪的教母”正與我面對面,她比我想象的瘦小、虛弱……哪里尋得到她狂放不羈的焰火?她喜歡低頭,長發順耳流泄而下,臉頰更顯清癯,皺紋在那里不動聲色。她問:你的耳環在哪里買了?夸張得好……
女人通向女人原來就這么簡單!
我們汪洋恣肆地聊她那些在別人眼里根本不值半毛錢的“寶貝”——從美濃鄉下淘到的一把油紙傘,到雕刻著福字的老銅戒指……她說,有些東西跟著你的年代一久,便成了家人。家人哪里能去論貴賤,也不能隨便就丟下吧。
我小心翼翼地與她繞到了男人這個話題——
我們繞過了荷西……我不忍心,她實在不是我們以為的那個強悍瀟灑、百毒不懼的三毛。
我們談那些無關痛癢的男人們,過一把指點江山的癮。
三毛對內地男人有種文化和地域的陌生感,他們讓她好奇、新鮮又困惑。
她語調婉轉地說,覺不覺得中國現代的男人好像缺少點舊式男人的儒雅氣和謙和?我極其贊同:“還是該讓他們穿長衫子。讓他們粗野的時候多少沒這么利索。”她被我的話弄笑了,眼里突然炯炯有神。“臺灣偶爾也會見到穿長衫子的男子。只是在一種場合,帶著禮服性的色彩。但好像都不對呀。好像穿長衫子的男子就只能呆在那樣的時空里。走過了,就不是那回事了……”她真是明察秋毫。但,似乎再尖銳的問題經她柔聲細語地說出來,就不那么鋒芒畢露了,她的聲音自帶了一種敦厚和寬容。
談王洛賓時也是風輕云淡。她很坦率地表達自己對他的好感,王洛賓是能夠撬動她隱秘激情的人——這不僅是因他曾為了理想圣徒般地在荒涼的西部流浪,也不僅是因他創作出那么多堪稱不朽的經典歌曲,更是因他的苦難!對,他的苦難像萬箭齊發的光束,逼得她背過身去。只是她沒想到那個寫下《在那遙遠的地方》詞曲的人竟還活著。他是怎樣活下來的?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一切。更想代表命運對這個度盡劫難的人加以補償……
川端康成曾說,青年人有愛情,老年人有死亡。恰好站在中年門坎上的三毛,真想攥住自己與王洛賓的頭發,升騰,擺脫時間的萬丈深淵……
三毛把王洛賓當作了自己的精神伴侶,世俗中的在不在一起已不重要。
愛情一直是三毛很重要的人生課程。在這個課程中,她既是學生,又是老師;她既會看見樹,更會看見森林。她理解的愛情也與常人不同,有種宗教意義上的廣闊,不是那種情感上的小女人,計較著一畝一地的得失。
三毛說自己其實是不擅交際的人,所以有時會造成一些讀者對她的誤會。
我知道,三毛有她的另一個世界,那是她為自己獨留的桃花源。我們這些“武陵人”自以為早已闖入過了,其實,即便作了多少記號,也不會再找到入口了……誰又能真正懂三毛?尤其是夜深人靜時的三毛,誰會深味她的輾轉反側?
我問她這次去不去黃桷埡看看,那個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呆到四五歲,才隨父母去南京,而后又去的臺灣,算起來已四十三、四年了。
三毛沒有回答我,感覺得到她的踟躕。她在糾結什么呢?少小離家,就怕老大還?她害怕了那沉甸甸的四十多年的時間……
顯然,黃桷埡在她記憶中絲毫沒有衰老過,她總是把它和那個野里野氣的自己一起記錄在案了。她還記得自己只管瞎胡鬧,“嗵”地一聲卻掉進了地下埋著的大水缸里,大人把她撈起來,臉都嚇白了,她還嘴里邊往外吐水邊幽默地說:感謝上帝。黃桷埡背街的山上墳堆林立。大人在嚇唬:別去哦,別讓里邊躺著的人逮住哦!她卻不信邪,偏愛在那些墳堆與墳堆之間爬來爬去。天黑了,大人喊了又喊,她仍在那里晃蕩。
她問我,重慶現在還有那種小黃花嗎?一到四五月份,野外到處都是的那種小黃花?我說還有還有,仲春便漫山遍野都是,一直開到夏天的尾巴。我們也叫它小黃花。還查過,說不清學名該叫“抱莖苦荬草”還是“串葉松香草”……“小時候我很喜歡和姐姐一道用媽媽的空藥瓶子盛滿井水,養一大篷小黃花在房子里。它也有香氣,帶著藥苦味的那種。”
該告別了。
我把那對色彩扎眼的藏式耳環送給了三毛。她攤在一支手的掌心間,用另一支手去撥弄,歡喜雀躍地說:給我了嗎?我要帶著它回臺灣,還有好多地方……
那一刻我相信了三毛的喜悅。我以為那樣喜悅著的三毛就是她該有的樣子和永遠的樣子。所以我起身告別的姿勢無比輕盈,仿若我們第二天又會再見面——
我邊向門邊退去,邊搖動手:三毛再見!
她如夢初醒:啊,這就走了……
一直記得她仿佛被什么蜇了一下的眼神,倏忽便黯然。她是個怕告別的人。
我步履輕快地下樓,以為后會有期。卻沒想到一面永恒……
兩個多月后,傳來三毛走了的消息——這么多年了,我都是用這個中國字來表述一個事實。曾為三毛留下若干經典瞬間的人像攝影大師肖全也同樣,在我們談及那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時刻時,他雙手向天開啟,說,三毛是飛了……我們都不愿接受她的自我了斷,那成了我們人懸崖下滄海中的旋渦……
1992年深秋,我在敦煌的鳴沙山到處找三毛的衣冠冢。沙海浩渺,人如螻蟻,哪里找得到?!
風才不管。它仿佛是從月牙泉那些長勢喜人的蘆葦叢之間一路吹拂過來,讓人神清氣爽,恍惚作了春風。想起三毛為電影《滾滾紅塵》寫的那句歌詞:至今世間仍有隱約的耳語跟隨我倆的傳說……獨愴然而涕下。
去年十月,我見到了三毛的大姐陳田心、弟弟陳杰以及弟媳、侄女,還有其閨蜜——畫家薛幼春……我們在一起無拘無束像家人一樣地聊天。他們為我構建了另一個立體可觸的三毛世界,讓我得以更深邃地繼續閱讀三毛。至少,她不再是我幻覺中那個孤孤單單漂泊在塵世間的女子,只是靠喝著浪漫和不羈的西北風而存在。她也是人家的妹妹、姐姐、小姑子、姨和嘰嘰喳喳說悄悄話的閨蜜。
這一家子個個溫文爾雅、談吐不凡,配得上做三毛的家人。尤其是近八旬的大姐陳田心,穿一身玉白色的蕾絲旗袍,斜戴一頂淺駝色的薄呢貝雷帽,兩耳綴著紅珊瑚的耳環,與紅珊瑚的花朵胸飾遙相呼應……她說話,柔聲細氣;微笑,抹著珊瑚紅的嘴唇便成優美的弧型……感謝她,讓我能揣想三毛老去的模樣……
薛幼春女士穿著當年三毛送給她的布長袍,白底藍花,扎染的那種,頭上系著同色系的發布。我小心翼翼和她談及心里的結——三毛為什么要放棄?她握住我的手,語氣堅定:三毛從沒放棄!她身體的痛苦非一般人能去想象和承受。她不愿它再拖垮自己的靈魂……
我沉入自己的海洋,四周游動著海參——女詩人辛波斯卡說:它舍棄一半自我,留給饑餓的世界,帶著另一半逃逸。它暴烈地將自己分成死亡與拯救,懲罰與獎賞,曾經與未來……女詩人這樣寫著海參面臨危險時的“自斷”。它把自己分成了肉體和詩歌,“一邊是喉嚨,另一邊是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