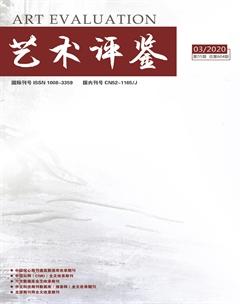從美術文論看西畫東漸對明末清初畫學的影響
曹明
摘要:西畫東漸對明末清初畫學的影響是個頗有爭議的話題。學界基本不否認這種影響的存在,但影響的力度、是否對后來中國畫的發展產生影響則是爭論的焦點。我們不囿于個別畫家或傳教士的魅力,也不著迷于社會學、經濟學的宏大敘述,而是翻閱那個時期保留下來的畫學專著或筆記題跋,試圖從文本的角度一窺西畫東漸在明末清初畫學的印跡。
關鍵詞:美術文論 ? 西畫東漸 ? 明末清初 ? 畫學
中圖分類號:J205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05-0043-03
自20世紀90年代,隨著眾多文檔的解密,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相關資料如書籍、來往信件不斷被發現,人們對那段似乎被歷史的風塵有意或無意遮蔽的歷史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學界對明末清初西畫東漸的研究也漸趨活躍。其中西畫東漸到底對中國當時的畫學和以后中國畫的發展是否產生影響及其深度、廣度均產生較大的分歧和爭論。一種觀點認為西畫東漸并沒有對中國畫學的發展產生實質影響。無論從當時還是以后的繪畫理論和實踐上,中國古典繪畫的話語體系依然是民族的、自足的。與之相反,一些歐美學者則認為西畫對當時的一些畫家個體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畫的發展。
明清之際執掌畫學牛耳的依然是那些文人士大夫。他們在創作或鑒賞之余,總會把自己的觀察和體悟行諸文字,或畫學專著、或筆記題跋。研究那些幾百年前文字中鮮活的思想和中西文化碰撞的歷史痕跡,或可追索西畫東漸對國內畫學產生影響的草蛇灰線。
明朝中后期,西方傳教士發現利用宗教繪畫進行傳教活動可以起到語言文字難以企及的效果,如傳教士金尼閣、畢方濟等人“皆言及用西洋畫及西洋雕版畫以為在中國傳教之輔助而收大效之事”[1]。1583年,羅明堅在肇慶所建的小教堂中懸掛圣母像,供信教民眾參拜。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傳教士利瑪竇呈獻給神宗皇帝的禮物中就包括一幅天主像和兩幅天主圣母像。喬瓦尼則在澳門教習中國人學習油畫。清朝前期的皇帝對異域文化相對抱有較寬容的態度,除了有對漢族文人集團所把持的學術話語權有所抑制的考慮外,也不乏宣揚其戰功偉業的“政治寫真”的需要。康熙末年 ,清廷與羅馬教廷的“禮儀之爭”,使得傳教士在內地的生存環境日趨嚴苛。“蘇州教案”和“江南教案”事件實際上使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在乾隆中葉趨于絕跡。
馬渭源在《論西畫東漸對明清中華帝國社會的影響》一文中述及社會各階層對西畫東漸作出的回應,并把西畫東漸研究的視野拓展到中外經濟與文化交流的范疇。對一種美術現象的考察固然可以有宏大的視角,但針對文本的考察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更有接近于事件真相的可能。
明代姜紹書在《無聲史詩》“西域畫”條目寫道:“利瑪竇攜來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踽踽欲動,其端嚴娟秀,中國畫工無由措手”[2]。蘇州知府趙心堂初見利瑪竇攜來之天主像,不禁贊嘆道:“是像非常,真為天地萬物之大主矣”,
乃設高堂,行跪拜禮。[3]
杜赫德曾描述過滿清官員無法理解在一張紙上如何能如此逼真的再現亭臺樓閣,“初見時,還以為是真的”。康熙時代,畫家切拉蒂尼用巴洛克風格裝飾北京耶穌會教堂的墻壁與天花板,當時參觀教堂的人們“不能相信那柱子是畫出來的。當他們抬起頭看天花板時,那些按照透視方法描繪出來的巨大空間,那些似乎在天國中漂浮的人物,令他們驚嘆不已”[4]。
中外美術交流的歷史早已有之。南朝畫家張僧繇的佛道壁畫人物就吸收了源自印度的“凹凸法”,通過暈染加強人物表現的立體感,敦煌壁畫也依然保存有“凹凸法”的畫跡。但是中國傳統繪畫的基因來源于文化,從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中國傳統繪畫并不是真正的視覺藝術,它只是文化的一種表征,是文人士大夫對于自身生存環境和所持儒家思想的一種隱喻。長期以來,文人繪畫并沒有追求技法和視覺真實的需要。民間畫工也只是把繪畫當作糊口的技藝,缺乏變革的動力,最多也只是一些炫技的刻苦罷了。在這樣一種大環境下,中國傳統繪畫在自足的發展,雖然也有風格的流變和個別畫家的嬗變,但終不離傳統的筆墨語言和丘壑樣式。普通民眾在突然面對全新的一種繪畫樣式,特別是寫實主義這種具有強烈視覺沖擊力的藝術形式,其不解和震驚自是難免。
傳教士出于傳教的目的,與北京、南京的官僚士大夫集團多有接觸。部分思想開明的文人如徐光啟、李之藻等對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抱有濃厚的興趣。一些畫家對西畫亦持相對公允的態度。
明徐光啟對《幾何原本》的翻譯其實已經把畫法幾何傳入國內,為國人掌握和運用真正意義上的透視法奠定了基礎。清代畫家丁皋在《寫真秘訣》附錄《退學軒問答八則》有云:“夫西洋景者,大都取象于坤,其法貫乎陰也。宜方宜曲,宜暗宜深,總不出外寬內窄之形,爭橫豎于一線”[5]。宮廷畫家鄒一桂認為:“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繪畫於陰陽遠近,不差錙黍。所畫人物屋樹,皆有日影。其所用顏色與筆,與中華絕異。布影由寬而狹,以三角量之。畫宮室于墻壁,令人幾欲走進”[6]。這些以乾坤陰陽等民族語言來理解西畫,相較于科學的透視法,還都屬于經驗的層面。
作為清高級官員的年希堯在初版《視學》序文《視學弁言》中有云:“余囊歲即留心視學,率嘗任智殫思,久未得其端緒。迨后獲與泰西郎學士數相晤對,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繪事”[7]。其所附圖版詳細介紹了西方透視法。在再版序言中,年希堯甚至有中西融合的想法:“中土工繪事者,或千巖萬壑,或深林密箐,意匠經營得心應手,固可縱橫自如,淋漓盡致,而相賞于尺度風裁之外。至于樓閣器物之類,欲其出入規矩毫發無差,非取則于泰西之法,萬不能窮其理而造其極”[7]。遺憾的是,在那個時代能以科學的態度和精神研究中西繪畫的學人和畫家實在太少。
在16-18世紀的畫論文本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中國社會至少是文人士大夫階層對西畫的態度從較寬容到日趨保守。
萬歷崇禎年間汪坷玉《珊瑚網》記載《西士作曼倩采桃圖》,有“亦頗神彩生動……雖吳道子運筆諒莫能過”之語。[8]陳烺在《讀畫輯略》中述及焦秉貞:“工人物,能以仇十洲筆意參用泰西畫法,流輩皆不及”[9]。蔣廷錫對所畫《牡丹》對西畫也頗多贊譽,他曾自題扇面:“戲學海西烘染法”。得意之情躍然紙上。清初幾位皇帝對西洋繪畫也情有獨鐘。康熙認為:“西洋人寫像,得顧虎頭之妙”。[10]并多次下旨征召懂西洋繪畫藝術的畫家入值供奉御用。他還把傳教士馬國賢刻印的避暑山莊三十六景銅版畫頒賜給他的子孫和皇親貴戚。
但在“四王”的藝術審美價值取向與審美標準成為官方和文人士族的精神燈塔的情況下,即便皇帝的藝術喜好也只能囿于紫禁城。作為宮廷畫家的鄒一桂雖也習學西畫,但骨子里仍堅定自己文人畫家的風骨:“學者能參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筆法全無,雖工亦匠,故不入畫品”[6]。這基本代表了當時文人畫家對西畫的基本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的一些畫家在看到西方寫實主義繪畫后,雖然不以為然,甚至義憤填膺,但確實在自己的創作中多少吸收了西畫的透視技巧和色彩表現,以使作品顯得更加立體,畫面空間更加真實。但這種將中西不同的觀察方法和表現技法加以綜合,創造出的所謂折衷主義畫風,影響范圍既不出紫禁城的高墻,也很快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而趨于消亡。
從大量文本的記述來看,基于文藝復興寫實主義風格的西畫在承擔宗教的功用方面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西畫獨特的藝術感染力特別是強烈的視覺沖擊力也著實吸引了一部分思想開明的文人畫家和市井畫工的興趣,并在自己的創作中有所體現。但我們不得不承認,西畫的影響確實有限:
就影響的人群而言,明末的萬歷皇帝對西畫的興趣僅在于新奇,新鮮感一過,也就不了了之。清康熙帝雖然征召懂西畫的傳教士為皇家服務,而且著令培養了一批掌握寫實技巧的院畫家,但所有的影響基本不出紫禁城的院墻。另外,康熙帝對西畫的重視,固然有個人喜好的原因,但作為一代英主,其實更看重西方古典寫實主義繪畫的強大視覺沖擊力和可復制銅版畫所具有的巨大傳播力量,這些都可以為政治服務。特別值得玩味的是,那些曾經在清宮供奉過的院畫家在離開紫禁城之后,又都回歸文人畫的傳統,幾無西畫的痕跡。如院畫家陳枚雖然學習過西畫技法,也創作過運用透視法的作品,但告老還鄉之后,其創作完全是傳統文人畫的趣味。明末清初,執畫學牛耳的董其昌和“四王”等學派雖然據考證都曾接觸過西畫或傳教士畫家,但在他們的書論畫論中,都絕少見到有關西畫的文字。至于廣大的士大夫畫家群體,西洋繪畫在他們的眼中就如茶余飯后的談資,卻也很快風輕云淡。民間畫工雖然以西畫為炫技,吸引市井百姓的興趣,但缺乏專業的畫法指導,終不免粗疏。隨著時間的流逝,民間繪畫殘存的那一點“泰西法”的印跡也逐漸消亡。
就影響的地域而言,西畫東漸的范圍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根據莫小也等專家學者的研究,北方天津楊柳青和南方蘇州桃花塢作為民間年畫的重鎮,也留下了西洋畫的印跡。另外,1614年,喬瓦尼在澳門的基督教圣保祿修院里設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傳授西方繪畫的美術學校,培養了倪雅谷、游文輝等一批中國的油畫家,并把與澳門相鄰的廣州發展成一個西畫中心。但這些地區相比廣大的明清疆域而言,實在微不足道。當時絕大部分地區的中國人可能終其一生也沒有接觸過西畫。即便是廣州,這個當時最“西化”的城市,按蘇利文的說法:“沒有跡象證明,在廣東與其它開放港口的文人學士受到過歐風藝術的絲毫影響,因為采用外國風格的畫家并不是與耶穌會有關的學者,而是那些沒有地位的畫家,他們竭盡全力為外國市場制作西畫,僅此而已”[4]。
就對當時社會各階層思想層面的影響和推動封建社會變革的可能性而言,西畫東漸的作用也并不顯著。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傳教士自身的素質所決定。許多傳教士及其信奉的宗教本身就對近代科學技術抱有敵意,更遑論傳播西畫所體現的文藝復興之人文主義和科學思想。二是傳教士到中國的目的并不在于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而是進行宗教思想的傳播,擴大基督教的影響力。據統計,從1582年利瑪竇來華到1773年耶穌會被解散的近200年間,耶穌會士在中國譯著西書437種,其中純宗教書籍251 種,占總數57%。[11]他們秉承的“文化傳教”策略,是通過權衡當時中華帝國國力而采取的一種妥協的手段。
西洋繪畫進入中國恰逢董其昌的“文人畫”與“南北宗”理論及“四王”的“襲古”“泥古”之風席卷畫壇,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審美價值取向之時。畫家的繪畫風格趨于同質化,任何變革創新的努力都會被視為異端。在這樣的范圍中,寫實主義的西畫和以筆墨意趣為旨的文人畫當然顯得格格不入。我們現在翻閱那個時代的畫論和筆記題跋,終不免臆測,如果西畫東漸一直延續下去,如果后來的文人畫家能持更寬容的態度,現在的中國畫會是何種面貌?
參考文獻:
[1]胡光華.中國明清油畫[M].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1.
[2]姜紹書.無聲史詩[A].于安瀾.畫史叢書卷七[C].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
[3]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M].北京:上智編譯館,1947.
[4]蘇立文.明清時期中國人對西方藝術的反應[A].黃時鑒:東西交流論譚(第一集)[C].上海:上海文藝出版,1998.
[5]李來源,林木.中國古代畫論發展史實[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
[6]鄒一桂.小山畫譜[A]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十四)[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7]年希堯.視學[A].《續修四庫全書》編篡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第1067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汪珂玉.鐵珊瑚[A].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三)[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9]王伯敏.132名中國畫畫家(三國-現代)[M].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4.
[10]方豪.中西交通史[M].長沙:岳麓書社,1987.
[11]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