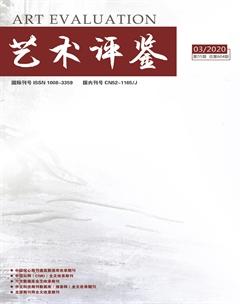亞瑟·丹托藝術(shù)終結(jié)論面面觀
陳怡蘋
摘要:“藝術(shù)終結(jié)論”的主要提出者是美國當(dāng)代著名的分析哲學(xué)家、藝術(shù)評論家亞瑟·C·丹托,他在自己所著的《藝術(shù)的終結(jié)》一書中,全方位地解讀了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等人的美學(xué)思想,以不同的視角開辟出了自己的藝術(shù)理論。此書一經(jīng)出版,便引得西方藝術(shù)界和美學(xué)界眾說紛紜。由于翻譯的問題和中西方語境的差異,亞瑟·丹托的《藝術(shù)的終結(jié)》在國內(nèi)流通的譯本造成了國內(nèi)許多讀者對丹托理論的誤解。基于這種錯(cuò)誤的理解,人們所看到的必然是被扭曲的丹托。筆者將基于亞瑟丹托《藝術(shù)的終結(jié)》一書,廣泛引證國內(nèi)外藝術(shù)評論家發(fā)表的對亞瑟丹托理論的文論,試圖闡述清楚藝術(shù)終結(jié)理論的實(shí)質(zhì)核心。
關(guān)鍵詞:“藝術(shù)終結(jié)論” ? 亞瑟·丹托 ? 哲學(xué)與藝術(shù)
中圖分類號:J0-05 ? ? ?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05-0162-02
藝術(shù)與哲學(xué)的關(guān)系既悠久又復(fù)雜。自藝術(shù)與哲學(xué)從人類文明中誕生以來,這兩門學(xué)科的關(guān)系就一直處于一種游離的狀態(tài)之中,百世紀(jì)以來無數(shù)學(xué)者對藝術(shù)與哲學(xué)的關(guān)系下過定論,卻始終無法正確看待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就如丹托在他的《藝術(shù)的終結(jié)》的開篇卷首語中所說:“把握這種其微妙程度恰足以與身心關(guān)系相提并論的關(guān)系,也許超出了我們所使用的分析性描繪法之所能,因?yàn)槲覀冞h(yuǎn)不能做到將藝術(shù)與哲學(xué)清晰地區(qū)分開來,因?yàn)樗囆g(shù)的本質(zhì)部分地是由被哲學(xué)所認(rèn)定的東西構(gòu)成的。”藝術(shù)和哲學(xué)的關(guān)系究竟如何?藝術(shù)到底會不會走向終結(jié)?終結(jié)后的藝術(shù)又會以怎樣的方式延續(xù)新的故事呢?筆者將對亞瑟·C·丹托藝術(shù)終結(jié)理論來源以及其理論核心做出的考察與解析。
一、柏拉圖對藝術(shù)的抨擊
柏拉圖的美學(xué)觀點(diǎn)與亞瑟·丹托藝術(shù)理論的形成息息相關(guān)。他認(rèn)為,藝術(shù)終結(jié)理論的源頭就在于柏拉圖對藝術(shù)的論斷之中,所以考究柏拉圖的藝術(shù)哲學(xué)理論意義十分重大。
亞瑟丹托在書中提及柏拉圖對藝術(shù)的兩階段抨擊:第一階段是主張“藝術(shù)與真理隔了三層”。“柏拉圖將藝術(shù)的實(shí)踐視為創(chuàng)造表象之表象,認(rèn)為它雙倍地遠(yuǎn)離了哲學(xué)所處理的實(shí)在(reality)。”柏拉圖將藝術(shù)定義為對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模仿,而現(xiàn)實(shí)世界則是對永恒不變的“理式”的模仿,如此一來,藝術(shù)便僅僅是一種與真理相去甚遠(yuǎn)的拙劣的模仿了。“認(rèn)為藝術(shù)閾限于第二序列現(xiàn)象范圍之內(nèi)的看法,就保證了藝術(shù)即使是在略少變質(zhì)的第一序列現(xiàn)象范圍內(nèi),也完全是無能為力的—它作為一種極端微不足道的現(xiàn)象,如同夢幻泡影一般。”柏拉圖試圖將藝術(shù)定義為“如夢幻泡影一般”的“一種極端微不足道的現(xiàn)象”,把藝術(shù)與哲學(xué)的距離拉開,同時(shí)也將藝術(shù)與政治實(shí)踐隔離開來,這樣一來,藝術(shù)就是一種十分邊緣化的事物了,必然也不會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產(chǎn)生任何影響和作用。“第二個(gè)階段在于盡可能地使藝術(shù)理性化,以便讓理性逐漸侵占情感的領(lǐng)域,是美的。”丹托指出,柏拉圖的這一階段的觀點(diǎn)極有可能是受到蘇格拉底對理性美執(zhí)著的認(rèn)同的影響,他稱之為“美學(xué)上的蘇格拉底主義”。自此,柏拉圖完成了他對藝術(shù)的兩個(gè)階段的抨擊,第一階段先使藝術(shù)變得微不足道并進(jìn)而使之無害,而第二階段則是在一定程度上認(rèn)可藝術(shù)的合理性,同時(shí)將它理性化,把它變成古典美學(xué)范疇中的一個(gè)微不足道的概念。這兩種階段產(chǎn)生的兩種論斷確保了藝術(shù)不會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產(chǎn)生任何的威脅,且僅僅是一種脫離現(xiàn)實(shí)的、無害的存在。如此看來,柏拉圖的美學(xué)理論可以說是藝術(shù)終結(jié)論的前身。
二、康德“藝術(shù)無利害性論”
康德是柏拉圖美學(xué)理論積極的繼承者之一,他從柏拉圖對藝術(shù)抨擊的第一階段出發(fā),繼承發(fā)展了他的觀點(diǎn),他采用了一種較為迂回的表述方式,將藝術(shù)描述成為一種“無利害性”的事物,認(rèn)為我們應(yīng)該以一種無利害性的態(tài)度去對待藝術(shù)作品。所謂“無利害性”是一種與“有利害性”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有利害性”是指這件事物對個(gè)人或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旦這件事物發(fā)生了改變或者不存在了,任何個(gè)人或社會都會發(fā)生一定程度的改變。一旦人們接納認(rèn)可了康德的“藝術(shù)無厲害論”,就意味著他將藝術(shù)變得無足輕重的目的達(dá)到了。至此可以看出,康德主張的所謂“無利害性”的對待藝術(shù)作品的態(tài)度,意在將藝術(shù)與真實(shí)生活間造成一種審美距離,削弱藝術(shù)對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影響。康德同樣藝術(shù)定義為“沒有任何明確目的的目的性”的事物,從這個(gè)角度出發(fā),削弱了藝術(shù)的哲學(xué)意義,使藝術(shù)無意義化,在邏輯上也等同于無利害性。“任何把它用作實(shí)際目的的行徑都有可能是一種誤用或者曲解。”康德最終的目的終于在此得到體現(xiàn),他所謂“藝術(shù)無利害性”實(shí)際上是一種迂回的態(tài)度,基于這個(gè)理論,藝術(shù)被徹底地中立化了,它既沒有實(shí)際的功用性,也遠(yuǎn)離了世俗利益與需求,甚至,連它帶給人的愉悅感受也只是一種淺表的、感官層面的愉悅。換言之,藝術(shù)與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一切都毫無關(guān)聯(lián),是一種架空的存在。
抱有類似觀點(diǎn)的還有喬治·桑塔耶納(George Santayana),從美的角度思考藝術(shù);布洛(E. Bullough)把藝術(shù)看成是審美距離的結(jié)果,另外一些哲學(xué)家則稱之為一種無利害性的觀照(斯托爾尼茨)或非中轉(zhuǎn)的感知(intransitive perception)(維瓦斯),即不從理由出發(fā)觀看一個(gè)對象。
三、黑格爾“藝術(shù)哲學(xué)取代論”
黑格爾的“藝術(shù)哲學(xué)取代論”直接對藝術(shù)下了最后的審判,“對于黑格爾來說……歷史終結(jié)于絕對精神意識到自己作為絕對精神的身份之時(shí),它不再因?yàn)檎`解自身的本質(zhì)而異在于自身,而是通過自身從而最終統(tǒng)一于自身:也就是說,通過認(rèn)識到在這里,主體和它的對象具有同一種本質(zhì),因?yàn)閷σ庾R的意識仍然不外乎是意識。”藝術(shù)“自身的本質(zhì)”,在黑格爾看來,僅僅是絕對精神發(fā)展的一個(gè)階段,藝術(shù)在逐漸發(fā)展的過程中必然會過渡到宗教,最后讓位給哲學(xué)。當(dāng)然,藝術(shù)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僅僅為了能順利的過渡到宗教和哲學(xué)階段,而完成這一使命之后,便沒有給予藝術(shù)關(guān)注的必要了。
當(dāng)代的現(xiàn)成品藝術(shù)的出現(xiàn)似乎是對黑格爾藝術(shù)觀點(diǎn)的一次證實(shí)。馬賽爾·杜尚(Marcel Duchanp)的作品《泉》(Fountain)是件看似如何都與藝術(shù)不搭邊的作品,而它恰如其分地從其內(nèi)部提出了哲學(xué)相關(guān)性的問題,從這個(gè)層面上看,藝術(shù)似乎已經(jīng)成為了“形式鮮活的哲學(xué)”。
四、亞瑟·丹托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
丹托《藝術(shù)的終結(jié)》的英文原名為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chisement of Art,直接翻譯過來為《哲學(xué)對藝術(shù)權(quán)能的剝奪》,這么翻譯也許的確不如《藝術(shù)的終結(jié)》來的引人注目,但卻是最確切的。
第五章《藝術(shù)的終結(jié)》系統(tǒng)闡述了丹托的理論觀點(diǎn),開頭引用了馬里于斯·德·薩亞斯在1912年在 《攝影》7月號發(fā)表的一篇題為《日落》的文字“藝術(shù)死了。他現(xiàn)有的運(yùn)動絕非生命力的征兆;他們也不是死前痛苦的掙扎;他們是尸體遭受電擊時(shí)的機(jī)械反應(yīng)。”藝術(shù)真的死了嗎?亞瑟·丹托提出的藝術(shù)終結(jié)論似乎直接給藝術(shù)下了“最后的審判”,但是丹托的“藝術(shù)終結(jié)”指的不是藝術(shù)走到這里已經(jīng)窮途末路了,相反的,藝術(shù)舍去了一直以來為哲學(xué)回答問題的重?fù)?dān),藝術(shù)自由了。
丹托藝術(shù)終結(jié)論的核心實(shí)質(zhì)是論證了哲學(xué)與藝術(shù)的分離,而非“哲學(xué)取代藝術(shù)”。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人文科學(xué)系李軍教授對丹托的理論具有相當(dāng)?shù)膮⒖家饬x,文章中他指出黑格爾藝術(shù)哲學(xué)理論與丹托理論的本質(zhì)區(qū)別:“……也是在這里,存在著但托與‘藝術(shù)的終結(jié)始作俑者黑格爾的根本差別。根據(jù)黑格爾……藝術(shù)階段的目的在于使宗教和哲學(xué)階段最終成為可能;換言之,藝術(shù)在達(dá)成目標(biāo)之后便被絕對精神棄如敝屣,不再引起黑格爾的注意。而在但托那里,使哲學(xué)成為可能的藝術(shù)是一種應(yīng)該終結(jié)的藝術(shù)—‘歷史時(shí)代的藝術(shù)。”將丹托的藝術(shù)觀點(diǎn)與古典哲學(xué)中的觀點(diǎn)作比較分析,便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丹托的觀點(diǎn)則恰恰是與黑格爾等的觀點(diǎn)不盡相同,丹托認(rèn)為,在經(jīng)歷過嬗變之后被終結(jié)的是一種“歷史時(shí)代的藝術(shù)”,即線性發(fā)展的,進(jìn)步的藝術(shù),這是一種“宏大敘事模式”的終結(jié),這與黑格爾消極的藝術(shù)觀點(diǎn)實(shí)則大相徑庭。藝術(shù)的終結(jié)是一種帶有積極意義的終結(jié),預(yù)示著“后歷史時(shí)期的藝術(shù)”的開始。
在丹托藝術(shù)終結(jié)論發(fā)表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很有幸地看到藝術(shù)非但沒有終結(jié),而且發(fā)展出了更加廣泛多元的形態(tài),這是藝術(shù)世界的成功,也是現(xiàn)代藝術(shù)史體制的成功。
參考文獻(xiàn):
[1]沈語冰.20世紀(jì)藝術(shù)批評[M].浙江:中國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2003.
[2]劉悅笛.藝術(shù)終結(jié)之后——藝術(shù)綿延的美學(xué)之思[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3]彭鋒.西方美學(xué)與藝術(shù)[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
[4][美]亞瑟·C·丹托.藝術(shù)的終結(jié)[M].歐陽英,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2001.
[5]李軍.被扭曲的丹托—對“藝術(shù)終結(jié)論”的一項(xiàng)必要的事實(shí)陳述[J].藝術(shù)設(shè)計(jì)研究,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