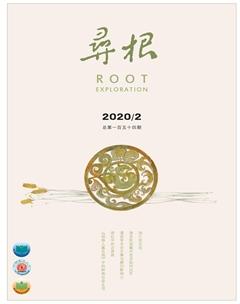消亡的天花
周巖壁
在20世紀,天花峰回路轉,實現了“歷史的終結”。1967年,世界衛生組織發起消滅天花的運動。1977年,最后一例自然發生的天花患者,在索馬里出現。1980年,世界衛生大會正式宣布:天花被完全消滅,天花病毒在自然界已不存在,只有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實驗室中保存有天花病毒,以備意外之需。
我們以天花在河南省的情況為例。1958年,郾城發現河南最后一例天花病人。1962年后,河南按免疫程序進行劃片種牛痘,預防天花。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天花消滅后,河南停止使用牛痘疫苗。(《河南大辭典》,新華出版社,1991年,第712頁)就是說,天花已成為第一種也是至今唯一被消滅的瘟疫。
一
《紅樓夢》第二十一回寫巧姐出天花,請大夫來診治。大夫說是出痘疹,即天花,要鳳姐預備桑蟲、豬尾。“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凈室款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鳳姐與平兒都隨著王夫人日日供奉痘疹娘娘。”十二日后,巧姐病愈,毒盡斑回,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
《紅樓夢》的描繪非常寫實,這也是舊時治天花的常規做法。對于家庭來說,出天花,是非常嚴重的事情,生死攸關,需要小心翼翼,鄭重對待。為什么?我們查一下歷史,在種痘法推廣之前,也就是19世紀前,西方世界大約60%的人口受天花威脅,出天花者的死亡率是10%,主要是兒童。(霍華德·馬凱爾:《瘟疫的故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4、77頁)中國情狀與西方世界仿佛。畢竟天花已遠離,自“80后”一代起,連預防天花的牛痘都不曾種。所以,對《紅樓夢》中巧姐出天花的描述,大都相當隔膜。這需要我們耐心對上引的那一段略加解說。大夫要鳳姐預備“桑蟲、豬尾”,這是天花病人常用的兩味藥。桑蟲,即桑蠹蟲,樣子像蠶蛹,寄生于桑,絞汁和白酒釀服,治痘瘡毒盛。豬尾,實指豬尾血,調龍腦(熱帶產的一種樹膠,可做香料)少許,新汲水服,治痘瘡倒靨——“倒靨”是行話,指天花將結痂時候。
關于痘疹娘娘,則是民間淫祀,有巫術成分。大約和曹雪芹同時的李汝珍,在《鏡花緣》第五十五回告訴我們:世間小兒出天花,皆痘疹娘娘掌管,男有痘兒哥哥,女有痘兒姐姐,全仗其照應,方保平安;痘疹娘娘一般供在尼庵里。大概賈府權勢浩大,痘疹娘娘很識趣,不避趨炎附勢的嫌疑,屈尊到賈府來接受供養了。
出天花時候,醫生交代的注意事項非常多:嚴冬多設炭火,盛暑多置冰水,務使室中寒暖和勻,臥處最要無風,通明忌暗,常令親人看守,夜中燈火莫離。慎帷幕,潔被服,除穢氣。忌觸油漆氣,忌吹滅燈燭氣,忌腦麝諸香氣,忌韭蒜糞穢諸濁氣,忌魚腥煎炒諸油氣,忌聞哭泣、罵詈、呼怒、歌樂及鑼鈸金器之聲,忌洗面,忌生水入瘡,等等。這些都是經驗之談,正和鳳姐的“四面”——上引文字中曹雪芹用了四個“一面”——忙亂鐘磬相應。我們再看舒白香回憶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3歲出天花的事兒:祖父請名痘醫孫谷留家不肯放歸。刺雞冠,割羊尾,搓桑蠶,皆祖父母親手安排,迨毒食足而痘見點。迨灌漿,癢而要搔,母親日夕不眠而管視予手。卒至于麻,亦天數也。(轉引自周作人:《兒時的回憶》)
在細節上與賈府的規矩不盡相同,卻都是慎而又慎。就這,百密一疏,舒白香撓癢抓破臉上的痘痂,成了麻子臉!好在是個男人,倒也不怕。女人麻臉就一定可怕嗎?也未必。《金瓶梅》里西門大官人的第五房姨太太孟玉樓,不就因為臉上有幾顆“白麻子”,增了幾分嫵媚嗎?何況,麻臉而生,總比夭折強吧。
關于天花的傳統觀念,我們總結一下:天花,一名天瘡,言為天行疫癘;又名百歲瘡,言自少至老,必患一次;又曰痘,豌豆瘡,以其形似豌豆。病原胎毒而起,至于天行傳染時益甚。剛開始,寒熱三日,發紅斑,俗名現點。初發于頭面,漸及肌體,三日成水泡,俗名齊苗。水泡內容物混濁,為乳性膿性。三日,中央現臍,俗名灌漿。又三日,膿泡干燥,成痂發癢,俗名上岸。痂脫乃愈。為時十二天。
二
巧姐和舒白香,他們出天花,都是因為沒有種痘。我們再看一下19世紀末紹興周家的三個孩子。周作人和他妹子幼年沒種痘,同時出天花,周作人幸而挺了過來,幼妹卻因此夭折。這是1888年,周作人3歲,妹子未滿周歲。(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他們的大哥周樹人,就幸運得多,3歲時父親請醫生來給他種牛痘。魯迅回憶說,當時還有個種痘儀式,“堂屋中央擺一張方桌,系上紅桌幃,還點了香和蠟燭,父親抱了我坐在桌旁邊”。(魯迅:《我的種痘》)這是在1884年。魯迅種的是洋痘,他沒有具體說是怎么種的。根據1935年版《中華大字典》的相關內容,大概是:“以刀刺小兒臂,以牛之血清納之,數日后,痘由刺處而出,俗稱挑苗。”
18世紀末,Benjamin Jesty根據一般人的觀念,認為患有輕微牛痘的擠奶姑娘不會感染天花。英國柏克利鄉間醫生Edward Jenner用科學方法研究這個問題,發明或者說改良了種痘方法:將病毒放入小牛體內,待其作用減弱時,再把痘漿注射于人體,從而使人減輕或完全避免這種疾病的危害。(W.C.丹皮爾:《科學史》,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360頁)這種種牛痘的方法,大概是隨著傳教士進入中國的。
在宋代,我們也有自己的種痘法,就是把痘痂研成細末,給孩子由鼻孔吸進去。據魯迅說,“痘疹發出的地方沒有一定的處所,但粒數很少,沒有危險”。關于土法種痘的效果,似乎很完美。但我們對魯迅的話,也不可全信。如果真是這樣,他的父親何必費事給3歲的魯迅種牛痘?這就是說,魯迅的父親已經知道土法種痘不如洋法——牛痘!1798年,接種牛痘的方法出現,而且非常有效,但它并沒有在世界各地得到大力推廣和普及。
天花是舊世界(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一種傳染病,據說公元前1122年——周武王伐紂時候——中國文獻里對它已有描述。(《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15卷,第422頁)唐代醫書《外臺秘要方》卷三“天行發瘡豌豆皰瘡方”十三首,羅列的就是十三種治療天花的藥方。天花雖然危害很大,是西方17、18世紀最嚴重的瘟疫,但天花在歷史上的影響,比不上14世紀的黑死病,主要可能是因為受害者以兒童為主,生過此病后,成年人大多已有免疫力。
但是當歐洲殖民者在15世紀末登上新大陸,情況就不同了。殖民者給美洲原住民帶去了多種前所未有因而不具有任何免疫力的傳染病,其中最致命的一種就是天花。科斯特率領300多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夠征服2500萬人口的阿茲特克帝國,用的秘密武器就是天花:阿茲特克人俘虜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有天花,由此傳染給土著!10年后,阿茲特克人口減少到650萬人,生存者一蹶不振,一個強大的帝國從此消失。另一個強大帝國——印加帝國(今秘魯及周邊國家),也因為天花流行而被皮薩羅帶領的180名西班牙殖民者輕而易舉地征服。北美殖民者有意將天花傳給印第安人,給他們送去天花患者用過的毯子。在天花肆虐下,幾個原先有數百萬人口的印第安部落減少到只有數千人或滅絕。在與殖民者接觸之前,美洲原住民有兩三千萬,到16世紀末,只剩下100萬人。殖民者卻自命不凡,得意忘形:印第安人像“腐爛的羊一樣”死于天花,“憑著非凡的美德和上帝的保佑,我們沒有一個人染上這種疾病”!(霍華德·馬凱爾:《瘟疫的故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78、84頁)
作者單位:鄭州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