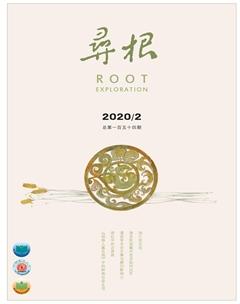科名有定數:明清南京的科舉敘事
孟義昭
科名有定數,是明清南京較為盛行的一種科舉敘事,科名占卜、科第征兆、科場果報,是其三種主要書寫形式。
科名占卜
科名占卜,多種多樣。根據占卜方式,有測字、扶乩、求簽、文章占卜等;占卜主體,有自行占卜和請人占卜;占卜者身份,有官員、士人、職業占卜者等區別。明清南京城內,科名占卜類型多樣,風氣十分興盛。
嘉靖、隆慶年間,南京有一讀書人崔自均,是狀元焦的親戚。顧起元《客座贅語》中,收錄其科名占卜之事兩則。其中一則為:“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后方置諸首也。”此處“焦鏡川大尹”,指曾任靈山知縣的焦瑞,當時焦瑞為應天府學生員,參加歲試時所中名次應驗,證實崔自均占卜科舉之事的高明。另一則是:顧起元之父參加隆慶四年(1570年)應天鄉試后,赴崔自均宅問卜。剛入其門,崔自均說:“得毋為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已得公數矣。必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后耳。”榜發,顧起元之父得中第130名舉人。查《隆慶四年應天府鄉試錄》,第130名舉人為張國輔。此處張國輔,即顧起元之父顧國輔。顧國輔之祖父,曾過繼至張姓人家,因而姓張。國輔中進士后進入仕途,請求恢復本姓,得到朝廷批準,更名顧國輔。顧國輔中舉之事,更印證崔自均占卜科舉之神。
嘉靖年間南京城內盛行科名占卜之風,甚至連負責學校與科舉事務的南直隸提督學政楊宜也不例外。關于楊宜主持應天府歲科兩試時閱文知人、以文卜運的事跡,《客座贅語》錄有兩則:
嘗試應天,見李種卷,拔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揪斂,似胸中有悲苦事。”種對曰:“赴試時,適喪偶。”
考童生,首取趙衢,以其廛無夫里之布、文獨諳典則故。后再試,閱其卷,對之顰蹙曰:“汝筆何甚蹇滯,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趙后僅廩于庠,卒奪糈,壹郁以死。
楊宜占卜科舉之神不僅在南京廣為人知,而且流傳江南一帶。文人學士多口耳相傳其軼事軼聞,表達對其敬佩之情。萬歷年間,房寰任南直隸提督學政時,舉楊宜為名宦,祀于學宮。
至清代,南京城內科舉占卜之風依然不減。袁枚《子不語》載有“徐步蟾宮”的故事:
揚州吳竹屏臬使,丁卯秋闈,在金陵扶乩,問中否,乩批“徐步蟾宮”四字。吳大喜,以為館選之征,及榜發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文中“吳竹屏臬使”,當指江西按察使吳之黼。乾隆十二年(1747年),吳之黼在南京參加江南鄉試,扶乩卜科舉之運,自以為必中,未曾想以落第而歸。扶乩所示“徐步蟾宮”四字,竟為徐步蟾摘得該科江南鄉試解元之兆。
清代南京求簽問科名之風較盛,而關帝廟是士子參加江南鄉試前常去的祈簽場所。南京城內關帝廟數量眾多,分官方致祭和民間致祭兩種。城內所有關帝廟中,以城北十廟中的關帝廟最為有名,規模最為壯麗,俗稱武夫子廟,與府學文廟相配,總督以下皆致祭于此。此外,官方致祭者還有小教場廟、駐防城廟、督署箭道廟、小倉山廟、府西大街廟、江寧縣署廟等。民間致祭者為數更多,如城西南吳家園、內橋北大街、安品街、普利寺之西、致和街河沿、鷲峰寺之西、聚寶門外、雨花臺旁、五圣巷內、安德門、鳳臺門、上方門、孝陵衛岡、觀音門、燕子磯等處,皆有關帝廟。當時赴關帝廟祈簽者,主要分為禱簽求醫和求簽問科名兩類,其中以求簽問科名最為常見。
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戊寅恩科江南鄉試在南京舉行,主考官為帥承瀛、盧炳濤。金鎮在入闈之前,赴關帝廟求簽問科名,簽云:“水到渠成聽自然。”金鎮三場座號字皆從水,頗為詫異。榜發,金鎮果然中舉。其房考官為贛榆知縣何恒鍵,字蘭汀,也從水。甘熙在《白下瑣言》中論及此事:“科名遇合,莫非前定者。”
江寧府署前關帝廟簽極其靈驗,南京城內赴此求簽者眾多。道光五年、十七年,甘熙兩次赴府署前關帝廟求簽問科名,其《白下瑣言》載:
乙酉七月朔,予曾以鄉試中否往禱,得簽云:“曩時敗北且圖南,筋力雖衰尚一堪。欲問君身前大數,前三三與后三三。”是科薦而不售,殊覺茫然,乃遲至丁酉科始中式。頭場次題“禮儀三百”二句,《禮記》題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方悟前后三三之語,早示于十二載以前矣。是年臘月,將計偕北上,復虔禱焉。簽云:“君家兄弟好名聲,只管謙莫自矜。丹詔槐黃相逼近,巍巍科甲兩同登。”語固上吉,而非兄弟偕應禮闈,正不可解。及戊戌會榜發,與表弟葉賡廷聲揚同登,并同出十一房涇陽張小圃先生門,乃晤簽詩首句,正指中表兄弟名聲者也。神明烏可測哉!
科第征兆
在科第征兆中,往往有吉兇之分。明清南京所傳科第征兆,以吉兆居多,并多與睡夢有關。夢中吉兆,是當時南京科第征兆的一個特點。
嘉靖十年(1531年)應天鄉試榜發,中式舉人有朱曰藩、呂潛二人。李詡《戒庵老人漫筆》記載關于兩人的科第吉兆:
辛卯科新中舉人寶應朱曰藩,升之之子也。增廣生考入試,來時夢至京,提學補廩,意謂不中之兆。是年中式,小錄誤刊學生補廩,應矣,乃神妙如此。
長洲縣呂潛亦中于是科,揭曉后,見本房考試官對眾言:有鬼神,謂呂初在備卷,已取之,卷封將送入矣。倦睡,夢一鬼扯起看卷,謂已取定無可看者。復睡去,鬼復來扯,驚異而起,乃試看,備卷之首即呂也。覺文字可取,無能為計,當送取卷,因攜此卷呈主考,兼道夢中之事。主考亦稱善,遂取之,而退所取數中一卷以填之。信非人為也。
萬歷七年(1579年)秋,正值應天鄉試舉行之際,顧起元祖父夢中遇一人對其說:“今科報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榜發,其祖父逐名對照,并無果驗。次年冬天,其祖父去世。萬歷十年(1582年),壬午科應天鄉試榜發,應天府學中式者恰為三人。這三名舉人家宅地址與顧起元祖父夢中之兆完全相符。第6名沈天啟,住剪子巷;第12名黃夢麒,住上新河;第14名張文暉,住北門橋。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感嘆:“夢之奇中如此,且逾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測也。”
上元人胡任輿,少時曾夢登高山,手摘香櫞兩顆,作詩記之,其中有“手弄雙丸天下小”之句。胡任輿參加康熙二十年(1681年)江南鄉試,得中解元,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殿試,又高中狀元。李調元認為,胡任輿奪得大魁,正驗證其少時夢中吉兆。錢泳《履園叢話》也載此事:
朱竹垞檢討于康熙辛酉主試江南,拔胡任輿領解。初,胡夢有人授以詩,有“手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甲戌會試,題為“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章。試后,謁其房師趙恒夫于寄園,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對果第一。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江南鄉試揭曉前夕,林端之父夢同里老友林蔚青、端木煜、翁恩元三人造訪其家,敘談半晌而去。榜發,林端高中該科鄉試解元,方知夢中三人之姓名為林端中解元之吉兆。此事載于甘熙《白下瑣言》,但林端中解元實有隱情。甘熙說:“丙子鄉試,林解元端納卷最早。其房師周次立大令以勛,中秋得之即薦元。數日后批回,竟未獲雋。及八月杪,前魁已定,獨無元卷。主司上堂以語眾,同考周君聞之,出位曰:‘昨得一卷,其文氣息甚高,然恐太遲,不敢薦耳。主司急索觀。乃以濃藍汁涂蓋墨跡,復用‘包掃一切四字改其前批呈上。主司閱未終篇,擊節嘆賞,遂取冠多士。南闈佳卷本多,閱者易目迷五色,此無足怪。而周君之愛才如命,洵相賞有真矣。”
除夢中所見科第吉兆,明清南京文人還將祥瑞之物視作科第吉兆,如金蟾、并蒂花等。
遇見金蟾,是士子中第吉兆,顧起元在《客座贅語》里講述了一個相關故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值應天鄉試舉行之年。當年春天,顧起元內兄王肖征赴朝天宮,行至城內九曲街時,見一乞丐臥于地上,其飯籮中盛有一大蛤蟆,蛤蟆有三足。王肖征當時深感迷惑,行至數十步開外始想起三足蛤蟆即為金蟾。驚訝之余,王肖征“亟回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當年鄉試榜發后,王肖征果然榮登賢書。查《南國賢書》所載嘉靖三十四年應天鄉試舉人名錄,第45名舉人為王肖征,可以證明顧起元所說關于王肖征的基本信息是可信的。
并蒂花開,也是士子的科第吉兆,而這種情況又多以蘭花、蓮花等較具文人雅士氣質的敘事花種出現。甘熙在《白下瑣言》一書中,錄入了兩個相關事例。
嘉慶十八年(1813年)春,甘福府邸蘭花盛開,叢中有并蒂一枝,花莖色赤如丹砂。當年,甘福二子甘煦、甘熙皆通過院試,入泮讀書,成為官學生員。時人認為并蒂蘭花為科舉瑞應,令兄弟二人在花前結彩以示謝意。甘福之友中,有人作詩稱賀:“天教蘭卉現嘉祥,并蒂連枝王者香。會見朱衣齊點首,宮袍對舞鳳池旁。”
嘉慶二十一年,并蒂花開作吉兆之事再次發生。當年正月,孫星衍赴任鐘山書院院長。六月,孫星衍所居冶城山館蓮花并蒂開放,色紅,其大如盞。書院月課,舉《并蒂蓮賦》,以“瑞不虛呈,修德應之”為韻。孫星衍之父當年正壽值八旬,在江南鄉試后重宴鹿鳴。甘熙認為,其師冶城山館并蒂蓮花之事與三年前甘府并蒂蘭花一樣,是祥瑞之征兆。
與科第吉兆相比,不祥之兆在南京文人敘事中尚不多見。但在明中期文人的科舉敘事中,南京也出現兩例科第兇兆。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應天鄉試,沈九思得中舉人。九思赴北京參加會試,其父早起送行,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夭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恐懼之下,二人潛藏在道旁屋檐下,等龍行過方出,時皆以為科第吉兆。不久,沈九思卒于北京。顧起元參考《占候書》及他人著述,得出結論:龍與其他水族蛇虺之屬一樣,凡出行遇之,皆為不吉之兆。
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應天鄉試舉行前,南京貢院開展修葺工程,有魚見于圊中,識者怪之。貢院中出現的這一現象,被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視為科場兇兆:
至第二場,忽于供給所搜得透印無名試卷數通。監試、提調大驚,拷掠左右甚苦,終不得其故,遂將私貯試卷之人斃之杖下,而不敢聞之朝,懼株連者眾也。次年元旦大朝會,時覲吏與試士俱集大廷,忽眾中有人持大鐵錐狙擊御史凌漢于班行,碎其首,仆地僵絕,舉朝大驚,急擒下,則故巡捕提督都督同知凌應登也。御史為從者舁至寓復蘇,用良藥敷治,僅得不死。是日相顧錯愕,謂今年必有異變。至二月會試,遂有假元一事,假元則去秋應天所舉也。魚有龍門飛躍之兆,而屈居溷穢,已屬奇妖,至于獬豸觸邪,反遭朱亥之厄,其事又發于辰年元會,兼有群龍無首之象。變不虛生,信然哉!
科場果報
果報之說,大體上可分為種德善報和作孽惡報兩種。明清南京科場果報之說較為流行,也可分作上述兩類。
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記錄一則“鼠拖卷”的故事,是明代南京科場果報說里種德善報的典型。嘉靖十九年(1540年)應天鄉試,第83名中式舉人為顏芳。揭榜前,其鄉試朱卷已被房考官抹擲案下,忽然又在案上,再擲去,轉而又混雜于所取卷中。房考官驚訝之余,再將其朱卷擲于地,并在榻上假寐以觀其緣故,竟然看到群鼠共抱其卷,自地拖至案上。房考官認為不可有違天意,因取以中式。撤棘后,房考官詢問顏芳:“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為拖卷若此?”顏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顧起元曾將此故事說與賓客,客笑曰:“物莫小于蟻,宋公序一為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于鼠,顏嗣桂三世不畜貓,而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為,豈不信哉!”顧起元進而感嘆:“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為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報于場屋,天之于鼠子何若是重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夫。”查《嘉靖十九年應天府鄉試錄》,第83名舉人為顏芳,應天府學增廣生員。顏芳確有其人,其科舉信息皆如顧起元所言,但“鼠拖卷”之事太過離奇,應當是顧起元精心加工的結果。
袁枚《續子不語》一書中也載有“鼠薦卷”的故事,基本上是顧起元《客座贅語》“鼠拖卷”故事的翻版,不過是考官變成了“繁昌令黃公”,考生變成了“閔某”,故事情節乃至“三世不蓄貓”的細節,也均相同,顯然是袁枚據《客座贅語》所載內容改編而成。顧起元《客座贅語》所載“鼠拖卷”故事影響之大,由此也可見一斑。
由于科舉的巨大吸引力,文人學士將科場果報之說加工豐滿,借科場的招牌招徠觀眾、聽眾,從而輸出其個人理念。這種敘事方式,在明代歷史上是較為典型的。顧起元敘述“鼠拖卷”的故事,表達出其“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態觀,在當時是十分難得的。
清代南京城內,種德善報的科場果報之說仍盛行不衰,最典型者莫如狀元胡任輿的故事。劉獻廷《廣陽雜記》載:
江南上元之胡氏,世有厚德。鼎革后,南京舊家仍守故宅者,惟胡氏耳。殿元之祖,字復之,每于除夜置酒,男女分坐,諸家人男婦亦下坐于兩旁,必舉杯訓其子曰:“吾徒讀書人何所能?經營家計,得以溫飽者,(指諸奴曰)皆若輩力也,當善視之。”江南人咸目為長者。其長子禹冀,字□贊,領鄉薦。任輿,江南解元,今又大魁天下。人以為積善之報。胡氏祖以打金箔為業,至今人猶稱之為“胡金箔”焉。
在南京乃至江南人看來,以打金箔為業的胡氏之所以能先出一個舉人,后中一個狀元,與其“世有厚德”密切相關。正是因為胡氏世代積德行善,胡任輿才連中解元、狀元,積善之報理所當然。
《子不語》一書,收錄一則“碌碡作怪”的故事:
常州武生某,素有力,往金陵鄉試,路過龍潭,見一婦坐門首,因口渴,向其索茶。婦以生不分男女,大罵,閉門進去。生思不與茶則已,何至詈罵,氣甚不平。見其田中臥碌碡一條,即用力擎起,架于樹上而去。明日婦開門見之,詢鄰人,皆曰:“此物非數人不能動,莫非樹神所為乎?”因朝夕敬禮,有求必應。或侮慢之,即有不利。如是者月余,生試畢歸家,仍過其地,見所置碌碡尚在樹間,其下香火羅列,禳禱者紛紛,心知為己所誤,笑而不言。是晚,宿店中,思此事終是惑眾,必轉去說明方好。忽朦朧睡去,見有人告曰:“我某處鬼也。游魂到此,假托樹神以圖血食。君新科貴人,故不敢隱瞞。若肯見容不說破,感恩非淺。”言畢不見。生遂不轉去,徑回常州。是科榜發,果中舉人。
武生某未說破鬼之行徑,對其有恩,受其善報,中式舉人。這一故事圍繞常州某武姓生員赴南京參加江南武鄉試展開,是為數不多的關于江南武鄉試的科場果報傳說。
在南京科場果報之說中,不僅有種德得報之說,更有作孽惡報之例。
道光五年,乙酉科江南鄉試舉行。寒字號一考生,自書文字于號板:“冤家已到,速速自裁。我死得好苦,惟其如此,所以如此,早知如此,悔不如此。”書畢,交白卷而出。堅字號一考生自言:“被披發鬼擊其背,欲帶赴城隍聽審。”神癡色變,僅寫破、承,不能握筆,遂被扶出。后來才知此人為老槍手,并善工刀筆。另一考生在卷上書寫:“趙錢孫李……哪有許多趙錢孫李?還有一百二十個趙錢孫李。”除此之外,該科闈中還出現其他數例類似事件,當事者均被貼出。對于此事,甘熙在《白下瑣言》中說其曾目擊,并認為這是科場報應。
不僅應考士子,南闈考官當中也有遭受惡報之例。全椒知縣凱音布,曾在乾隆三十三年、三十五年先后兩次赴南京擔任江南鄉試同考官。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凱音布第二次擔任江南鄉試同考官,疽發于背,死于闈中。《子不語》載:
庚寅分校南闈,疽發背卒。公母懷孕時,將至期,祖某為內務府總管,晚見庭下有巨人,長過屋脊。叱之,漸縮小,每叱一聲,輒短數尺,拔劍追之,化作短人,奔樹下而滅。取火燭之,乃一土偶人,長尺許,面扁闊,聳右肩,左手少一小指。因拾置幾上,而婢報某娘子房生一男矣。三日后,抱視之,左手少一小指,狀貌酷肖土偶。舉家大驚,乃取土偶供祖廟中,禮事甚虔。及凱卒后,送神主入廟,見土偶為屋漏故,雨滴其背,穿成三孔,仆于坐上。凱死時,背瘡三孔皆穿。家人悔奉祀不虔,已無及矣。
奉祀不虔,致使凱音布死于闈中。袁枚與凱音布交好,關系十分友善。而在《子不語》中,袁枚虛構出這樣一個離奇的故事,無疑是受到科場果報之說的影響,將凱音布卒于南闈之中的原因進行神化,納入科場果報說的敘事邏輯之中。
余? 論
科名有定數是明清南京文人的一種科舉敘事,其主要思想是:科名自有定數,前生已定,此生難改;若要更改科名定數,必須付出慘重代價,甚至是壽算。
袁枚親家曾講述“史宮詹改命”之事,后被袁枚載入《子不語》中,茲錄于下:
溧陽宮詹史胄斯未遇時,赴省鄉試,遇南門外湯道士,談命甚精,因以年庚求為推算。道士曰:“照丑時算,你終身只一諸生,壽可八十三歲;若照寅時算,便可官登三品,今科便中。汝丑時乎?寅時乎?”曰:“丑時也。”曰:“若然,則今科不中矣。”史愴然不樂。道人曰:“命可改也,但陰司壽算最重,君如肯減壽三十年,當為君改作寅時。”史公欣然愿改。道士曰:“果情愿者,明日早來。”次夜,史五鼓熏沐到寺,道士已啟戶待,曰:“子誠信人,但日后官尊壽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燭對天自陳。道士披發仗劍,口中喃喃誦咒,良久,另書一庚帖與之。史公持歸,置篋中,果于是年鄉會聯捷,官至宮詹。五十二歲,希圖降級永年,而任內總無過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至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偶染微疾,上命太醫往視,為藥所誤,竟不起矣。
文中“宮詹史胄斯”當指史貽直之父史夔,官至詹事府詹事。康熙二十年(1681年),史夔赴南京參加江南鄉試,中式舉人,次年殿試,二甲第一,賜進士出身。按《子不語》所載,史夔在南京城南門外遇見湯道士,為了考取功名,情愿減壽30年更改年庚,最后改命成功,考中進士。
盡管史夔改命之事似與當今社會科學觀念有明顯的沖突,但其所涉及的相關基本信息,如史夔的字、科名、官職、壽數等,大體上是準確無誤的。在當時的社會觀念下,史夔改命顯然是合情合理的,并為世人所接受,這對于研究當時文人的科舉敘事是一個絕好的案例。至于改命之事真實與否,并不十分重要。
[本文系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項目“明清科舉考試與南京城市發展研究”(AHSKF2018D7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