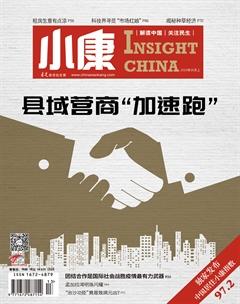“治沙功臣”帶來的“地方病”
郭煦

始料未及 沒有人料到,對治沙植物的過度敏感,已經危及一部分社會群體的健康,圖為內蒙古地區長勢旺盛的沙蒿。
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民李奧博自8年前患上過敏性鼻炎后,病情一年比一年嚴重。2019年12月,他有一半時間都是在醫院度過的。
“剛開始只是打噴嚏流鼻涕,眼睛耳朵癢,頭痛,嚴重時會連續打幾十個噴嚏。晚上躺著睡覺經常會被憋醒,我只能坐在沙發上睡,真的是痛不欲生。”李奧博邊說邊打哈欠,并用紙巾擦拭不斷流出的鼻涕,“我的過敏源早就確定了,蒿類花粉是主因,醫院呼吸科現在人滿為患,大部分患者病情跟我一樣,醫生告訴我這病只能緩解,無法根治。”
李奧博說,他是2011年從北京來鄂爾多斯工作的,一直沒有鼻炎,來到這里的第二年鼻子就開始不舒服,而且越來越嚴重,去醫院一查是得上了過敏性鼻炎,問了大夫是內蒙古當地的植物沙蒿引起的,這些年里,內蒙古鄂爾多斯每到6—9月,他的鼻子就開始不通氣、流鼻涕。聞到刺激性的味道時,就忍不住連打噴嚏,鼻涕眼淚直流。
“來這里時孩子才2歲,漸漸地孩子也開始出現過敏情況,我的妻子也得了鼻炎,她們倒是沒有我的嚴重,但是到了每年的患病季節也會出現打噴嚏、流鼻涕的癥狀,而且每天都休息不好。現在鼻炎在當地年輕人中很普遍,單位像我這樣癥狀的同事也不少,有的比我還嚴重,也沒有什么特效藥,就只能每年患病了,買點藥頂一頂,也沒有其他辦法。”李奧博稱。
西北地區過敏性鼻炎發病率高
鄂爾多斯中醫院一位呼吸科醫生表示,過敏性鼻炎現已成為內蒙古西部地區的“地方病”,患者人數逐年上升,目前醫學尚無徹底治愈的辦法。而當下最主要的過敏源,就是蒿類花粉。
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耳鼻喉科主任醫師李玲香表示,近年來,蒿類植物引發過敏性鼻炎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去年門診患者當中,八成以上都是過敏性鼻炎患者。這個病成因非常復雜,到現在也沒有確實有效的治療辦法。用長效激素效果比較好,但人們對激素普遍有抗拒心理,最好的辦法是遠離過敏源。”
陜西省榆林地區也是過敏性鼻炎的重災區,亦是沙蒿飛播較為集中的地區。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此前的統計資料顯示,榆林市沙蒿保存面積為328.5萬畝。沙蒿耐旱速生,種植成本低,于是成為西北地區治沙主力。為了抵擋風沙向大城市飄散,前些年開始推廣沙蒿飛播,治沙成績斐然,有些地方,不僅是郊外,就連市區的房頂上也長出了沙蒿。因此,每年的7月中下旬到9月,沙蒿花粉就會漫天飛舞。每年7—9月,榆林許多過敏性患者噴嚏不斷,鼻涕眼淚橫流,嚴重者還會引發過敏性哮喘,甚至有生命危險。榆林市各大醫院耳鼻喉科門診,就診量比平時增多。
有的重癥患者每年這個時候就放下手頭事務,一路南行。今年35歲的魏女士和孩子都患有過敏性鼻炎,娘倆做過相關治療,但收效甚微。“剛開始幾年還好,后來感覺越來越嚴重,從2016年開始,我們娘倆每年就前往西安暫住3個月。”魏女士苦笑著說,自己就像候鳥一樣,每年都會“遷徙”。
“最難受的時候頭痛欲裂,呼吸困難,不停地擤鼻涕。乘飛機離開榆林,飛機一升到高空,癥狀立即就緩解了……”榆林市民任曉華說,每年夏末秋初,過敏性鼻炎都讓他痛不欲生,只得放下手頭工作請假離開榆林。“患病的當地人比比皆是,外地人卻很少。”
2002年開始,就有榆林當地媒體報道沙蒿引起的過敏性鼻炎,當地衛生部門后來也承認,沙蒿可能是誘發過敏性鼻炎的一個因素。榆林市衛健委所做的《榆林市過敏性鼻炎流行病學調查》顯示:在榆林市抽查5901人,覆蓋人口廣泛,調查區域分別在城區和沙蒿種植區,患者整體比例為21%,城區則高達27.3%。
兩年前,陜西一家公益組織對沙蒿導致過敏性鼻炎的現象進行調研。調研發現,陜西北部及內蒙古、寧夏區域有大量過敏性鼻炎群體存在。該公益組織提出關注全國沙蒿過敏性鼻炎患者的建言,依法申請政府公開沙蒿過敏性鼻炎相關信息。
“我們想引起政府相關部門及全社會對沙蒿引起的過敏性鼻炎群體的關注。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相關數據印證我們調研的結論是否正確。我們先后多次向陜西、榆林、神木、寧夏、內蒙古各級政府提起行政復議。”該公益組織負責人陳麗娟說,國家衛健委、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陜西省衛計委、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榆林市衛計局均對此進行了回復。
其中,國家衛健委回復表示,尚未對“榆林、神木、內蒙古、寧夏等地區過敏性鼻炎、蒿類過敏性鼻炎、哮喘患者等三類人員的人數及就診人數”進行統計,因此,該公益組織申請的政府信息不存在。
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回復稱,為治理黃沙,榆林市實施飛播造林,主要采用種間混播的方式,其中沙蒿占總播種量的1/5。有關數據顯示,榆林市沙蒿保存面積328.5萬畝。為應對沙蒿引發的過敏,“十三五”以來,榆林全面停止人為種植沙蒿。
該公益組織此后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希望督促衛健委重視過敏性鼻炎對患者的危害。2018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此案,2018年11月8日,這場公益訴訟案件正式開庭審理。庭審中,國家衛健委認為其做出的《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原告訴訟請求。最終,該起公益訴訟以敗訴告終。
“這場公益訴訟的結局并不重要,我們不是去追究責任,也不是為了分出勝負。”該公益組織負責人陳麗娟表示,希望以此為契機,引起相關部門重視。
“治沙功臣”是元兇?
前不久,呼和浩特、鄂爾多斯、包頭等多地朋友圈、微博流傳這樣一條信息:整個內蒙古地區過敏性鼻炎的發病率呈逐年遞增的趨勢,而且越來越低齡化,其罪魁禍首就是蒿屬植物,望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及時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鄂爾多斯市林業和草原局《關于沙蒿引發鼻炎的情況說明》指出:“沙蒿”是黑沙蒿和白沙蒿的泛稱,為菊科蒿屬植物種,多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下的荒漠與半荒漠地區的流動與半流動沙丘或固定沙丘上,也生長在干草原與干旱的坡地上,在荒漠與半荒漠地區常組成植物群落的優勢種或主要伴生種。
鄂爾多斯從2000年開始,在庫布其沙漠和毛烏素沙地實施飛機播種造林,飛播造林主要目的樹種為大白檸條、楊柴、花棒和沙米。為飛播前期更好地固沙,也復合飛播白沙蒿,屬非目的飛播樹種。
近年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人們的生活節奏改變,生活和工作壓力加劇,加之食品的種類和制作工藝越來越多,致使許多原來不過敏的人可能逐漸演變成具有過敏體質的人,使潛在過敏人群不斷擴大。沙蒿過敏成為市民熱議話題,眾說紛紜。不少人反映7—9月,過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患者居多,均將致病根源指向本地野生植物沙蒿。但目前尚未有權威機構表明,沙蒿就是鄂爾多斯市過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患者的真正過敏源。
2017年,在《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第13次締約方大會高級別會議舉行期間,針對“過敏性鼻炎高發與防沙工程中固沙植物沙蒿相關”的說法,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副局長劉東生表示,截至目前,尚未有權威機構證明,沙蒿就是過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患者的真正過敏源。下一步,將與衛生等部門開展相關研究。
劉東生提到,沙蒿是我國防沙治沙的先鋒植物種,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沙區就開始大面積種植沙蒿,但那時候沙區群眾的過敏性鼻炎狀況并沒有現在那么嚴重。劉東生表示,下一步,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也將與衛生等相關部門合作,共同研究沙蒿與過敏性鼻炎是否有關系,或者有多大的相關關系。“如果有的話,將研究如何調整樹種結構進行治理。”
陳麗娟作為陜西省上述公益組織的負責人,從2017年開始帶領團隊著手調研沙蒿引發過敏性鼻炎這一課題。在對陜西北部及內蒙古、寧夏區域大量過敏性鼻炎群體進行調研后,大家都把目標鎖定在了沙蒿上。“每每聽到、看到過敏性鼻炎和過敏性哮喘患者每天承受的折磨,我的心情就異常沉重。”陳麗娟說。
讓陳麗娟感到欣喜的是,目前,國家林業和草原局開始收集全國沙蒿的相關信息;內蒙古等地的政府相關部門開始對過敏性鼻炎問題做調查;榆林市政府重視沙蒿引起過敏性鼻炎問題并準備重點治理……
“沙蒿曾是治沙的功臣,現在卻對人的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相關部門也逐漸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開始選擇替代植物來治沙。但沙蒿本身繁殖能力很強,治理起來非常麻煩,當務之急就是盡快研制出對應的治療藥物,最好是研究出阻斷花粉傳播的方法。”有關專家指出。
在榆林之外的鄂爾多斯和呼和浩特,關于當地過敏性鼻炎的討論帖每個夏天都會在貼吧大量出現,“鼻炎又犯了”是這些討論帖里重復率最高的句子。有前來北京就醫的呼和浩特患者向本刊記者表示,在他身邊“十個里有三四個都有過敏性鼻炎”。
上述過敏性鼻炎患者一致認為,是沙蒿導致了本地高發的過敏性鼻炎,“做過敏原測試都是蒿類植物過敏”。為了證明過敏性鼻炎與當地沙蒿的關系,他們曾深入榆林郊區的沙蒿地,摘下鼻罩親身測試過敏反應,結果大多數人“五分鐘就不行了”。
除了治療,患者更關心的是“以后怎么辦”。
沙蒿過敏應引起重視
《小康》雜志、中國小康網記者在榆林市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了解到,對近年來過敏性鼻炎季節性高發現象,榆林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成立了全市過敏性鼻炎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多次召開專題會議討論和部署全市過敏性鼻炎防治工作,組織專家赴北京、內蒙古等地考察,學習借鑒先進地區過敏性鼻炎防治經驗和做法,制定了《榆林市過敏性鼻炎防治工作方案》,并由市財政年度預算專項經費,用于購置過敏性鼻炎防治設備和開展課題研究。
“結合診療需求,在市第二醫院建立榆林市變態反應中心,設立變態反應科,并納入市級臨床重點專科培育項目,引進北京協和醫院等機構的全國知名專家來榆林市義診,每年7—9月定期在市二院坐診。” 榆林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相關負責人說,還在其他二級以上醫療機構掛靠內科、耳鼻喉科設置了變態反應(過敏)門診,也在高發季節開展宣傳和防治工作。
為更好地遏制過敏性鼻炎,榆林已全面停止人為種植沙蒿,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結合榆林市地理特征,在神木、定邊、綏德、榆陽四個縣設立“北、東、西、中”四個花粉暴片監測網點,動態收集分析花粉暴片“一線”數據。由北京協和醫院指導市疾控中心科學制定流調方案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工作,依托市第二醫院變態反應中心開展過敏性鼻炎基礎和臨床研究,繪制榆林市過敏性鼻炎患者過敏原譜,探索遏制過敏性有效治療手段。
“沙蒿引發的問題給我們深刻地上了一課,未來在治沙選擇上,我們已經充分考慮到植物多樣性和可能對居民生活產生影響的問題。”陜西榆林市林業和草原局相關負責人表示。
2019年兩會后,榆林市政府將“過敏性鼻炎防治工作”列入“十大民生實事”,政府撥款,完成過敏性鼻炎流調、專科建設、課題研究、花粉濃度監測與播報、人才培養、適宜技術推廣等工作。
多位醫生表示,過敏是遺傳與環境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按照“衛生假說”,隨著城市發展,衛生條件改善,人們生活在過于干凈的環境中,感染性疾病減少,就容易導致過敏性疾病增加。
尹佳在《過敏醫生赴榆林考察治沙植物紀實》中寫道:沙漠城市變成森林城市的同時,也進行著農耕文明生活方式向工業文明生活方式的跨越,或許這才是過敏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深層次原因。
治沙播綠改善生態,無疑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也是人類營造健康生活環境的必然選擇。但沒有人料到,對治沙植物的過度敏感,已經危及一部分社會群體的健康。沙漠要堅持治理下去,沙漠邊的居民也要健康地生活。如果治沙植物真的與人的健康發生沖突,那么這是不是西北地區當前出現的一個新的矛盾呢?近年來,西北地區多個城市確定建設生態名市,著力為當地百姓打造宜居城市,如何真真切切讓人宜居,令輝煌的治沙成果帶來的健康影響最小化,是擺在執政者面前的新課題。
如今,沙蒿引起的過敏性鼻炎患者越來越多,發病呈低齡化,發病范圍呈全國蔓延趨勢,沙蒿過敏已經成為公共衛生安全事件。
有關專家建議,面對如此嚴峻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國家衛健委應該重視起來,啟動過敏性鼻炎以及哮喘兩類疾病的統計調研工作,給出詳實的數據和病情調研結果,盡快拿出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