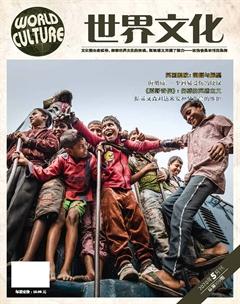晚清官員對日本的教育考察
賴某深
從1901年開始的清末新政,雖然在政治方面乏善可陳,在教育改革方面卻可圈可點:興學堂、鼓勵留學、廢除科舉,在中國教育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值得大書特書。
本文所介紹的,就是清末新政期間為了進行教育改革而派遣的赴日考察教育的官員所寫的日記。透過這些一百多年前的文字,不難看出當時日本的政治、社會、教育狀況,從一個側面了解中日文化交流史,更可以窺見我們的先人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所思所想以及步履之艱難。
宇宙最大之事業,無逾教育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受兩江總督張之洞派遣,江南高等學堂總教習繆荃孫一行十一人到日本考察教育。回國后將考察見聞寫成《日游匯編》一書,下面分別介紹書中的主要內容,并略作評述。
第一部分為講義卷,是記錄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君所講。嘉納君即嘉納治五郎,是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為日本著名教育家,曾多次訪問中國,亦曾多次接待中國赴日教育考察團,考察團成員的日記中屢屢見到其身影。繆荃孫以數千字的篇幅記錄了嘉納治五郎的談話,嘉納治五郎全面介紹了日本教育狀況,指出教育大別有三(普通教育、實業教育、高等專門教育),普通教育又分為三門(小學、中學、高等女學),日本學校種類大別有三(官立、公立、私立)、日本的學制以及商業學校、農業學校、工業學校、美術學校所教科目等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嘉納治五郎的教育思想,如說:
初級教育,最重德育。
國家富強之基,實肇于德育。
德育不講,人皆貪黷,其害匪淺。
歷史即富強之基也。
小學年限,不宜過長。
大學專重學理,不重實用。

國家之盛衰,視國民之愚智。國民之愚智,視教員之賢否。
尤其是“宇宙最大之事業,無逾教育”(引文除特別注明者外,均引自《日游匯編》)高論,穿越時空,震爍古今,至今讀來,仍光焰萬丈,令人心折。原文是這樣說的:
教育之事,在常人視之,極為無謂。而在教育家觀之,則宇宙最大之事業,無有逾于此者。試以軍事家論,軍事家戰勝攻取,以衛國民,所系可謂重矣。然軍事家所保全者,數十百年已耳。數十百年以后,其功業泯滅,殆如白駒之過隙。人民所享之幸福,非復曩之軍事家所造就矣。譬之貴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元太祖諸人,豐功偉業,非不震爍一時,然時移代易,則其澤斬焉。孔子一布衣,講求教育,萬世之下,學者宗之。蓋教育家之支配人心,其用迥出諸家之上。人類茍不滅,其教斷乎無絕期也……教員悟此,自知教育為唯一之偉績,舉斯世之榮利,均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想是行動的原動力,仔細想想,“宇宙最大之事業,無逾教育”是不是比我們經常宣傳的“教育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事業”,“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的作用是“傳道、授業、解惑”更加深刻,更加能夠揭示教育的真諦?更加能夠使教師增強職業自豪感和榮譽感?倘若我們的教師都能明了“宇宙最大之事業,無逾教育”,都把教育當作終生追求的事業,而非僅僅是謀取衣食的職業,又怎么會產生職業倦怠感?又怎么會產生事業的挫敗感呢?
第二部分為日本考察學務游記,是嚴格的日記體,記錄了自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初十自江寧赴滬至三月十一日自日本返國至滬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其中大部分內容是考察日本各類學校的記錄,計有東京府高等師范學校、東京府第一中學校、東京美術學校、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東京盲啞學校、東京商船學校、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郵便電信學校、宏文學院、早稻田大學、農科大學、東京帝國大學等,可以說從幼兒教育到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察,還會見了眾多的日本教育界知名人士。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如下內容:
幼兒園的快樂教育:“幼稚園無讀書,習字課程,惟教唱歌、游戲之易者,及古昔賢哲嘉言懿行淺顯易曉者,使小兒身體發達,腦力活潑,漸知練習學校規矩。”——不知長期接受和信奉“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理念的中國家長,不知當今有些把幼兒園辦成“小學預備學校”的人,讀了會作何感想!
關于日本小學分單級、多級的介紹:“一教員擔任一學年或一學科者,謂之多級小學;一教員擔任四學年兼授各學科者,謂之單極小學”。“多級一學年為一教室,單級則僅一室而已”。說白了,單級教學就是教員在同一個教室內,給不同年級的不同學生上課,這如何教?日本教育家嘉納君是這樣描述的:“如教一年生習字,則當其摹寫時,即可以讀本授二年生。二年生讀書,三年生即可學誦。教員乘其暇,又可授四年生算數。以此類推,則教員可不勞,而諸生皆受教矣。”想必中年以上且在農村偏遠山區上過小學的讀者看到這里,立即就明白了,這不就是自己兒時接受過的“復式教學”嗎?作者還說,“單級只山村、小邑之類,不得已而行之者”,是迫不得已、因陋就簡而發明的一種教學方法。寫到這里,想起不久前讀到的一篇名為《復式教學——不可或缺的教學模式》的文章,該文一開頭就說:“復式教學是我國居住人口分散的農村,特別是山區農村的一種重要的教學形式,是誕生在中國農村大地上的一種課堂教學的特殊模式。”不禁啞然失笑。

關于東京帝國大學陳列室的介紹:該校工科陳列室(書中稱為“列品室”)有七個,即土木工學、機械工學、造船學、電氣工學、建筑學、應用化學、采礦及冶金學。其中土木工學陳列室有“關于鐵道、橋梁、運河、港灣、水道下水等標本模型二百三十余具,各國土木工所用之物羅列靡遺”,電氣工學陳列室“有關于電信、電話、電燈、電力之各種模型標本器械一千五百五十余種”。理科陳列室有三個,即動物學、地質學、人類學。因文字過長,不具引。一百多年前,東京帝國大學學科設置就如此齊全,研究領域就有如此廣泛而深入,不能不令人嘆服。

除了考察教育,日本社會政治也是作者關注的重點。日本為何能夠在近代迅速富強?作者雖然沒有深入進行考察和分析,但從其日記及感慨中可以窺見端倪。日本新聞業非常發達,“全國報館林立,主筆者咸有采訪權,事無巨細,悉可直書無諱。”作者頭天抵達長崎,次日新聞即已見報,“消息之捷,可以覘國之所由興矣!”日本善于借鑒和學習,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參觀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時,作者看到了許多機械設備,大部分并非是日本所制造,“其本國所制僅有二種,蓋日人能絜各國之長,用其新器、新法,故不必自制機械,即能爭衡各國也。”特別是在參觀大阪(作者稱為“大坂”)博覽會時,作者感慨更深,日本幾十年中,“工商業之進步實可驚羨”,而反觀中國,送展的物品“均用舊式,未能推陳出新,較之各國之物均覺瞠乎其后。至機械、教育,則并不能以一物爭勝,可慨也!”
來到強國又是敵國的日本,作者對于國恥的感受非常強烈,民族大義和愛國情懷熾熱,喚醒國人急起直追的意識呼之欲出。參觀九段國光館時,看到了“庚子天津戰役油畫”,再現了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的場景,只見“炮火迷離,田廬狼藉,聯軍躍馬馳突,不見中國一兵。間有一二裹紅巾、披辮發、仆地不起者,則聯軍所斃拳匪(指義和團)也”。日本以此畫來鼓勵國民,每當有游客參觀,則“命一僮演說日軍戰勝之狀”,走筆至此,作者極為憤懣,“吾輩至此,慘憤交集,歸時當以此普告國人,使知國恥民艱,急宜振奮,不可如故之泄沓也。”在參觀大阪博覽會時,看到人類館端坐的臺灣纏足婦女,“任人注視,其狎侮吾同種至矣”,深感這是對中國的極大侮辱,“茍有血氣,能無憤恨,而坐視國人死守舊習而不變哉!”在參觀東京高等學校化學定性分析室時,作者見一印度留學生在試驗藥水,日本人介紹說:“該校有三國人留學,中國及朝鮮、印度也。英滅印度,奴隸遇之,雖有才智,不得受高等教育。印度人出而留學,則英人貽書各國政府,誡各國毋得使之學政治、法律,僅以工商制造賤業教之而已。故印度人之在日本者,學業程度遠不如中國及朝鮮人。”印度被英國滅亡后,居然連接受高等教育的資格都被剝奪,作者不由評論道:“亡國之慘,至于如此!”想必作者在寫這段話時,情不自禁地想起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1901年空前的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的簽訂,那種感受和滋味,不身臨其境是很難體會的。
作者的政治立場和觀點是保守的,自序中將清朝稱為“圣清”,吹捧清朝建立以來,“闿澤深仁,史所罕見”,對于自由平權之說不以為然,甚至稱之為“邪說”。但另一方面,對于日本的進步之處不吝贊美,對國內的落后腐敗批評毫不留情。作者到達橫濱,收取行李,“海關查驗,嚴而不擾”,而一回到上海,化學器械都被海關扣留,直到五天后,“由關道給信方提出,并索費,無理紛擾百倍日本矣”,堂堂的“江南高等學堂總教習”過海關時尚且受到如此敲詐勒索和刁難,小民百姓更可想見。在參觀東京巢鴨監獄時,看到監獄講究衛生,對犯人進行文化教育以促使犯人“悔罪自新”,尤其是“授以生業,使之將來可以謀生”,不禁發出由衷贊嘆。而“我國之監獄,黑暗穢臭,獄卒凌辱,而處其中者又不盡皆死罪,有株連波及者,讞獄未終,而其人已瘐死。其幸而出獄者,既未加以教訓,又未授以生業,則仍為從前之所為耳。故今日言施仁政,非自監獄始不可。”只是他的拳拳之心,不知當政者有幾人能深刻領會?
第三部分為日本訪書記,作者是著名的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據說是其捉刀),他提醒到日本訪書的學者,如何衡量古書的價值,其心得是:“大約古抄卷子本為上,宋元舊刻次之,翻刻本而未加和(指荷蘭)文者次之,活字本次之,影寫者次之,分類以求,謹以告東游好古之士。”
興學為立國之根本
袁世凱是亂世之梟雄,治世之奸雄,盡人皆知,但若說他也重視教育,恐怕沒有多少人相信。不過事實勝于雄辯,在清末新政期間,在其擔任直隸總督時期,他的確曾多次派遣官員赴日進行教育考察,甚至親筆為考察記作序,卻是不爭的事實。

光緒二十九年,受直隸總督袁世凱派遣,王景禧赴日本“視察”學制,從九月初一日啟程赴日,至十月二十二日返程,歷時五十日,作者自云:“此行視察學校,自幼稚園,而尋常小學,高等小學,中學,高等學,大學,以次遞進。”幾乎是馬不停蹄,“視察”了各級各類學校數十所,并將其見聞寫成《日游筆記》一書,本文不打算面面俱到地介紹其內容,只是就其中最重要部分加以點評和分析。
關于教育的重要性:九月十五日,作者赴直隸留學生歡迎會演說,劈頭就說:“國之振興,基乎教育。”他研究日本教育,深感“興學為立國之根本,而小學之國民教育,尤為根本之根本”。何為國民教育·“所謂國民教育者,謂有普通之知能,能勝國家之職務,始足為此國之民”。反之,“無普通之知能,則雖有耳目心思,雖有手足肢體,而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有此人幾如無此人,且須仰給于人,直與廢人等耳”。作者認為,日本人能各司其職,“一無游惰”,“其原因皆由全國普及之小學國民教育而來”。接受了國民教育,“乃能擔任一般國民之義務,具一般國民之資格,乃能擔任一般國民之義務”。
關于日本各級學校不同的培養目標:小學要普及國民教育,“無貴賤賢愚,悉令受學,皆民生日用所必需,無容或缺者也”;中學以及實業學校,“則為養成能勝職業者之程度,學求有用,即知即能也”;高等以至大學,“則為養成主持政法,指揮職務,發明理要者之程度”。也就是說,小學是傳授民生日用所必需的知識,中學是培養能勝任職業的有用人才,大學則培養高級的專門人才。
作者對于日本各級各類學校都重視唱歌和體育,印象深刻,評價甚高。他觀察到 “此邦各校,無不有唱歌一科,所以激發忠愛,涵養德性”,“體操一科,則自幼稚以及大學,尤汲汲而不一懈”。“從前幼稚園重智育,今則體育德育視為并重”,這不是德智體全面發展思想的萌芽嗎?他多次參觀各校舉行的運動會,對比賽項目津津樂道,試看其記載:
九月十九日午后,“往觀女子師范學校高等女學校之運動會。運動會者,每年一次,合全校師生,為各項運動。來觀者數千人,寂坐無嘩,贊賞者但鼓掌而已。名目四十有二,有寫生競走,裁縫競走,割烹競走,插花競走等,以最敏捷者第一人為優等。”女校運動會的比賽項目的確別出心裁,有女子學校的鮮明特色,而數千觀眾“寂坐無嘩”,從中不難看到日本國民的素質。
九月二十七日日記,“昨日觀大學堂運動會,有曰棒飛者,立二標桿,高約二尋有余,上浮置一橫線,一人拄捧,飛越而過,線不少動。”“尋”是古代的長度單位,一“尋”等于八尺。“棒飛”不就是今天人們在運動會上經常看到的“撐竿跳”嗎?

再看其對日本學校體育課的記載。九月二十一日,參觀東京府立第一中學校,“至體操場,觀角抵術,二人相持,地鋪厚薦,雖仆不傷,教習言此名柔道,亦名柔術。觀擊劍術,則皆以鐵網罩面,以革蔽身,用竹作長劍,盡力擊刺,以中要害為主。教員亦蒙面裹革,由學生奮擊,口中亦作吶喊聲。驟觀可駭,實則注意體育者至矣。”身為日本著名教育家、“柔道之父”的嘉納治五郎,雖然“年近五十,尚躬自入場,年少者或不能敵”。對于體育和體操的作用,作者贊賞有加,認為注重體育,能使人們“絕無畏難茍安萎靡不振之習”。“至體操一端,學人則以為不屑,實則體質脆薄,日即頹惰,于力行一訓,多所愧缺”。甚至認為“唱歌為教育之心,而體操為教育之骨矣”。想必研究教育史的人都注意到,凡是到日本留學過或考察過教育的人,都非常注重體育,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南開大學的創辦者張伯苓都是如此。作為大學校長,張伯苓可能是最重視體育的,他關于體育的名言不勝枚舉,像“德智體三育之中,我中國人所最缺者為體育”,“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強我種族,體育為先”,“教育里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甚至認為“不懂體育的,不應該當校長”(《思想者的產業——張伯苓與南開新私學傳統》128—129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身負送直隸留學生到日本的重任,所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學習生活情況也是他關注的重點。九月十三日,他和中國駐日大使楊樞、參贊馬廷亮擬定直隸留日學生課程,計有教育學(附心理學)、教育制度(日本歐美)、教授法(附編纂教科書法)、學校管理法、地理學(附地文學)、歷史學(附近世外交史)、法制經濟學、數學(分數小數開平開立代數)、博物學(動物植物礦物生理)、理化學(物理化學之實驗)、日本語文、體操(普通器具兵式)十二門,從中可見留日學生課程開設之一斑。還規定留日學生每星期內參觀學校一次,至第三學期,每星期兩次,注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用意非常明顯,這都是研究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好材料。十月初九,參觀日本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成城學校和振武學校,校方介紹:“本校教中國陸軍學生,純以激發忠義并學識技能為主,凡一切革命平權等謬說,斷不容令學生聞之。即各報之語失其當者,亦嚴禁閱看。”思想控制不可謂不嚴,然而令校方和清朝統治者想不到的是,此校的眾多中國留學生,回國后相繼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蔡鍔、陳獨秀、孫武、吳玉章、李烈鈞、蔣介石,就是其中最為著名的。
書中關于裸體模特兒的記載,也是很有超前眼光的。九月三十日,作者參觀位于上野公園內的美術學校,“凡繪畫共十余室,無不殫思研慮,至以生人為模型而寫之,全身畢現,以為非此不肖。傭此等人之值,每一小時兩元矣。”作者雖然沒有指明裸體模特兒是男是女,也沒有一個字的評論,但如此客觀記述已相當不容易。須知中國第一個裸體女模特兒,到1920年的上海美專才正式誕生,從裸體女模特兒誕生之日起,爭議和反對之聲就不絕于耳,什么“有傷風化”啦,什么“傷風敗俗”啦,上海美專“分明是妓院”啦,如此等等,冷嘲熱諷,不一而足。當時的上海縣長下令禁止人體寫生課,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下令通緝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對是否使用裸體模特兒依然爭議不斷。1964年,康生等人曾在一份《關于使用模特兒問題》的報告上批示:“這個問題現在必須解決它。用女模特兒是不是洋教條?可不可以廢除?難道吳道子的人物畫是靠這個辦法練出來的嗎?”“我意應堅決禁止,我決不相信要成為畫家一定要畫模特兒。”他們甚至還認為,“這種辦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美術界玩弄女性的借口。”官司打到毛澤東那里,直到毛澤東批示,“男女老少裸體model,是繪畫和雕塑的基本功,不要不行”,才算終結了爭議。當然,這是后話。
作者王景禧(1867—1932),字燕泉,號石蓀、石遜,山東滋陽人(今隸兗州)。他15歲即中秀才,21歲成舉人,23歲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5歲朝考一等,授翰林院編修,可謂少年得志。1902年被任命為直隸學校司總辦;次年,又改任普通教育處總辦,兼編譯局總辦及官印局會辦,并且被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同時護送一批留學生到日本宏文學院學習。其赴日考察時還寫了《瀛談剩語》詩集,從中頗可看出他當時的思想情況。如“我愛東瀛地,圖強果自強。有人皆教育,無處不膠庠。會社新株式,衣冠半古裝。交通尤便利,左右太平洋”(《雜詩》五言之三)。“新詩三十首,吟罷雪盈顛。對照方知愧,瘐詞敢浪傳?精神真教育,關塞慘風煙。不敢聞雞舞,恐將三島翻”(《雜詩》五言之十三)。“同胞四萬萬,聽我語無嘩。學以實為貴,國之本在家。富強唯教育,時代尚萌芽。不惜詞多諷,揮戈日已斜”(《憶否》之十)。可以與其赴日考察記對照閱讀。當然其最著名的詩作是20世紀20年代末所作的《宮井詞》,寫的是清光緒皇帝和珍妃的愛情悲劇,對清末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都有涉及。詩中充滿了濃濃的故國之情,滄桑之感:“天留老眼看興亡,兒女江山夢一場。剩有御溝嗚咽水,年年遺恨哭滄桑。”堪比白居易的《長恨歌》和吳梅村的《圓圓曲》。
順便提一下,網絡上所見到的關于王景禧的文章,包括其家鄉人樊英民先生所編寫的《兗州史話》以及王景禧第三子王迺泗先生所寫的《憶我的父親晚清翰林王景禧》,一方面為人們了解王景禧的生平事跡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史實錯誤,如把王景禧的赴日考察記《日游筆記》誤成《日游日記》,把王景禧護送直隸留學生二十人赴日留學說成是二十二人,為防止以訛傳訛,在此特作說明。
國勢強弱之分,大半視教育普及與否為比例
三十多年前,《走向世界叢書》主編鐘叔河先生到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訪書,意外地發現了雙壽所著的抄本《東瀛小識》,于是復印下來,成為此次整理出版的底本。筆者曾遍查國內各大圖書館的古籍書目索引,均未見著錄此書,專門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或者教育史的論著,也未看到引用該書,不知收藏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最豐富的“實藤文庫”(《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作者實藤惠秀捐贈,藏于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是否有此書。由此可見,倘若不是鐘叔河先生發現此書,并提議收入《走向世界叢書》出版,《東瀛小識》不知道還會在書庫中沉睡多久,看來書的命運和人的命運一樣,有遇有不遇也!
原書無序跋,書前除書名外,僅有“湖北學務處委員試用同知雙壽謹呈”題簽。雙壽何許人也?姓氏為何如此偏僻?經多方搜尋查考,得知雙壽是鑲紅旗蒙古人,字如山。曾在宣統初年署理武昌知府和漢陽知府,民國年間修的這兩個府志應該能查得到。至于雙壽的其他履歷,因手邊資料欠缺,一時無從了解,企盼高明指點。
雙壽是誰派遣到日本考察教育的?查張之洞的履歷,1889—1907年任湖廣總督。1901年7月設學務處綜理湖北全省學堂事務。因此可能為張之洞所派遣。
雙壽是何時到日本考察教育的?原書只標注月日而未系年,但《東瀛小識》七月初三記載“明年以大坂(今稱大阪)賽會,刺繡圖畫各課甚忙”。“大坂賽會”即大阪博覽會,1903年召開,因此雙壽于1902年赴日考察教育無疑。
《東瀛小識》所記起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二十五日參觀成城學校,至九月初三參觀華族學校,歷時三個多月。和其他去日本考察教育的人不同,雙壽考察的重點是日本的軍事教育,其參觀的軍校計有成城學校、陸軍士官學校、炮工學校、戶山學校、騎兵實施學校及附屬之獸醫學校、陸軍大學校、軍醫學校及陸軍經理學校,記載各軍校的入學資格及科目設置,還曾到步兵第一聯隊、騎兵第二聯隊、近衛野戰炮兵聯隊看操,并到陸軍省直屬之織絨局參觀。作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人對軍人的重視及不以從軍為苦:

其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大之立靖國神社,以祀死難諸臣,春秋致祭,帝后親臨,凡屬軍人,皆來觀禮;小之則一歌曲之微,一圖畫之細,莫不隱寓獎勸愧勵之意于其中。故其民之及歲而為兵者,父母以為喜,戚友以為賀,榮之以鼓樂,勉之以詩歌。以為此國民擔任國家之義務宜然,豈復有以從軍為苦者哉!
日本人不以從軍為苦,戊戌變法失敗后在日本流亡的梁啟超早就注意到:“冬臘之間,日本兵營士卒,休息瓜代之時,余偶信步游上野,滿街之紅白標幟相接,有題曰歡迎某師團步兵某君,某隊騎兵某君者,……其本人服兵服,昂然行于道,標則先后之,親友宗族從者率數十人。其為榮耀則雖我中國入學中舉簪花時不是過也。其標上僅書歡迎某君送某君等字樣,無甚贊頌祝禱之語,余于就中見二三標,乃送入營者,題曰‘祈戰死三字,余見之矍然肅然,流連而不能去。日本國俗與中國國俗有大相異者一端,曰尚武與右文是也。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詩歌無不言從軍樂。”(《清議報》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梁啟超對日本親友數十人送新兵入伍印象深刻,對題寫“祈戰死”肅然起敬,進而聯想到日本國俗和中國的巨大差別,感慨“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也許只有陸游是例外,他在《讀陸放翁集》一詩中感慨:“詩界千年靡靡音,兵魂銷盡國魂空。詩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兵魂”就是尚武精神,是“國魂”的集中體現,梁啟超將“兵魂”和“國魂”的關系點破,的確發人深思。
除了考察軍事教育,雙壽還考察了日本的普通高等教育。值得一提的有八月十五日參觀高等商業學校,注意到“其尤重在商家道德一科,以明此則可謀公利以保其私利”,這令人聯想到朱镕基擔任總理時,親筆為三個國家會計學院題寫“不做假帳”校訓;八月二十九日參觀醫科大學,“見解剖一孕婦,血肉狼藉,慘不忍觀”,醫師對他說:“解剖已死,而可活未死。解剖一人,而可活眾生”,不禁贊嘆不已:“文明各國,雖明知此事殘忍,而所見甚大,所求甚精,故亦相沿成風,不以為怪。”但是他的知識水平,他的見識,他的視野限制了他對日本教育的深入了解,且看他八月二十八日到大學參觀時的記述:“其文科法科皆空文,無可觀覽。閱工科理科各教室,見應用儀器標本,以程度太高,知其貴莫名其寶。”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而返。所以他雖然也有“國勢強弱之分,大半視教育普及與否為比例”的認識,但總體上對日本教育考察浮光掠影,和日本教育家也缺少深入交流,記述不免流于表面,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