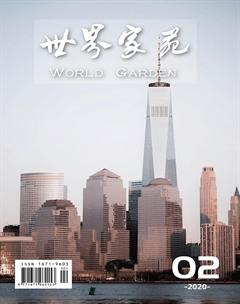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認知二元論
李洋 鄭煜
摘要: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在客體、主體、訴訟性質方面具有二元化的特殊性,相應地在司法認知方面也具有二元性。檢察機關辦理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其司法認知在二元體系中起到先決作用,需要以庭審實質化的理念指導調查核實程序,從而克服不當司法前見,形成正確的司法認知,保護環境民事公益。
關鍵詞: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認知;司法前見;庭審實質化
環境,除自然之物外還包括社會因素和經濟因素。因此,涉及到環境污染和破壞的侵權行為,與普通民事侵權行為的區別在于,所侵害的客體直接地體現為特定(或不特定)群體的民事權利以及一定的普遍社會管理關系,并且更突出地體現在社會管理關系層面。這也是環境公益訴訟產生和演進的緣由之一。
1 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特殊性
基于環境侵權行為的性質,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1)客體方面:權益損害和法益損害二元性。學界有觀點認為環境侵權二元性是指人身財產侵害和生態系統侵害的二元性。但更重要的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被告的行為之所以被歸為公益訴訟的對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對法益的侵害。在環境法領域,對于法益的理解,不僅抽象于“法保護的利益”,更具體在“法保護的環境秩序”。如在違法傾倒有毒廢液致使土壤污染的案件中,環境秩序所體現的是受污染范圍內的社會生存條件和經濟發展條件,這種公共價值與個體權益同時存在,構成了民事環境公益訴訟客體的二元性。
(2)主體方面:公益保護與司法保護互補。所謂公益保護,是指基于環境秩序維護,通過原告的身份對環境民事公益的保護,包括社會公益組織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以及政府部門啟動磋商程序和提起生態損害賠償訴訟。有的觀點認為“生態環境賠償訴訟的本質是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實質上,這種本質的統一背后蘊含著“公益保護”訴訟性質的同一性。所謂司法保護,是指通過司法權的主動介入對環境民事公益的保護,在現行立法框架內是指檢察機關以司法機關的身份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
(3)訴訟性質方面:公益與公訴并行。公益組織和政府部門提起的環境損害賠償之訴,其公益性毋庸置疑。在檢察機關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情形下,檢察機關既作為“公益訴訟起訴人”行使原告的權利,又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訴訟過程進行職權性的審視。檢察機關進行調查核實,根據取證情況確定訴訟請求,并對裁判結果是否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進行監督,實質上體現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公訴”屬性。
2 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司法認知的二元化
(1)檢察機關的司法認知。司法認知乃是司法者對于法律問題“探尋理性的過程”。基于檢察機關的司法定位,檢察機關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其中包含了兩種司法認知,一種是在法院審判中法官對證據效力和案件事實的認知,另一種是基于檢察權的司法權屬性,檢察機關站在法律監督角色地位上對證據效力和案件事實的認知。
(2)檢察機關司法認知的先決性。對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而言,檢察機關的司法認知決定了案件訴前階段的演進方向。因檢察監督缺少質證辯論的環節,檢察機關在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中,更易形成對環境公益損害的司法前見:一是對被告行為構成公益損害的前見;二是對涉案行為人責任劃分的前見;三是對損害賠償數額的前見。造成司法前見的原因在于大量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與行政處罰案件或刑事案件相關,在之前的法律處置中,已經形成了在追究責任思路引導下的證據材料;檢察機關在審查線索立案后,按照民事訴訟的原則和標準組織證據,難以避免地受到此前法律處置的影響。
3 庭審實質化理念與司法認知糾偏
(1)庭審實質化理念。庭審實質化要解決的問題是“庭審空洞化”。試圖通過庭審對證據進行審查,進而形成正確的司法認知,是庭審實質化改革的內在要求。在傳統的民事訴訟檢察監督中,檢察機關作為案件的抗訴機關,在庭審中并不參與法庭辯論,僅對依職權調查的證據予以出示和說明。在這種訴訟模式下,檢察機關的抗訴理由以及當事人對抗訴理由的反駁意見,無從通過庭審予以爭辯。法官的司法認知來源于對書面材料的審查判斷,即使在再審庭審中聽取原被告雙方當事人的意見,也未對檢察機關的訴訟請求進行實質化的“直接審理”;相應地,檢察機關在調查取證時也沒有將關注點放在庭審效果上,其取證往往蘊含著一定的“司法前見”,將調查的思路預先固定在了原審的錯判上。而對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角色實際置于公益訴訟起訴人角色之后,檢察機關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通過庭審勝訴來達到對環境權益和環境秩序的保護。
(2)司法認知糾偏。環境侵權案件在證明標準和舉證責任方面不同于普通民事侵權案件;檢察機關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因需要一舉達到證明“權益損害”和“公益損害”兩個目的,而必須采取更嚴格的證明標準和更審慎的舉證責任。如何消除不正確的司法前見,形成準確的司法認知,從而實現維護社會公益的訴訟目的,是擺在檢察官面前的重要問題。根據檢察機關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取證特點,在起訴前檢察機關應當對有關證據進行“實質檢驗”:一是對于證據的審查,不能僅限于形式合法的要求,還要注重審查證據的內在合理性與邏輯性;二是注重聽取被告的辯解和證人的陳述,必要時組織公開聽證,在檢察監督中引入法院庭審的類似模式,變間接審查為直接審查;三是嚴格把握證據能力,對于證據來源和取證程序不合法的證據,要依法予以排除;四是堅持嚴格的證明標準,對于達不到“基本事實排除合理懷疑”的情形,不能作為訴求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提出。
4 結語
檢察機關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不可避免地要解決司法認知的二元化問題,即檢察機關的司法認知與法院的司法認知如何協調統一。檢察機關的司法認知具有先決性,需要在辦案中正確認識調查取證環節的司法前見,避免錯誤司法認知對審判環節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王映雪.生態損害賠償與環境公益訴訟的銜接路徑研究[J].北京政法職業學院學報,2019(03).
[2] 李浩.生態損害賠償訴訟的本質及相關問題研究[J].行政法學研究,2019(04).
[3] 王申.法官的理性認知與司法前見[J].法律科學,2012(06).
[4] 黃河.裁判者的認知與刑事卷宗的利用[J].當代法學,2019(05).
[5] 宣剛.從“刑事印證”到“實質檢驗”——庭審實質化改革中事實認定模式的轉變[J].寧夏社會科學,2019(04).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科基金項目“生態法哲學視野下的低碳發展法治研究”(19CFXJ10)及淄博市重大研發計劃項目“淄博市生態環境損害修復的公益訴訟機制實證研究”(2019ZBXC280)。
作者簡介:李洋,山東理工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山東省淄博市人民檢察院員額檢察官。
(作者單位:山東理工大學 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