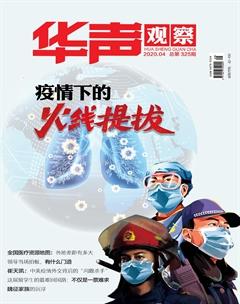徐玲:“遼寧號”航母的女舵手
陳霖

1988年生于江蘇盱眙的徐玲,是中國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艦”的女舵手。如今,距離她掌舵航母的那年已過七載,退役后的她回到家鄉,在地方海事處當一名普通的辦事員。這里緊靠淮河,徐玲覺得:“淮河有小舟、小艇,我把它們當軍艦,也是對海的一種依戀吧。”
熟記3000多個艙室的位置
“遼寧艦”重達6萬噸,以前掌舵的均是男兵。近些年,我國海軍實力不斷增強,“艦艇出海就跟下餃子一樣”,2009年末出現了艦艇女兵,徐玲就是其中之一。一次出海護航,徐玲和其他女水兵上船,首長讓她們選擇想負責的項目,有人選通信、有人選雷達、有人選報務。徐玲走進船艙,第一眼就看到了深棕色的操舵盤:“首長,我可不可以開船?”首長笑笑說:“可能不行,歷史上還沒有女的開船。”“可我想做這個(第一個)開船的,行不行?”首長同意讓徐玲試試,她便開始了航母舵手的訓練和考核。
第一項就是找艙室。遼寧艦有十幾層,每層只有一兩個出口,分布于各層的上百個艙室,舵手必須對出口的位置爛熟于心。考官從3000多個艙室中選出5個,在房間里放東西,讓徐玲在半小時內找出來。“艙室長得都差不多,我方向感很差,一開始真是摸不著頭腦。”徐玲就用土辦法,多跑站位,每天執勤結束就上樓看艙室,幾個月下來,記下了3000多個艙室的位置和每層的出口。除此之外,徐玲還學習損管:當航母觸礁,船身破損時,在第一時間補洞、補漏。半年后,徐玲完成舵手考核,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航空母艦女舵手。
徐玲熟練掌舵“遼寧艦”后,海軍部隊認可了女兵在船上生活工作的能力。這使得近年來航母逐漸出現了女舵手,如今“遼寧艦”的女舵手來自新疆,是名哈薩克族姑娘,和當年的徐玲一樣,也是24歲。
綁在鐵輪里抗眩暈,“旱鴨子”成女水兵
2009年10月1日,徐玲在烈日下走過了長安街。她作為三軍女兵參與了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閱兵式,接受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的檢閱。此前,還是海軍通信兵的徐玲進入閱兵村,與300多名女戰友進行長達一年的閱兵訓練。大閱兵結束后不久,海軍選調女艦員,徐玲立刻報名,成功入選,成為中國海軍首批艦艇女兵。
“旱鴨子”徐玲當了女艦員,得先學游泳。班長把繩子系在她腰上,推她下水。徐玲不會游泳,在水里掙扎,大口喝水,喝飽了,班長把她拉上來。“我把水吐了,班長又把我推下去。人有求生的本能,幾個來回就會(游泳)了。”
可怕的還有暈吐。徐玲上了船,暈得很厲害,便開始進行抗眩暈訓練。她站進一個大鐵輪里,手腳均綁在輪子邊上,班長轉動輪軸,讓鐵輪轉起來。第一次轉了兩圈,徐玲感到天旋地轉,從輪子上下來,雙腿跪地,“五臟六腑都要爆炸了”,然后增加圈數,10圈、20圈……最后能連續轉10分鐘。
等到上了船,徐玲發現,抗眩暈訓練和實戰是兩碼事。在鐵輪里是一個方向地轉,出海后是上下左右360度地晃。她吃米飯,被船晃幾下就吐出來,但必須吃飯,才有力氣,就再往嘴巴里塞。
2010年,徐玲首次掌舵,駕駛“和平方舟”號醫院船赴亞丁灣。駛入亞丁灣之前,海浪特別急,整艘船劇烈震蕩。徐玲忍不住暈吐,便在耳朵上掛了個塑料袋,邊吐邊開,但雙手緊握操舵盤,即便青筋暴起,也不曾松手。這樣開了一周,總算過了這個危險之地。
開“三甲醫院船”,談“海上戀愛”
“和平方舟”號是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首艘萬噸級大型專業醫院船,搭載的不少醫療設施達到三甲醫院的水平。它2008年入列,已航行24萬余海里,到訪過43個國家和地區,為至少23萬人提供了醫療服務,被稱為“流動的海上三甲醫院”。2019年底,中宣部授予它“時代楷模”稱號。
徐玲開著醫院船,每到一個國家待一周到半個月,讓醫療隊給當地人進行醫療救助,“白內障手術對中國醫生來說并不難,但在非洲國家則是非常大的手術。那段時間,醫生一天要做上百臺手術”。
大海還給她帶來了一位愛人。2010年,徐玲結束“和平方舟”號的執勤任務,回國到舟山為醫院船進行補給,結識了另一個部隊的護航班長張標。張標曾4次去索馬里護航,立過二等功。兩人領著各自帶的士兵上岸購買物品,一段時間后變得熟絡,很聊得來,開始談戀愛。但確定關系的第二天,徐玲就回到大連,之后被選中進入“遼寧艦”,張標則留在舟山。此后4年里,徐玲和張標聯系,幾乎只能通過電話。誰出海了,就用海上衛星電話打給對方,在陸地上的那人只能等,“手機不能沒電,每次它響了,我就很激動,猜是不是他”。徐玲退役后,與張標在淮河邊舉行了婚禮。
“家長里短”都關乎國家建設
2013年,徐玲從海軍退役。徐玲離不開大海,主動申請到盱眙的海事處當辦事員。“這里雖然沒有海,但有淮河,總能讓我想起大海。”每天清晨,徐玲一到海事處,要先到淮河邊,看看船、看看水,才進辦公室。
徐玲的辦公室有十幾個大屏幕,便于她實時監測淮河流域上來往的船只是否超載;船舶碰撞,要跟同事們一起打撈船舶;船之間“打架”了,船長爭吵誰先撞到誰,徐玲也要前去調解。最棘手的是與漁民打交道。有的漁民經常拉網,影響船舶正常通行,徐玲讓他們撤網,但漁民不聽,有時候一著急,會說臟話,甚至抄起家伙要打架。最后沒辦法,徐玲和同事就與漁民談補償條件,讓他們撤掉漁網,保證淮河水域航道的安全。
“那陣子,我的腦袋常是懵的。我就是不明白,這么清晰的問題,規定寫在那里了,不能拉網,我使勁跟他講,為什么他就是不明白?”以前在部隊,徐玲的工作習慣是執行領導下達的指令,退役后到地方,困于事務細節,第一年,她差點得了抑郁癥。
想不明白的時候,她就像曾經在部隊那樣,上甲板望望水面。“后來我想通了,站在漁民的角度想,他們以捕魚為生,漁網就是飯碗,是生活中極其重要的經濟來源。你把人家飯碗給砸了,他們肯定是要跟你理論、拼命的。”慢慢地,徐玲解開了心結,之后再遇到拉網的漁民,就耐心和他們講,直到對方明白規定。后來,有的人不小心拉網了,還會主動過來接受懲罰。
如今天天與淮河為伴的徐玲,對地方工作有了新體會,“看似處理小流域的日常瑣事,好像‘家長里短,但事無大小,都是國家建設的點滴”。
摘編自《環球人物》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