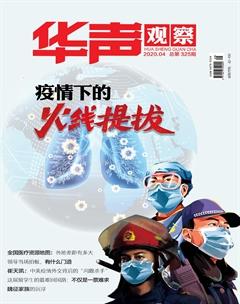過億老洋房的追捧者們
史千蕙
在價值千萬甚至上億的老洋房里,生活是怎樣的?
住老洋房也有煩惱
一部分符合工薪階層對有錢人的描摹:衣帽間里,一面墻都是鉑金包,襯衫們由專門的收納師負責整理,由淺入深地排好順序。拉開酒柜,里面是3萬元一瓶的紅酒,要用單價大幾千的水晶杯來裝。杯子撞在一起,發出悅耳的聲音。
受邀前去作客的Sammi——一位從事了17年老洋房生意的房產中介,每次碰到這樣的時刻,她都會說,別給我這么貴的酒,我也喝不出來好壞。但或許,酒柜里也沒有便宜的酒。
原本的處處更是寶貝,墻面紅瓷瓦、斜陡坡屋頂,還有混搭著多樣化建筑風格的裝修和布置:手繪的彩窗玻璃、用老木頭打在墻上的書桌、黃底紅邊的窗欞、哥特式的煙囪……西式房屋的格局,配上中式庭院的小橋流水,掩映在成群的法式梧桐里,褪色的浮華沒有黯淡的光,而是有了另一番趣味。
但老洋房的最迷人之處,不在于昂貴,也不在于底蘊,而在稀缺。據資料顯示,全上海現存的老洋房只有不到5000棟,其中九成以上的產權為國有。再除去有產權糾紛的房子,余下可供出售的,只有一兩百棟。
這些房子分別來自上個世紀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而房子的現任主人,有富豪榜上有名的大商人、90后新貴、也有一線明星。Sammi負責讓房子和這個年代的主人相遇,當她的客戶完成了裝修和搬家后,通常會邀請她來吃一頓晚飯,或是喝一頓下午茶。
煩惱也是他人難以想象的。即使住進了上海老洋房里,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徐匯區、長寧區擁有200平米的大花園和三層別墅,也并不意味著,生活就因此沒有煩惱了。
周先生的房子在原來的“法租界”,上海圖書館附近。他已經在這里住了十年了。院子里有四棵合抱粗的百年老樟樹,它們的根部在地下暗暗蔓延,院子的圍墻有了裂縫。三層樓的高度也惱人。拿個東西要跑上跑下,麻煩。近年來,周先生發現自己變懶了,大部分時間,他都在一樓,除了睡覺,幾乎不上二樓。三樓的客房、洗衣間和儲藏室,他一年也上不去幾次,只有住家的阿姨會去洗衣服和打掃露臺上的落葉。
“不一樣”的房子
老洋房們不愁找不到客戶,品相好的老房從來不缺主人。

1998年,周先生從歐洲回國,在經過那些從小看到大的老房子時,他和太太說,這套房子帶大花園,我們以后買吧。九年后,周先生第一次正式邁入這套房子的院門。古樹陰翳,世界好像突然就安靜下來,也涼快下來了。在那個瞬間,他感受到了“神圣”。
真正上億身家的買家很少全程參與購房的過程,更多時候,他們只做最終的拍板決定。周先生從了解到買下,中間隔了一年,他只看了一次。那天看房的人很多,他站在花園里,見到一層層的人們涌過來,報出的價格一層層抬上去。
將近一年后,帶他看房的中介跟他說,那套房子價格有回落。這一次,周先生選擇坐在咖啡店里等消息,不多時,中介談好了價格,給他打了電話。他們當場完成了交易。
花園,是周先生看中這套房子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他住過新里洋房,需要穿過客廳,才有50平米的花園。而現在,門一開,就是200平米花園,“眼前那個感覺還是有點不一樣的。”
在看房的那天,他就想,孩子還小,以后長大了,可以一起在花園里打羽毛球。這個消遣在今年突然成了這棟房子的動人之處:回國后的14天隔離期里,周先生和他的家人不僅可以在各自的房間里享受獨處,也可以一起去花園里散步。
他和太太不太喜歡全中式的裝修,覺得太沉悶。他們保留了陽臺上雕花的鑄鐵柵欄,找人做了除銹和噴漆,再原樣裝了回去。幾十年前的欄桿,握在手里沉甸甸的,花紋細膩,怎么看都覺得好看。他們還改造了客廳的采光,把一個內陽臺打通,做了一扇外凸的落地窗臺。花園里的梧桐、銀杏和桂花樹們,會在夏天合力伸開枝蔓與葉片,幫一家人擋住熾烈的陽光,房間里涼爽無比,又在冬天掉光葉子,不影響室內的通透。
老洋房的生意經
和所有收藏市場一樣,老洋房的買家們自成一個圈子,圈子里暗流涌動。有人買了房,自己也想買。有人買了更大的房,自己也要換。
當有洋房情結的客戶需要買房時,遇到中介,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試探。有的客戶是上海本地人,他們本能地不那么相信不說上海話的中介。為了專業,汪平買了一大堆相關的書,裝了滿滿一個書架。這些書很貴,有的還是和老洋房一樣稀缺的古籍,光是上下兩冊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就要兩萬八一套。十幾年下來,光是買書,他就花了幾十萬。
他帶客人去看房,看到和書中一樣的馬賽克瓷磚,他會很興奮:花紋復雜的馬賽克,是上海老洋房的特色之一。有的房子里,每個樓梯轉角的花紋都不一樣,遇到能夠保存完好的馬賽克,更是難得的意外之喜。汪平會就馬賽克這一個細節,和客戶聊上半天,客戶察覺到他的用心,“覺得你是靠譜的。”
中介也好,買家也好,與老洋房密切相處的人們都表示,一旦看中,下手必須穩準狠,品相好的老房子就那么些,買得起的人卻越來越多。
汪平在2009年,賣出了他迄今為止最貴的一套房:5000萬。買家是互聯網行業有名的大佬,11年后,那套占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已經漲價到一點幾個億。周先生目前住的房子,在2007年購入的時候,整棟樓連上地價,一共2000萬。現在,他保守估計,至少也漲到了七八千萬——講到這里時,他笑出了聲。
在胡先生買進賣出、搬來搬去十多年后,上海的樓市價格也進入了平臺期。他賣掉了手里大多數的老房子,只留下現在住的一套,折騰累了。最近,他開始聯系熟悉的房產中介,希望可以拋開情結,換一套純自住的房子。大房子好看歸好看,但打理起來有些費勁,不如換一套更輕松的,“哪怕小一些也沒關系。”他說,夫妻兩個人住,250平方米,房間不用太多,四面臨空,“稍微有一點花園”,可以給太太施展園藝,足夠。
Sammi每次被邀請去老洋房里做客時,都很開心。她喜歡看到一家人愜意起居的樣子,但更開心的是,也許,住在這里的人有天要換房,那時,她又有房子可以賣了。(應受訪者要求,汪平為化名)
摘自“每日人物”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