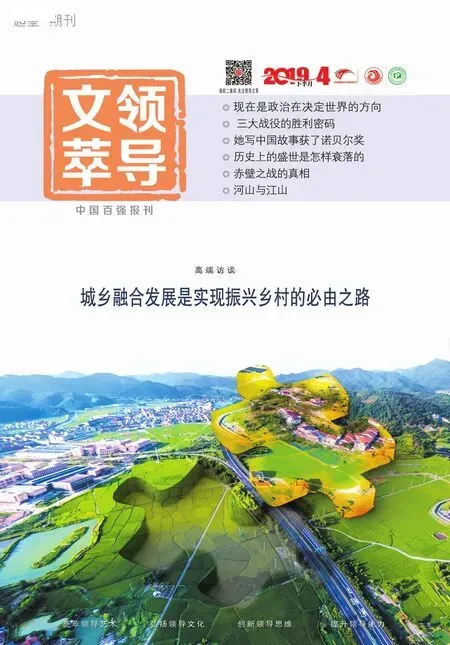龔自珍們的中年危機
胡赳赳
現在回到三個甲子前的己亥那一年(1839)。自杭州北漂至京城,當一個小公務員的龔自珍,終于被北京的權貴們擠出局了。那一年,他不得不展開“逃離北上廣”的旅程。
京城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圈子。龔自珍最知名的朋友有魏源和林則徐。這一年,魏源還沒有寫出他的《海國圖志》,影響日本歷史的明治維新尚沒有發生。而林則徐則在這一年去了廣東,開始為虎門銷煙做準備。臨行時,他婉拒了龔自珍請求隨行的動議。
的確,龔自珍這個人的毛病太多。他聽從外公段玉裁的教誨“要做名儒、做名臣,不要做名士”,因此屢屢戒詩,又屢屢開戒。他有天生的名士做派,行為不甚檢點,議論朝政,出語傷人,是常有的事。他甚至說,整個朝中和江湖,都沒有有才能的人,全是一幫傻子。
他還有一個毛病,甚會得女性歡心。盡管他是個五短身材,面貌倔強,但絲毫不妨礙他以詩歌的才能進入女人的心扉。顧太清被稱為大清第一女詞人,她曾經是一位王爺的側福晉,因為與龔自珍過從甚密,詩詞唱和,引來非議,最終被逐出王府,流落民間。據說,己亥這一年龔自珍的離京,與這段經歷有莫大關系。
48歲時,龔自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對新疆、西藏的地理有深入研究,希冀能派上用場,朝廷有朝一日讓他去拓疆安土。然而這樣的機會遲遲不來,他只能做一些秘書和校對的工作。他的劍生了銹,簫在秋天里也只能呈現蕭索之意。最美好的事情莫過于去西山或南城賞花了。他和文友們騎著馬,飲酒作詩,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由于朝中的擠對,以及來自八卦的風言風語,龔自珍在京城的進取之路一敗涂地。他眼中所見,皆是滿目蒼涼。帝國的氣運和他的命運在這一年里形成了某個隱性的轉折點。他預見到摧枯拉朽的力量即將到來,但又滋生出無能為力之感。
此時,龔自珍與所有中年狀態的人士一樣,有了家室之累:正室側室,一雙兒女。他的身心經歷了疲憊的淘洗,他也并沒有在為官的時候實現財務自由。
安身未卜,立命未卜。龔自珍是個徹底的失敗者。除了擁有一些詩名之外——他在這一年沿途寫的詩,會因為傳誦早于他抵達家鄉。途中有道士在祈雨,聽說大詩人龔自珍來了,請他寫醮詞,他大筆一揮:“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詩人和巫師的雙重人格合體了,龔自珍扮演了那個求雨之人,他用文字的靈性呼吁天地之間來一場大的洗滌,將腐朽與沒落徹底掃除。
一路上,他不在醉中,便在詩中。朋友們與他談論詩文與學問,時政與蒼生,這給了他不少慰藉。從春天走到夏天,他才回到了杭州。
這似乎是一個悖論:士子究竟是該“以天下為己任”還是以“安頓性命為旨歸”。思想的流淌,驅動著不同的行事風格和人生路徑。48歲的龔自珍一無所有,兩手空空,他不停地否定自己,既沒有在小學領域接續上外祖父的學問,又沒有在做官上展示新的策動論力。他不過是譏人諷事,憤憤不平而已。有人稱他龔瘋子,背地里卻想這是一個憤青、刺頭、麻煩。
但那仍然是隱隱有個中年危機的。與俗子的中年危機不同,士子考慮的不是個人際遇、職場爭斗、子女教育,而是對一塊大陸共同的深情,對吾民同胞的休戚之感。多一些公平,多一些正義,多一些文明;同時,少一分謊言,少一分愚弄,少一分卑劣。
一切歸結于人心,龔言“人心亡,則世俗壞”。再好的制度,不去執行,仍是一張廢紙。國民教育如果僅僅是知識的獲取,而非智識的增長,那和皇帝的新衣有何區別?
人到中年,一切都還來得及嗎?能看到機運昌明的那一天嗎?為什么龔詩能一發千鈞,自此影響中國近代思想界的走向?一個詩人,一個命定的詩人,為何能天心人心,打成一片?
龔自珍仍沉溺于歸途中的酒與色,詩與友。他緩緩歸矣。家人與市民用超乎尋常的熱烈歡迎了他。求字、求墓志銘,絡繹不絕。他不得不在吃了半個月酒席后,又閉關半個月,完成稿債。他終歸是個名士,他的名聲,他的不妥協,傳遍了整個杭州,他的詩文被傳頌,行跡被模仿——他終于成了外公所痛恨的人。
他的名句在一點一點發酵,原來“美人如玉劍如虹”是他的句子啊。“但開風氣不為師”是多么美妙的境地啊。“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十年香”,又是何等的深情直白啊。
他考慮了接下來的生活,他要在杭州附近的昆山,把自己的別墅在山中建好。余生以待,他有一個自我休憩與優游的空間。如此退隱,豈非中年的急流勇退,豈非上蒼待我不薄的田園之樂?
他甚至偶爾內心一動,希望將沿途交好的歌伎召入府中,從此不問外事。但世俗與禮教的束縛又使他放棄了這個念頭,他將心跡都付諸詩篇當中。當人們閱讀這些詩篇時,不免有人罵他是玩弄女性感情的大混蛋。好幾次,他不敢面對歌伎與他的送別,倉皇駕船先行。有一位與他長情的女子早逝,對自己的母親遺言說,如果龔先生要來墓前,那還是可以的。
對于龔自珍而言,己亥(1839)是個由盛而衰、盛極而衰的年份,無論是他個人還是整個國家,都感受到無以復加的光榮的頂點,但燃料就快燒完了。大清的迷夢被隨后而起的鴉片戰爭(1840)拉開了屈辱的序幕;十年后,太平天國運動(1851)又將之沖擊得搖搖欲墜。
是龔自珍在己亥之年發出了先知的聲音,他在這一年的歸鄉之旅中,看到了大半個中國的真實現狀:人們的困苦和上流階層的無知,已經有了不可彌合的鴻溝。
“士子”最終會選擇“悄隱”,原因很簡單,有底線的斗不過沒底線的。在巨大利益面前,盤根錯節的關系會消耗人無窮的精力,智商與情商再高的人,也會受“看不見的手”的撥弄,這只手的名字叫“利益”。要么選擇進入這張大網,貢獻聰明才智,成為家族代言人;要么與之決裂,放棄既得利益,成為一個自謀出路、不負所學的個體。
人到中年后,容易變得犬儒而非奮起,社會空間又往往是鐵板一塊,不可理喻的事情太多,荒誕的新聞也不少,面對世事人心,“士子”的呼告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龔自珍為后人揭示了傳統中國的人格美學與生活美學,體現了個體生命的大視野和大情懷。
(摘自《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