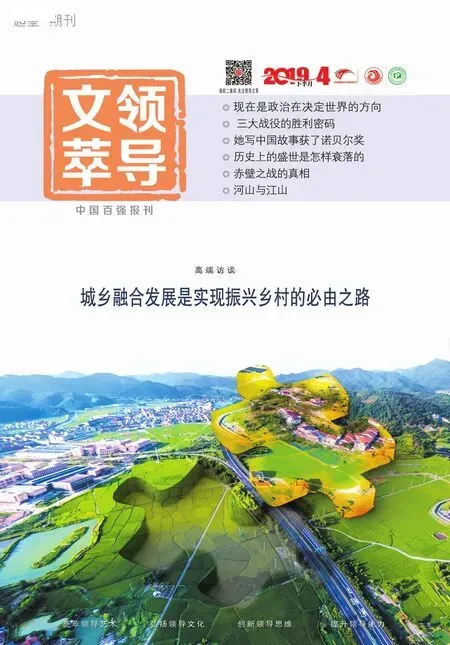“憂(yōu)患”與“資治”:司馬光與他的時(shí)代
鄧小南

司馬光于1019年出生,1086年去世,正值宋真宗晚年到哲宗即位初期,這一時(shí)段基本上是北宋王朝的前中期。宋代是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制度建設(shè)、科技文化領(lǐng)先于世界的時(shí)期;同時(shí)也是周邊被擠壓、內(nèi)政因循求穩(wěn)、面臨嚴(yán)峻挑戰(zhàn)的時(shí)期,戰(zhàn)略格局與政策應(yīng)對(duì)有諸多問(wèn)題。
北宋前中期的政治格局
北宋王朝建立八十年之后,長(zhǎng)期積累的內(nèi)外矛盾愈益突出,改革的呼聲逐漸高漲,范仲淹等領(lǐng)袖人物被推舉出來(lái),開(kāi)始推行新政。“慶歷新政”的主要綱領(lǐng)目標(biāo),是希望“法制有立,綱紀(jì)再振”,也就是要回到祖宗朝那樣的“理想狀態(tài)”下。司馬光沒(méi)有機(jī)會(huì)和范仲淹等人共事,但是他對(duì)范仲淹等人十分敬仰、欽佩,認(rèn)為“范公大賢”。
“慶歷新政”進(jìn)行一年多就中止了,學(xué)界通常稱(chēng)之為“夭折”,但是新政揭示出來(lái)的問(wèn)題并沒(méi)有解決,一些青年官僚經(jīng)常討論國(guó)事方針,感覺(jué)遲早還是要有改變。當(dāng)時(shí)有所謂“嘉祐四友”之說(shuō),指的是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和韓維,他們?cè)欠浅SH密的朋友,司馬光、王安石彼此之間都懷有欽敬之心。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主持“熙寧新法”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是“慶歷新政”二十五年之后,此時(shí)范仲淹已經(jīng)去世了,他當(dāng)年的同道,像富弼、歐陽(yáng)修、韓琦這些大臣都還在,但是他們這個(gè)時(shí)候都已經(jīng)超過(guò)六十歲了,可謂垂垂老矣,對(duì)于國(guó)政也有了另外的主張。神宗器重的王安石和司馬光都竭誠(chéng)國(guó)事,都觀察到當(dāng)時(shí)綱紀(jì)隳紊、風(fēng)俗弊壞等問(wèn)題,但對(duì)于治國(guó)理政的路徑,應(yīng)該采取什么樣的方略,意見(jiàn)全然不同。
面對(duì)內(nèi)外重重矛盾,王安石秉持“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堅(jiān)持推動(dòng)新法;司馬光卻認(rèn)為“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主張穩(wěn)健緩進(jìn)。針對(duì)國(guó)家財(cái)政問(wèn)題,王安石主張“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cái),取天下之財(cái)以供天下之費(fèi)”,開(kāi)源重于節(jié)流;司馬光則認(rèn)為“天地所生貨財(cái)百物止有此數(shù),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朝廷所謂“理財(cái)”無(wú)異于盤(pán)剝,對(duì)家國(guó)民庶并非益事。司馬光曾經(jīng)有書(shū)信勸誡王安石,王安石則斷然拒絕了司馬光的意見(jiàn)。兩人自此分道揚(yáng)鑣。宋神宗希望把他們都留在朝廷,但是兩個(gè)人堅(jiān)決不同意共事,神宗最終選擇了主張變法的王安石。
這一期間司馬光身為翰林學(xué)士兼侍讀學(xué)士,在講筵為神宗講授《資治通鑒》。時(shí)人曾經(jīng)稱(chēng)道說(shuō):“司馬公,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zhí)法殿中、勸講經(jīng)幄用,則前無(wú)古人矣。”從《司馬光日記》和《手錄》里可以看到,神宗經(jīng)常征詢(xún)司馬光對(duì)于政事的意見(jiàn),司馬光對(duì)神宗的態(tài)度也坦率誠(chéng)懇。其后,司馬光未接受樞密副使任命,曾經(jīng)以端明殿學(xué)士出知永興軍。后來(lái)到洛陽(yáng),開(kāi)始專(zhuān)心致志地修撰《資治通鑒》,一去十五年。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繼位,政權(quán)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手里,傾向于維護(hù)“祖宗之法”的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等人被召回朝廷,政局發(fā)生了明顯的轉(zhuǎn)折。
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司馬光被任命為尚書(shū)左仆射兼門(mén)下侍郎,就是當(dāng)時(shí)的首相,達(dá)到他仕履的巔峰。他回朝后提出的“十科薦士法”等建議,都被陸續(xù)采納,新法也先后廢罷。當(dāng)年四月,王安石去世了。此時(shí)司馬光身體已經(jīng)非常不好,無(wú)法上朝,但他還是手書(shū)致函另外一位宰相呂公著,稱(chēng)“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guò)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建議“朝廷特宜優(yōu)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fēng)”,對(duì)王安石有很高的評(píng)價(jià),希望朝廷優(yōu)予追贈(zèng)。由此可以看出司馬光作為政治人物的磊落情懷。
同年九月,司馬光去世。之后,北宋政治又有很多波瀾和翻覆,包括徽宗時(shí)期蔡京等人操弄的“元祐黨籍”黨同伐異事件,司馬光等人被追貶……這些都是司馬光的身后事了。司馬光離世四十年后,沉溺于“盛世”幻景中的北宋王朝,大廈轟然倒塌。
士人文化與“資治”意識(shí)
宋代的士人文化與前代有高度關(guān)聯(lián),特別是中唐以來(lái),經(jīng)過(guò)五代到宋,有延續(xù)也有變革,文化特色形成于整體的嬗變背景中。日本學(xué)者曾經(jīng)提出“唐宋變革論”,葛兆光老師也說(shuō)“唐宋文化的嬗變,在中國(guó)文化史上也許是最值得研究的題目之一”。變革涉及很多不同的方面,大體的趨勢(shì)是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宋代內(nèi)部的政治環(huán)境還算穩(wěn)定,北宋前中期的文化氣氛也相對(duì)寬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士人群體比較活躍,社會(huì)充滿(mǎn)了活力。
許多士人通過(guò)科舉脫穎而出,對(duì)于時(shí)代體制有高度認(rèn)同,對(duì)“家國(guó)”“天下”有強(qiáng)烈的關(guān)懷。其中的優(yōu)秀者以天下為己任,這種責(zé)任感集中體現(xiàn)于集體性的憂(yōu)患意識(shí)。“先天下之憂(yōu)而憂(yōu),后天下之樂(lè)而樂(lè)”的精神,不僅是范仲淹的高尚情操,像王安石、司馬光等人,也都有由當(dāng)時(shí)國(guó)家的格局背景所帶來(lái)的強(qiáng)烈憂(yōu)患意識(shí)。唐末五代的紛擾、北方政權(quán)的壓力、社會(huì)內(nèi)在的矛盾,在他們心中一直徘徊不去。
宋仁宗后期,王安石給皇帝的章奏中即指出,國(guó)家“內(nèi)則不能無(wú)以社稷為憂(yōu),外則不能無(wú)懼于夷狄,天下之財(cái)力日以困窮,而風(fēng)俗日以衰壞”;司馬光也說(shuō):“上下一千七百馀年,天下一統(tǒng)者,五百馀年而已。其間時(shí)時(shí)小有禍亂,不可悉數(shù)。”他又在《稽古錄》中說(shuō):“自古以來(lái),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可不戒哉!可不慎哉!”熙寧年間,有關(guān)變法利弊,他也曾經(jīng)對(duì)宋神宗表示:“臣之所憂(yōu),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資治”的意識(shí),正是在戒惕憂(yōu)患、期待治世的大背景下產(chǎn)生的。即便政治上失意之際,他們?nèi)匀徊环艞壸约旱闹螄?guó)理念,對(duì)于學(xué)統(tǒng)、道統(tǒng)仍然有所堅(jiān)持。
歐陽(yáng)修是北宋著名史家,他從不諱言?xún)?nèi)心認(rèn)知:“史者,國(guó)家之典法也。”韓琦也曾經(jīng)說(shuō),修史是要樹(shù)立“萬(wàn)世法”。這是士大夫集體性的政治責(zé)任感。神宗皇帝把司馬光進(jìn)呈的《通志》賜名為《資治通鑒》,事實(shí)上司馬光本人以史“資治”的意識(shí)也是很強(qiáng)的。司馬光的“資治”意識(shí),不僅體現(xiàn)在《資治通鑒》中的“臣光曰”,也不僅體現(xiàn)在這一部鴻篇巨制里,應(yīng)該說(shuō),他的言行舉止,和當(dāng)時(shí)許多士人一樣,處處都有體現(xiàn)。
余 論
所謂“資治”,首先是士大夫的自覺(jué)意識(shí);如何資治,當(dāng)然關(guān)系到治理者的襟懷、見(jiàn)解、能力等。《邵氏聞見(jiàn)后錄》中記載,北宋后期有人跟劉安世說(shuō):“三代以下,宰相學(xué)術(shù),司馬文正一人而已。”劉安世回答說(shuō):“學(xué)術(shù)固也。如宰相之才,可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為第一。”也就是說(shuō),歷代宰相中,司馬光學(xué)術(shù)上確實(shí)很強(qiáng),但是作為宰相,才干能力應(yīng)該能夠統(tǒng)馭四海,司馬光可能算不上第一等的人才。
司馬光是一位注重紀(jì)綱、正派端方的人物,為人處事篤實(shí)精勤。他的學(xué)術(shù)指向,在于經(jīng)世致用;他關(guān)心國(guó)家盛衰,關(guān)注生民休戚,也注意是非細(xì)節(jié)。他編修《資治通鑒》,不為褒貶好惡所拘,不逢迎不曲解,將嚴(yán)肅的考辨研究引入史學(xué)編纂。他不僅關(guān)注歷史過(guò)程,編修《資治通鑒》、撰著《涑水記聞》,也曾編修《書(shū)儀》《家范》;他對(duì)于禮儀軌范、名分次序、倫理道德的重視,都證明了他畢生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所在。他心目中的“資治”,意義所及,不只在于政治、軍事、國(guó)家財(cái)政,更在于“理想秩序”的建立。在《資治通鑒》卷一,他就指出:“何謂禮?紀(jì)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可以說(shuō)是憂(yōu)勤惕厲,念茲在茲。
現(xiàn)在可以看到存世的司馬光尺牘、手稿,字跡端勁方正。另外,跟他的仕履有關(guān)的有:日本熊本縣立美術(shù)館收藏了熙寧二年(1069)司馬光充史館修撰告身,臺(tái)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了元祐元年司馬光拜左仆射的告身。
總體上看,司馬光是北宋中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蘇軾稱(chēng)贊司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誠(chéng)心自然,天下信之”。我想這個(gè)評(píng)價(jià)是比較公允的。
(摘自《文史知識(s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