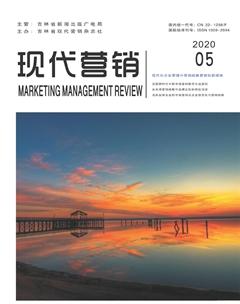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新鄉賢參與模式創新研究
摘要: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發揮新鄉賢在推動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作用。當前,新鄉賢參與的聯絡和組織機制相對不健全、參與的制度激勵機制相對缺乏、參與監管不足、存在權威異化風險等問題。化解這些問題,需要理論聯系實際,進行參與模式的創新,從而切實發揮新鄉賢獨特的優勢,助力鄉村的振興發展。
關鍵詞:鄉村振興;新鄉賢;參與模式
一、相關研究述評
(一)對新鄉賢的研究現狀
1.新鄉賢概念界定
對“新鄉賢”這一概念的界定學術界還未完全統一,但其主要內涵來源于“鄉賢”的概念。錢念孫(2016)提出新鄉賢的概念:“有德行、有才華,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謂之新鄉賢。再寬泛一點,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動,愿意為農村建設出力的人,都可以稱作新鄉賢”[1]。郎友興等(2017)認為新鄉賢是農村精英的代表,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優勢,他們是對農村發展做出一定貢獻的人[2]。蕭子揚和黃超(2018)基于對社會知覺和中華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的理解,強調新鄉賢是建立在主動的自我知覺的狀態下,處在后鄉土中國這一社會背景之中,一切愿意為鄉村發展服務的人[3]。學界依據空間對新鄉賢進行劃分,張頤武(2015)依據主要居住地和發展事業地把新鄉賢分為在場的新鄉賢和不在場的新鄉賢。在場的新鄉賢如農村優秀的基層干部、道德模范、退伍軍人和創業先鋒等,不在場的新鄉賢如農村走出去的企業家、教育科研人員、黨政機關干部等[4]。筆者認為,在當今時代,新鄉賢就是有比較直接的鄉土淵源,在鄉村里有德行、有才能、有聲望,深受當地民眾尊重、敬仰和擁護,能對家鄉建設建言獻策、出錢出力的社會精英人物。
2.對新鄉賢參與模式的探索
李思琪(2018)認為新鄉賢的發展經驗有3個方面:一是在發現培養階段,通過多種形式發現和培養鄉賢帶頭人,鼓勵他們回到鄉村參與社會治理,并提供相關的培訓,以此來提高新鄉賢的服務水平;二是在實踐活動環節,對新鄉賢群體加以引導,并建立相應的常態化工作機制;三是建立激勵機制,一方面可以通過互聯網對新鄉賢的事跡加以宣傳,另一方面可增加新鄉賢群體的儀式感和認同感[5]。劉昂(2019)認為,新時代鄉村治理實踐中,培育和發展新鄉賢必須保障新鄉賢的經濟地位、健全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機制、激發新鄉賢的價值認同[6]。蕭子揚和黃超(2018)認為目前新鄉賢在農村的主要任務是提升農民的知覺能力,引導和推動農民參與農村治理,帶領村民更為科學地治理鄉村。他強調農村社會工作者也是新鄉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未來農村變革和知覺運動中起著倡導和引導的作用,扮演專業型和專家型參與和協助的角色[3]。梁新莉(2018)認為,新鄉賢要有一定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在村兩委的領導下,應保障新鄉賢群體對于村務在建議、監督等方面的權利[7]。張露露、任中平(2016)認為要擴大新鄉賢的作用領域,建立相關激勵制度,鼓勵新鄉賢在多個方面 “登臺亮相”。通過各類活動吸引新鄉賢返鄉,參與現代鄉村建設,并通過土地產權激勵新鄉賢在鄉村落地發展,切實保障新鄉賢群體的基本利益[8]。
(二)新鄉賢的文獻評述
“新鄉賢”作為特殊的社會資本,是我國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探索。回顧相關研究,不難發現,現階段仍然存在“反思過多,實踐過少,口號過多,落地較少”等問題,具體包含:其一,概念尚未統一,存在過度解讀。目前學術界對于新鄉賢的定義并未形成統一,尚存在一些分歧,導致社會對該群體的認知也存在偏差。學界對新鄉賢的反思性研究太少,很少有文章運用批判性思維去看待新鄉賢的作用。新鄉賢是由若干個體組成,人均有趨利避害的天然特征,這一組合并非是完全理性人的組合,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其作用的發揮需要領導與控制,也需要監督與制約。其二,視角選擇過大,理論提煉不夠。大多文獻均選取宏觀視角探討新鄉賢的作用,探析其在鄉村場域中文化、經濟、道德風尚等方面的基本作用,觀點大同小異,重復性研究較多;其三,對新鄉賢的參與路徑探索力度不夠。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關鍵在于如何產生和培育新鄉賢以及如何完善和創新參與模式,但是目前這一方面的研究還停留在比較初步的階段。而且,新鄉賢作為鄉村振興和農村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鄉村發展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議題。因此,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如何用好新鄉賢資源,如何調動新鄉賢的參與積極性,讓其積極參與到鄉村治理和鄉村振興中來,以及如何隨著時代和地域變遷調試和創新參與模式,這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是本研究所關注的重點。
二、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中所面臨的問題
(一)新鄉賢參與的聯絡和組織機制相對不健全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鄉村“空心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傳統熟人社會逐漸向半數人社會過度,宗族意識淡化。在鄉村中雖然不乏具有奉獻精神、樂于參與公共事務的退休官員、退休教師、退伍軍人、技術員、鄉鎮企業家、經濟能人、致富帶頭人、大學生村官等,但由于缺乏相互認識和聯系的渠道,加上部分村民和村干部存在一些不當認識,對新鄉賢返鄉參與鄉村治理產生偏見和誤解,甚至出現懷疑和排斥現象。在參與的實踐中,往往偏重“官鄉賢”和“富鄉賢”的參與,而忽視“文鄉賢”、“德鄉賢”和“草根鄉賢”的參與。因而,這些群體在村民中的知曉率、聲譽和威望并不太高,其反哺鄉梓的愿望往往因缺乏渠道和媒介而難以實現,能稱之為“新鄉賢”的人總體數量仍然不多。
(二)新鄉賢參與的制度激勵機制相對缺乏
社會轉型期,受市場經濟發展因素的影響,新鄉賢文化很多地方日漸式微,一些企業家、經濟能人、致富帶頭人忙于“悶聲發大財”。同時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只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社會效益,未能看到新鄉賢在帶動本地經濟、文化發展中的帶頭引領作用,忽視了對本地新鄉賢激勵機制的制定。每個鄉村都有到城市工作或生活的領導干部、律師、醫生、教師、會計、退伍軍人、技術員、經濟能人、企業家等。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對家鄉都有難以割舍的情懷,有濃濃的鄉愁,也樂意為家鄉的經濟、文化建設出謀獻策、出錢出力。由于這些身處異地的新鄉賢返鄉面臨較多的問題和困難,如部分新鄉賢返鄉沒有居住場所、缺乏相應的生活保障等,這些問題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積極性。因此,建立和完善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激勵機制已成當務之急。
(三)對新鄉賢參與的監管不足,存在權威異化風險
城鄉建設涉及大量惠農資金、拆遷安置資金,村干部巨貪、農村黑惡勢力抬頭等情況屢有發生,此外,還有部分新鄉賢在利益誘惑面前蛻化,存在權威異化的風險。村民自治、民主協商演化為“鄉賢治理”、村支委功能弱化,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可能異化為某人或某姓的“一言堂”,并以家族鄉賢、宗族鄉賢為代表,與村支委發生沖突。新鄉賢的精英俘獲可能導致部分資本代理人自身或其尋找的代理人成為新鄉賢[9],一旦作為“資本的邏輯”代理人的人成為村支委成員或新鄉賢,或者村支委成員或新鄉賢蛻化為資本代理人,他們必然切實維系“資本的邏輯”,并不斷實現新的“物的依賴”“資本的邏輯”[10],其經濟訴求、政治訴求的實現,有可能使村莊在短期繁榮后對村莊長期的整體社會福利造成危害,或者形成新的城鄉剝奪或地區剝奪,對其他地區的長期整體社會福利提升造成危害。
三、鄉村振興背景下新鄉賢參與模式的創新路徑
(一)明確新鄉賢的標準,積極擴大與培育新鄉賢
首先,要明確新鄉賢的標準。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選出符合標準的新鄉賢,寧缺毋濫,確保選舉出來的新鄉賢得到老百姓的認同。建立在冊新鄉賢名單,根據新鄉賢的行業、創業地等進行分類并建檔立卡。其次,在“引”上謀新招,建立有效激勵機制。打好鄉情牌、鄉愁牌,促進各路人才“上山下鄉”投身鄉村振興,要在幾類重點群體上下功夫。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劉奇認為,重塑新鄉賢要著重從幾類群體上努力,一是離退休人員葉落歸根;二是大學生村官;三是城歸農民工;四是接受優秀家風家教熏陶的世家大族、名門望族的后裔;五是新富賢能者[11]。再次,構建多層次新鄉賢聯絡溝通平臺,形成內外新鄉賢協作機制。依托鄉情鄉愁,打好“感情牌”,定期舉辦新鄉賢大會,建立新鄉賢微信交流群,定期舉行座談會或登門拜訪,交流成功經驗,敘敘濃濃鄉情,通報家鄉發展狀況,讓新鄉賢了解自己家鄉的發展情況和今后發展中需要得到何種資源支持。最后,著力打造新鄉賢活動平臺,提高新鄉賢參與度。以新鄉賢理事會和新鄉賢工作室為基礎,成立諸如“矛盾糾紛調解工作委員會”、“產業發展指導委員會”等組織,為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提供有效的平臺支撐。
(二)創造良好的新鄉賢投資環境和支持體系,推動鄉村經濟發展
其一,完善新鄉賢回歸項目在審批、用地、財稅、金融等方面優惠政策。對重大鄉賢回歸項目,實行“一事一議”,可以給予一定的稅費減免。對于經濟貧困的鄉村,可以設立扶貧基金,提供企業貸款。其二,落實好新鄉賢企業家們在土地征收、土地使用、占用土地審批、資源實現共享方面的服務工作,適當放寬土地使用范圍,在土地使用費和使用時間上給予優惠。其三,夯實與完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新鄉賢群體返鄉創業,必須把改善農村基礎設施作為“先手棋”,著力抓好農村水、電、路、氣、房、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城鄉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農村基礎設施提檔升級,讓新鄉賢真正在鄉村留得住。
(三)完善參與機制,使多類型新鄉賢成為鄉村多元治理的重要力量
一要重視并充分發揮“文鄉賢”“德鄉賢”“草根鄉賢”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鄉土化。通過發揮新鄉賢遵紀守法、尊老愛幼、樂于助人、熱心公益,勇于犧牲,樂于奉獻等先進帶頭作用,宣揚優良家規家風、鄉規民約,提升鄉風文明,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鄉土化,如加強鄉村普法宣傳、推動鄉村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等,使鄉村居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效消除傳統道德風俗約束力下降、鄉村原子化帶來的村民精神空虛、邪教興起、低俗文化大行其道等不良現象。二要通過文化研究、村莊規劃、公益慈善等不同于傳統宗族、迷信、道德等傳統象征符號的新的象征符號塑造,來強化包括新鄉賢在內的所有村莊居民對于村莊的歸屬感,提高村莊凝聚力。最后,要充分發揮新鄉賢的示范帶頭作用,激活農民的主體意識,引導農民參與到鄉村治理中來。完善相關動員機制,重視新鄉賢的引導作用,加強保障,讓農民從“看不見”到“看得見”,從“看得見”到“給意見”,從“給意見”到“有主見”,從而激活農民的創造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積極投入鄉村振興事業中去[12]。
參考文獻:
[1]吳小杰.新農村呼喚新鄉賢——代表委員暢談新鄉賢文化[N].光明日報,2016-03-13(1).
[2]郎友興,張品,肖可揚.新鄉賢與農村治理的有效性——基于浙江省德清縣洛舍鎮東衡村的經驗[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7(04):16-24.
[3]蕭子揚,黃超.新鄉賢:后鄉土中國農村脫貧與鄉村振興的社會知覺表征[J].農業經濟,2018(01):74-76.
[4]張頤武.重視現代鄉賢[N]. 人民日報,2015-09-30(007).
[5]李思琪.新鄉賢:價值、祛弊與發展路徑[J].國家治理,2018(03):28-36.
[6]劉昂.新鄉賢在鄉村治理中的倫理價值及其實現路徑[J].蘭州學刊,2019(04):165-172.
[7]梁新莉.新鄉賢反哺:鄉村治理的文化路徑選擇[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03):47-49.
[8]張露露,任中平.鄉村治理視閾下現代鄉賢培育和發展探討[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8):57-63.
[9]何倩倩.“鄉賢治村“調查[J].決策,2015(4).
[10]楊華、羅興佐.階層分化、資源動員與村級賄選現象——以東部地區G鎮調查為基礎[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
[11]張玉玲.鄉賢、鄉土、鄉愁:探尋鄉村振興的文化力量[N].光明日報,2017-11-30(016).
[12]汪星星.鄉村振興要激活農民主體意識[DB/OL].宣講家網,2018-08-01.
作者簡介:
夏偉(1988—),男,安徽六安人,碩士,中級講師,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