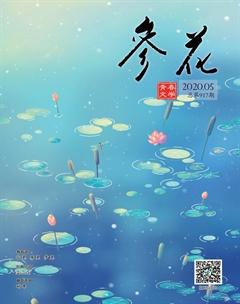七歲、八歲關鍵期,我陪你度過
王瑩
“這個字寫得這樣不行,再重新寫去!”孩兒爸頭也不抬地說道。
“我不寫!”孩兒反駁道。
“你馬上去寫,聽見了嗎?”語氣明顯不耐煩了。
“不去,就是不去!”孩兒非常生氣,對其表現出不配合。
“你寫不寫,我還治不了你……”孩爸說時遲那時快,飛快地從腳上取下拖鞋,憤怒地舉起手中的拖鞋,面向一個七歲的孩子,只見孩子恐懼地望著他,不說一句話,滿臉的憤怒,小手氣憤地緊緊地握著,不服輸地瞪著他爸……
這是疫情宅在家的第二十五天的時候,發生在我們家的一幕,我不知道這鞋能不能落下,若落下,我想得花多長時間去修補孩子心理上的創傷,若不落下,那么他舉起的一瞬間,起什么作用呢?只是為了發泄自己內心的不滿嗎?說實話,此刻,我既為為父者感到憂心忡忡,也為孩子感到可憐。我們知道孩子的成長,一般都要經歷三個叛逆期,即兩三歲時的“寶寶叛逆期”、七八歲時的“兒童叛逆期”、十二歲以后的“青春叛逆期”。其中,七八歲時期是最令人頭疼、最討人嫌的叛逆期。正如俗語所說的“七歲八歲討人嫌,惹得小狗不待見”。可孩兒爸并不知道這個年齡段意味著什么,即便知道這個時期是叛逆期,也并不知道該采取什么方式來解決,來引導。由此,一場談話即將展開……
“你覺得這種方式孩子能聽你的嗎?”
“能。”
“達到你想要的效果了嗎?”
“那是因為還不夠狠,打得不夠。”
“為什么你認為教育孩子時打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小時候都是被打大的,怎么的?”
…………
原來這一切行為的背后都源于原生家庭。在中國的教育中,特別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溝通不是很常見的事,有很多家長與孩子也不知道如何與子女進行有效的溝通,有的父母一開始就將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地位,有的父母僅僅暫時放下自己盛氣凌人的嘴臉,有的父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沒有耐心……在這種隱形的對立面下,不少孩子就選擇了沉默,我們家孩兒爸是這種情況下受害的一員,所以延續了父輩的教育方式,渾然不覺有什么不妥。實際上,他應該反省一下為什么這種方式效果不佳,在我冷眼看著這一對話期間,是缺乏責任心,耐心甚至愛心導致。所心當我知道這行為背后的原因后,感到首先應該改變的是大人,大人的憤怒是因為自己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再來一次,你沒看見你掌握不好球嗎?”
“有本事你來呀!”
“是你練球,不是我練球。”
“我還不練了!”
“你練不?讓你練就得練,你還反了嗎?”
又是一次失敗的引導,其語言溝通的藝術性不言而喻,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嘆,有本事的家長、會教育的家長,會讓孩子認同自己,喜歡自己;還需學習、有觀念缺失的家長們,面對孩子們的逆反,多會采用暴力方式來解決。我個人覺得,當孩子碰到困難時,遇到挫折時從孩子的不是中,總能找到值得表揚的地方,總給孩子良性暗示和正面刺激,這樣下來,孩子慢慢就會獲得成就感,把為時間而練球,改成為技能而練。當他不再和家長對抗,心里真正想要練好球時,他是不在乎多練一會兒還是少練一會兒的;而且認真練半個小時的成績會好于磨洋工一個小時。若是以上對話,換成另外的語言,孩子或許更能接受:
“這次球打得不錯啊,技術掌握得越來越好,咱們再來挑戰一次,看看怎么樣?”或許孩子這時候有情緒,實在不愿練了,那么就做個順水人情,“來,咱們一起休息一下。”趁機談談剛才打球時成功的地方是緣于耐心、穩定,出現失誤的地方是過于急躁,“來,咱們心平氣和地再來試試”。我想這樣一來交流溝通,是不是能讓孩子更能接受,而不是一味地督促打球,練球,不愿練的時候還要強制要求練,即便孩子不說話在高壓之下練了,效果怎么樣呢?
我始終都相信一句話:在親子教育中,你想要孩子成為什么樣的人,那么你就去成為那樣的人。所以,當孩兒爸屢戰屢敗的情況下,他當起了逃兵,“我說什么他都不聽”,這話一是為了逃避責任,二是說明已經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式。所以,當這個時候,我們坐下來談談問題出在哪兒,為什么每次都失敗而歸,顯然不是孩子的問題,于是我建議他讀讀幾本育兒方面的書,帶著自己的無奈、失敗感來讀,用心地讀,能從這本書中汲取到多少解決問題的方法。想要孩子達到理想中的狀態,首先自己得是這個狀態中的人。用自己的言行去感染他,影響他。
對于這個階段的孩子,我們在教育的時候,需要抓住問題的關鍵點,講究一定的策略和方法,用孩子喜歡的方式和孩子達到合作。什么樣的方法和策略是孩子喜歡的,什么樣的溝通方式是孩子愿意合作的呢,需要我們每一個為人父母者好好學習。親子的教育,我最期盼的大概就是一起成長,在愛、理解、尊重、包容與約定的規則下,共同進步,砥礪前行。
(作者單位:淄博高新區實驗小學)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