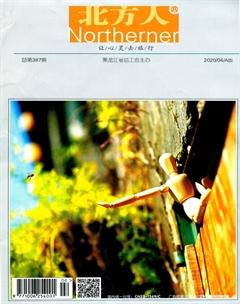“進食障礙”是種病
王景爍

瘦是有止境的,對瘦的渴望沒有。
最瘦的時候,身高148厘米,體重24公斤,身體像根“火柴桿”,盧佳羽還是覺得自己不夠瘦。
過去3年里,北京的這位中學生通過節食瘦了30多斤。“消瘦”不足以形容她。因為攝入脂肪過少,影響了雌激素的合成,她停過月經。
她對進食這件事斤斤計較。某種刻板程序遙控了她的進食:她需要在固定的時間進餐,一頓飯能吃一個小時;碗盤要按固定順序擺放;水果要切成指甲大小;米飯幾乎是一粒一粒咽下。她列過一份不容出錯的食譜,打印后貼在墻上,家里請過2個阿姨最后都選擇了辭職。她為了控制煮雞蛋的時間而購買了計時器。家人給她的杯子里加多了牛奶,也會導致她的大喊大叫。就連在課堂上,她也常常為計算卡路里而走神。
這種狀況在2016年——她13歲時出現。第二年,母親在社交網絡描述了她的情況,有人提醒要去就醫。她確診了。
官方定義是“進食障礙”。這個孩子符合醫生對進食障礙基本特征的描述:進食行為異常,對食物和體重、體型過度關注,多發于年輕女性——根據醫學文獻,女性與男性患者的比例超過了10:1。這是精神疾病的一種。
常人對它幾近無知。在2019年3月之前,百度百科詞條里,進食降礙還被列為消化內科疾病,主要癥狀被描述為,“營養不良,消化道及內分泌癥狀”。
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進食障礙學組副組長、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綜合三科病房主任李雪霓作為專家參與了詞條的修改工作。更新后的版本是:“精神科疾病,由個體因素、家庭因素及社會文化因素造成”。
醫生李雪霓見過不少進食障礙患者的死去。她所在的北大六院,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是國內最早治療進食障礙的醫院。
進食障礙本身并不致死,但過度消瘦會引起心律失常、器官衰竭,進而導致壽命縮短。通常情況下,患者會產生抑郁情緒。有人死于自殺。
據李雪霓介紹,按照醫學論文公開報道的情況,進食障礙群體有個“四分之一”定律:不干預的話,1/4的人可以自行痊愈;1/4的人會好轉,帶著癥狀正常生活;1/4的人患病慢性化,生活受到影響;1/4的人可能會死掉。
過去很多年里,醫學界沒人認為中國存在進食障礙這種疾病。
1987年,中國大陸幾乎沒人聽說過進食障礙時,張大榮的導師、精神病學家沈漁邨就提出,這將是未來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
沈漁邨后來成為中國精神病學領域的第一位院士,她的預言已經部分成真。
北大六院綜合三科統計,2002年到2012年,該院住院的進食障礙患者從年均20余例增長至180余例。開了專科病房之后,李雪霓曾以為會缺乏病源,可一段時間后,發現這個問題根本不存在。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進食障礙診治中心負責人陳玨說,進食障礙曾被認為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在中世紀就有關于自我絕食的記載。自20世紀50年代起,西方文化“以瘦為美”之風愈演愈烈,進食障礙的發病率也逐年上升。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還沒完全解決溫飽問題,加上傳統文化中孩子以胖為美的觀念,進食障礙在當時的中國并不是一個突出的問題。然而今天,溫飽問題解決后,人們吃飽了飯,進食障礙又多了。
吃不下飯的風險,很多人意識不到。
最瘦的時候,盧佳羽肋骨根根分明,后背骨節清晰可見,臉色蠟黃,頭發干枯、掉落。有人形容她“瘦得就像筷子似的,一碰可能就折了”。她身體容易發冷,冬天在開了熱風的房間,即使蓋了兩床被子,還是感到冷。
另一位患有進食障礙的學生描述,走路時,她總感覺腳懸著沒著地,好像一陣風都能把自己吹倒。教室外一排柜子的柜門反彈力度有點兒大,她曾被彈倒在地。
北京協和醫院臨床營養科副主任陳偉為不少進食障礙患者做過胃鏡,他見過的胃壁,有的跟“一張紙一樣,幾乎要破掉”。
進食障礙主要分為厭食癥和貪食癥。貪食癥患者會出現反復發作、不可控制的暴食,并在暴食后采取誘導嘔吐等代償行為,避免體重增加。因為暴食,胃會被一點點撐大,胃壁也越來越薄。
陳偉認為,進食障礙由于多發于青少年成長發育期,對人的影響十分多元。直接的反應是,厭食癥患者因為長期不吃東西,胃腸排空能力變差。他解釋,瘦到一定程度后,人體產生“保護措施”,食物不會被快速消耗,有的患者48小時前吃下的東西還停留在胃里。
這位營養科醫生指出,人體的許多功能能夠跟隨營養狀況動態變化,但這些患者即使營養恢復,“仍有一些機能無法恢復到之前的健康水平”。
這些人或多或少地伴有便秘、脫發、失眠、骨質疏松、卵巢早衰等癥狀。長期營養不足,神經元的功能受到影響,也會造成精神抑郁、注意力難以集中等情況出現。
即使是現在,進食障礙的確切病因也是未知的。一個共識是,生病的前提是極端減肥行為和個人、家庭、社會因素碰在了一起。
盧佳羽小時候,父母先是分居,后來離婚,她跟著母親從國外回到中國,頻繁地搬家,換學校。她覺得“交朋友是世界上最難的事”。為了掩飾尷尬,一個人在學校食堂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午飯,之后就在教學樓繞圈打發時間。她成績突出,當過辯論賽的最佳辯手,也曾在舞蹈大賽里斬獲亞軍,她同時抑制不住自己要去“討人喜歡”。
李雪霓醫生形容,就像是“一個個鎖扣都扣在一起了”,要全部解開是件麻煩事。治病的同時,還得治人。
對盧佳羽來說,減肥是一切的開端。她13歲那年生了一場大病,服用激素藥物,看著自己的臉“像饅頭一樣發起來了”。
她的想法是:只要瘦下來,一切都會變好的。
此后她視高熱量為敵人。1千卡等于4.186千焦,她把卡路里對照表背得滾瓜爛熟。為了減少攝入油脂,這個少女告別了生日蛋糕和蘋果派。
一般來說,人體BMI指數低于18.5屬于過低,低于13就是高危。盧佳羽的BMI指數最低時只有11,令她的母親憂心忡忡,因為很多醫院不敢接收BMI低于13的患者。
盧佳羽記得,體重秤上遞減的數字帶來過成就感。家人覺得她有驚人的自制力,朋友的夸獎接踵而至。
她吃飯的緩慢也變得“全年級有名”。和同學一起用餐時,她會偷偷把肥肉和主食塞在餐巾紙底下,假裝自己吃了。
有人甚至從家庭餐桌上退出,躲進自己的房間吃飯。在這些家庭里,圍繞著吃飯產生的問題層出不窮:有人無法控制自己,經常摔東西罵人;有的患者自己吃不下去,喜歡看別人吃飯來“望梅止渴”,一位疼愛女兒的父親因此連吃了5個饅頭,等到第六個真的吃不下了,只能藏在褲兜里。
“為什么不吃飯?”這是厭食癥患者被問到最多的一個問題。其實,他們并不像這種疾病名稱的字面意義那樣“厭惡”食物。很多人都曾在網上搜索過一些高熱量的食物圖片,將圖片一張張劃過,常常一看就是一下午,隔著屏幕“吸收養分”;有人的直播平臺賬號關注列表里,是一連串的“吃播”主播。
目前在中國,能為進食障礙患者提供專業化病房的醫院,主要有北大六院和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進食障礙診治中心。許多外地患者出院后很難在家鄉復診。
生活在美國,何一了解到,僅在波士頓,這樣的機構至少就有5家。
這兩年來,中華醫學會心身醫學分會進食障礙學組培訓了來自各地的醫護人員,有的學員回到當地后,開設了進食障礙門診。
但是,門診單一科室能做的很有限,要病房收治還需要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團隊,懂營養的、研究心理的,需要時間。李雪霓曾去英國的進食障礙中心參觀學習,她羨慕人家的治療團隊和硬件條件。她記得對方告訴她,是花了20年才變成這樣。“我想我們也是有希望的,也許用不了20年。”
北大六院的醫生已經明顯地感覺到,過去,患者要花3年-5年才能找到癥結,但現在,這個時間被縮短為3個月到半年。
這些年,志愿者老曹看到,盡管醫護力最日臻成熟,還有為數不少的患者徘徊在社會的邊緣:有人消極不自救,有人接受了治療但還是無法恢復社會功能,讀不完高中。他們在與進食障礙的搏斗中,度過了青春期,邁入了成年。因為病情,只能應聘到一份工資低于自身能力或平均工資水平的工作,小心翼翼地生活。“就像把一個沉重的龜殼背在身上,他們卡在中間,如履薄冰地負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