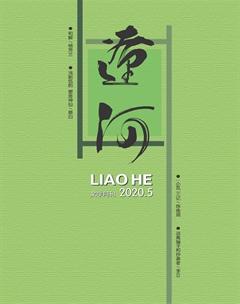“小瓦”三記
陳魚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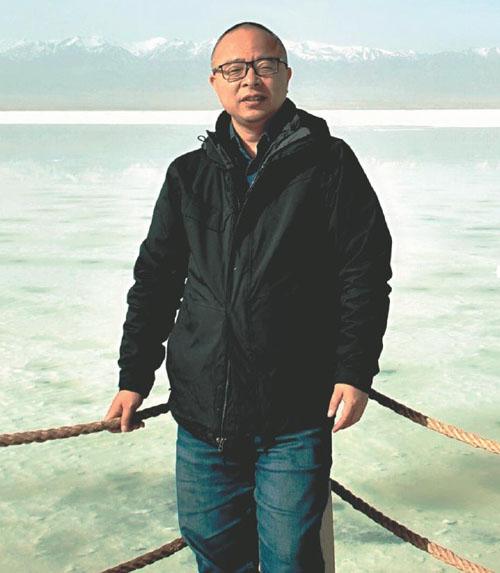
露營“小瓦爾登湖”
與其說“小瓦爾登湖”是一個湖,不如說是一個由人工堰塞而成的小水庫。湖面呈Y狀,由兩條溪谷匯聚一起后截流而成,她躺在山的最高處,與城市的距離大約三個小時。
大概是年代久遠的緣故,就近采石壘成的水庫堤壩上長滿了比人還高的雜草,看不到鋼筋水泥的痕跡,它們本來就是山的一部分。在堤壩下面,是一條蜿蜒曲折的高峽深谷,更遠處隱約著一個破敗的小村落,小水庫可能是這個村落的供水池。聽說這個村落里的村民早在十多年前就移民到城市居住,供水池自然也就廢棄。往往廢棄的就成為人文,因為廢棄,被稱作“小瓦爾登湖”的水庫與自然無異。
正如香格里拉和桃花源是人們的理想國一樣,瓦爾登湖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心靈家園。
我之所以把這里稱作“小瓦爾登湖”,就是因為她隱秘、僻靜、自然,遠離塵世的是非和喧囂,除此還有被“廢棄”后的自由。在這里,任何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于她徒然,任何與人類有關的活動和她無關。她屬于她自己,被我發現是她的不幸,卻是我的幸福。我需要一整個夜晚,或者更長的時間,向“小瓦爾登湖”傾訴我的一切,盡管我的闖入有些輕狂,盡管這滿眼的湖光山色不會為我動容,但我還是要留下來,試圖用一領帳篷的想象與她一夜廝守。
“小瓦爾登湖”的堤壩是平坦的,只要斬除那些與人齊高的雜草,就能在上面搭建帳篷,這個過程當然不能忘了將雜草鋪在帳篷下,使之成為與今晚的夢最親近的朋友。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將隨身帶來的酒和牛肉饕餮一番,然后趁著酒興,除去全身的衣物,跳進被“廢棄”的湖水里感受自由,這可能是人類融入自然最有效、最放肆,以致成本最低廉的“壯舉”了。
在酒足飯飽后,我點燃爐火,舀一碗湖水燒煮,順手在水中投入一把馬尾松針葉,沏一壺別致的松針茶,在彌散的松香里等待夜合上雙眼。
“小瓦爾登湖”的夜黑得很快,隨著一層暮靄漫過來,一杯松針茶還沒喝完,山色與天色、樹影與人影就已融為一體,如果還有一點點的慰藉,唯一只有湖面上的浮光掠影了,她們低調地白著,似乎在等待夜色沉入湖底。對于光的追逐,我的想象不敢更進一步,她們必然要從我的眼睛里消失,最后,連我的眼睛也成了擺設,長在臉上與隱藏腳底沒有分別。
“小瓦爾登湖”的夜黑得固執,完全與我的想象背道而馳。于是我只能躲進帳篷,用兩平方米的帆布世界抵御夜的侵入。雖然毫無意義。
不過帳篷還是給了我一些信心,至少我可以借助它遮蔽湖面上傳來的水汽,并且收聽到自己呼吸的聲響。然而最可怕的事情終于發生了,湖面上沒有出現星星的倒影,取而代之的是風雨雷電的全面引爆。閃電瘋狂地鉆進帳篷,如同一條條閃耀的繩索將我緊緊捆綁;驚雷似乎要把帳篷掀翻;風在耳朵上盡情地撕咬;雨水變得富有節奏。帳篷開始走向風雨飄搖,我的心也隨之晃蕩……
于是我試圖用一場睡眠來解決這場力量懸殊的戰斗。合上雙眼,讓世界與我無關。
可是我無法回避世界。從一數到百,然后倒回來,那些被莊子稱作“天籟”的玩意總是充斥著帳篷的每一個角落,包括我刻意造作出來的鼾聲。蜷縮在帳篷里,我想起宋人蔣捷的《虞美人·聽雨》一詞,今夜的我聽雨帳篷,又將豢養怎樣的情愫?好在秋天還算有些良心,在幾陣肆虐之后,風雨終于走向冷靜。
當偌大的山谷突然了無聲息,卻讓我有一種措手不及的驚恐,整個心好像被掏空,很快又被寂寞霸占。于是我發瘋般地用手機向山外的人類發送求救短信,包括女人和男人,甚至輸入一個隨機號碼,我愿意把這個號碼的主人當成今夜的有緣人。一條條短信在山谷間回蕩,有些被湖水打濕,有些流入民間,在等待回信的過程,寂寞更加寂寞,寂寞演化成恐懼。
是的,“小瓦爾登湖”已讓我感到戰栗。我想此時,任何蟲豸和野獸的隨意經過都有可能讓我死于非命,從此讓“小瓦爾登湖”天下揚名。
山中無歲月。我渴望夜早點過去,沒有比陽光更親的親人。夜變得更加漫長,時間像墜落的松針,一枚枚地生生扎進我無處逃遁的胸口。沒有比寂寞讓人更加痛不欲生,我躺在帳篷里,似乎就躺在一座墳墓中,雖然沒有泥土的重量,也不管有沒有風雨雷電的騷擾,無聲的對峙就足以讓我感到窒息。
面對寂寞,如果湖里躍上鯉魚精,或者從山間顯出狐貍精來,只要能陪我說話,我就會試著去愛上她。理由就這么簡單,從來都是。無論我的想象多么卑賤,夜總是要露出她的底色來。
夜的底色自然是白色。有人說這是被“小瓦爾登湖”的湖光漂白的,也有人說是被周圍兀立的山峰頂破的。其實這些都不要緊,要緊的是經過一夜的糾纏,“小瓦爾登湖”還在,秋天還在,我還能醒來。我不知道昨晚的帳篷外,鯉魚精和狐貍精是否來過,抑或是來了一只狗熊,借著“小瓦爾登湖”的波光,偷走了我的魂魄。
重返“小瓦爾登湖”
在去年秋天一場即將到來的臺風之前,我帶著帳篷和干糧闖進了樂清西山的深處。這里亙古的山巒已逐漸麻木于人類對她的抒情和想象,而一個藏得比山巒更深的小水庫卻還要與人類最后的遺棄和偏見相抗衡,因為她是廢棄的,所以顯得安寧;因為她是孤單的,所以顯得自我。于是我把這個小水庫命名為“小瓦爾登湖”,不為附庸梭羅留下的意象,只想給自己找一個親近自然的理由和可能。所幸臺風到來之前的時間總是靜的,那一天下午的“小瓦爾登湖”與秋天“靜”在一起,與我廝守在一起,我用一領帳篷將“小瓦爾登湖”收藏,借那里的“靜”下酒、說著夢話……
直到深夜臺風登陸,“小瓦爾登湖”開始波瀾壯闊,露出了難得的崢嶸,原來她在這里一直等我這個陌生人的到來,用一個夜晚的激動來表達一年、十年,或者更長時間的話語。那一夜我讀懂了“小瓦爾登湖”的聲音,也愛上了她的性格。
從秋天到春天,我用將近半年的時間寫著一首關于“小瓦爾登湖”的詩。在詩中,我極力避免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的出現,更多的副詞讓我對“小瓦爾登湖”的追憶像一枚繡花針般刺穿了一個個酣睡的夜晚,我已無法分辨疼痛和負罪的界限,我必須醒來,在世界沒有吐綠之前,帶著兒子重返“小瓦爾登湖”,我要在那里砍伐樹木,搭建籬笆,拒絕一切與我無關的人類闖進。我要讓“小瓦爾登湖”成為我的領地,我是國王,兒子是唯一的王位繼承人,我要給每一塊水田取一個村莊的名字,給每一只螞蟻封一個騎士的稱號,給過去的日子修一部編年史。一公里外的養雞場是我的屬國,那里的臣民將每天進貢新鮮的雞蛋;更遠處的一所道觀將每天為我和我的國家祈福。
在寫詩的空隙,我可以去道觀講誦經文,讓前來聆聽的蝴蝶、蜜蜂和蚊子們得道成仙,白日飛升。然后我會在道觀的墻壁上畫畫,畫出烏鳥反哺的仁慈,畫出鹿草鳴群的情義,畫出羔羊跪乳的感恩,畫出螻蟻塞穴的智慧,畫出公雞報曉的信用。最后,我還要畫一顆樹,抑制它生長的欲望,以及變老的能力。從此,我只要站在“小瓦爾登湖”的堤壩上,不必變換任何角度和視線,就能讓一座城市變小,讓一片天空變大,讓一個湖恰到好處地存在下去。
與第一次尋訪“小瓦爾登湖”不同,重返這里的我已無須敲門,一切到來是如此的自然和貼切。重返不是時間,也不是距離,那是一次靠近人性的偏執。在重返“小瓦爾登湖”的路上,兒子問:在那里能看到什么?我回答說:一個隱士!
我知道,在“小瓦爾登湖”,我隨時都能見到一個隱士,如果我成為這里的國王,隱士將是唯一的叛逆者,我必須趕在春天結束之前來到這里,將隱士驅逐出我的國家,我要讓吃飯的人都學會勞動,讓湖水不因人類的目光而騷動,讓多情的杜鵑花開得放心、開得認真。兒子說:釣到魚的是漁夫,釣不到魚的才是隱士。然而我的重返已讓隱士的身份徹底暴露,他的嘆息被一塊塊巖石阻擋,好在他的一天一無所獲,一條魚竿成了“小瓦爾登湖”漂動的圖騰。我的到來是隱士離去的全部意義,隨他一起出山的,還有陽光、云朵和長尾巴丁的叫聲。
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次重返是在何時?天氣預報傳來:明天降溫,多云轉小雨。我想“小瓦爾登湖”又要穿起她的小棉襖,風吹來的時候,隱士留下的魚餌將隨湖面蕩漾。
再見“小瓦爾登湖”
辛卯年四月十三,初夏,天陣雨。宜嫁娶、納采、出行、祈福……元亨利貞,黃道大吉,遂登城關西象山,沿山梁而上,穿越荒徑、竹林、石嶂,最后抵達“小瓦爾登湖”。
自八個多月前找到這里后,因傾心于她的恬淡和靜謐,于是借梭羅筆下的“瓦爾登湖”為之命名,讓一個廢棄的山村小水庫多出了一些超驗主義的說辭。從此,這里被更多“瓦派”的信眾所接受,從形而下到形而上,人類膜拜的理由總是那么突然,且簡單又固執。這是我第三次來到“小瓦爾登湖”,我不知道山是否有了某種潛移默化的蛻變,畢竟從秋天到夏天,我的離開已經太久,而我的歸來卻依然匆匆。在“小瓦爾登湖”,我開始相信杜鵑花已開在遠方,我必須接受溪水變厚的事實,我甚至驚嘆時間留下來的殘骸一如“小瓦爾登湖”般的自在、超然。
在初夏的雨天,滿山的樹豐腴起來,將整座山抱成一團,成為一朵綠色的花,“小瓦爾登湖”被山的綠徹底霸占,持久地綻放,大氣、睿智,無所顧忌……
然而通往“小瓦爾登湖”的路是艱難的,我的抵達比午飯足足遲了三個多小時。在這一段被時間蝕穿的隧道中,一座山顯得并不空蕩,與我走在一起的,除了乖順的孩子,還有啁啾的鳥聲和窸窣的蟲鳴。在一路的穿越中,我的雙腳被那里的雨水浸濡,然后向上漫延,褲管、腰帶、襯衣都沾滿了“小瓦爾登湖”流灑的記憶。我想此時的云或者壓得很低,給了“小瓦爾登湖”哭泣的可能,那些飽受風雨洗劫的日子,如一枚枚下墜的松針,一直向湖心扎去,頓時,湖面疼成一朵蓮花的模樣,愴然流出的花葉,倏然而遠,不見回頭。
我依然沒有讀懂“小瓦爾登湖”的滴滴咒語,卻在上游的某個地方,看到兩塊寫著“水庫養魚,禁止垂釣”字樣的告示牌在向我招搖,似乎告誡我,這里住進了新的貴族,魚已是唯一的主人,“小瓦爾登湖”的所有榮耀都將為它祈禱。而我雖與“小瓦爾登湖”只有一步之遙,卻只能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接受著人類的輕狂。“小瓦爾登湖”注定不能幸免一張肆意強加的網,在我的潛意識里,幼稚地認為,魚不過是剛剛走過的春天將一群無家可歸的孩子寄養給了“小瓦爾登湖”罷,漁人的腥味與他們的笑容同樣可憐。
他們說養在“小瓦爾登湖”的魚比松針還細,我自然無法看清它游弋的樣子,或者它習慣潛在水底,吐納著水中的月色和星光,我想會是在某一個夜晚發現它的身影,只是冰冷的砧板比饑餓更加陌生。于是魚還要在這里再等三年,它鮮美的肉將成為“小瓦爾登湖”最后的銘牌,直到堅硬的時間被人類嚼成碎末。世界容不下它的眼睛。
聽說那些養魚者來自一公里外的雞舍,也來自兩公里外的牛場,他們必須姓雞,或者姓牛,他們曾發誓與“小瓦爾登湖”老死不相往來。也不知在何時,他們翻過兩公里外一座道觀的圍墻,將無辜的魚塞進“小瓦爾登湖”的懷中。從那一刻起,“小瓦爾登湖”開始成為一個新的墓地,她將隨時收藏魚的死亡,從此,她必須學會節制的抒情,必須拒絕水蜘蛛來覆蓋她的寂寞,必須在綠的霸占里找到自己的倒影,無數的“必須”讓“小瓦爾登湖”淪落成捕魚者曖昧的腳印,上面寫不進一枚松針墜落的嘆息。
最后一個垂釣者急急趕來,他使用魚竿的權利已被“小瓦爾登湖”剝奪,他必須沖進雞舍,用一場饑餓來對抗一只剛剛被斬殺的公雞的誘惑。雞舍中住著的養魚者無法給出任何與“小瓦爾登湖”有關的證明,就連養雞的自由也成為一場荒誕的“騙局”,隨著更遠處牛蛙的厲聲吼叫,四處聞訊趕來的人們紛紛拔出腰間的手臂,山的骨頭露出了它的固執,風呼呼地吹,“小瓦爾登湖”似乎有了些許波瀾,水蜘蛛們蠢蠢欲動,魚驚恐地潛入湖底,不見抬頭。突然,“唰”地一陣雨將“小瓦爾登湖”緊緊裹住,我終于不知道那里發生的時間,魚更加陌生,或者三年后我能在人類的餐桌上見到它,或者雞舍、牛場的主人會愛上“小瓦爾登湖”,就請他們用距離喂養那里的精靈!
或者我也不再蹈足,就讓魚靜靜地長大,無論它是否屬于“小瓦爾登湖”,我都將給它祝福。
再見吧!“小瓦爾登湖”,無論杜鵑花開在哪里,我都將用平靜的記憶收攏雨傘,遠山在陣雨過后的落日中漸漸沉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