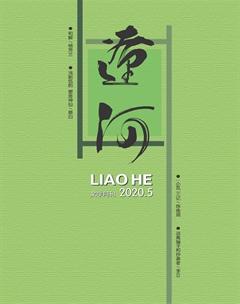一群喜鵲在飛(組章)
胡世遠(yuǎn)
一群喜鵲在飛
舊年已去,永無歸期。
大悲大喜,亦不足掛齒。我親眼目睹,一片片雪花在陽光的輝映下,從枯黃的葉子上飄落下來。那一刻,我從這白色的花瓣間穿過。
一路上無語。在東陵公園的后山上,十二屬相園的小動(dòng)物雕像被白雪烘托,愈發(fā)顯得栩栩如生。更有紅布條系在上面,紅白相間的輕盈,在這春節(jié)來臨之際,每一絲美好的感覺都值得珍惜。
吵鬧著跟隨上山的小狗曲奇,在樹林間來回穿梭,仿佛在尋找新年的禮物。它的歡快和四周的寂靜形成鮮明的對(duì)應(yīng),被積雪壓著身體的枯草從容自在。
一切好像劇中的場景,或許就是真的,當(dāng)我們踏進(jìn)這圣潔之處。我相信,有一片安靜是屬于我的。我看到的,也只能是局部的畫面,事實(shí)上,我們從未真正進(jìn)入過冬天。當(dāng)一片飛雪像親人一樣撲過來,我還在抱緊昨夜的睡眠。
像往常一樣走向春天。風(fēng)吹過塵世,它留下故事。等待有人記住,等待有人講述,等待有人傾聽。眼前這些上百年上千年的樹木,看起來如同一本厚重的書,關(guān)于靜謐、孤獨(dú)和歸處。
布滿綠苔的石頭,尚未腐爛。我仰慕樹的形象,能夠做到物我兩忘。說出來你也許不信,在白雪覆蓋中我看見自己。
還有,一群喜鵲在飛。
道路之上
我們到來之前,地面上早有無數(shù)雙腳印。
此時(shí)的凌亂,糾結(jié)于開始和結(jié)束。神秘的隱喻之中,陽光很輕。我多么希望,在某個(gè)拐角,那些走遠(yuǎn)的人突然折返,我們和影子重疊在一起。
風(fēng)一直在刮。那些驚慌的葉子,逃往各自的方向,就像一群人剛剛還聚在一堆,忽然間就漸生涼意。你所遇見的人和事物,每一個(gè)都不是多余的。
似乎冥冥之中,我們?cè)缫押蜕_(dá)成默契。當(dāng)星辰落在酒杯里,在這鐘情的土地上,我們像所有的人一樣,一次次面對(duì)選擇和放棄。捉襟見肘的窘境里,柔弱的肩頭試圖托起落日。就像其它所有的時(shí)間,我們不知道風(fēng)究竟來自哪里。
一片孤零零的白云掛在天空,像在關(guān)注大地上每一個(gè)被影子追逐的人。容易打折處理的光陰,來自沉默或麻木,來自虛假或禁閉。
失去拐杖之后,我不得不嘗試著踉蹌前行,只是后來,當(dāng)我確信自己可以站穩(wěn)腳跟時(shí),熟悉的道路卻消失了。
那么多分岔面前,遠(yuǎn)方那么近,又那么遠(yuǎn)。每每回到故鄉(xiāng),我不說話,沒有人知道我是回來尋找記憶的人。
無數(shù)條道路屬于雙腳。一份信念,照亮了道路之上,所有的荊棘。
風(fēng)吹不皺思緒
所有不甘現(xiàn)狀的人,多么像你,如此清晰。
在樹叢中,像星星,像鳥鳴。
接下來,可能還會(huì)有重要的事情,將要發(fā)生。
當(dāng)寂靜回歸事物本身,我們的秘密,有時(shí)候我喜歡閉上眼睛想。
我知道,風(fēng)吹不皺思緒。就像空曠的草原,迎來春天。草繼續(xù)生長,馬繼續(xù)吃草。我慢慢靠近馬,仿佛離春天近了點(diǎn)。??? 遼闊的草原,一片寂靜。除了心跳,只有穿過的風(fēng)聲。草兒睜開一雙會(huì)說話的眼睛。綠色里,我把自己想象為一陣風(fēng),一棵青草,抑或一匹馬。
我記得,在童年膽子小走夜路的時(shí)候,大人們說,折下桃枝,或拿一截桃木的棒子,就可以避邪。
長大后,落下一個(gè)習(xí)慣。身上揣著桃木掛件,家里藏著桃木斧頭,就這樣過去了好多年。
直到有一次,誤入桃花深處。
我突然感到,一種恐懼,蒼白的臉,仿佛風(fēng)帶走最后的炊煙。在這個(gè)世界上,除了陽光、空氣、水和笑容,我們還需要什么呢?
整個(gè)下午都是晚上,一直在刮風(fēng)。
而且將要有大風(fēng)。
思緒坐在一個(gè)人的心中,像個(gè)嬰兒倒立于母親的子宮。
老槐樹
穿過一場場風(fēng)雨吧!
你和我一樣,都不是瓷器。
你就是一棵樹,一棵上了年紀(jì)的槐樹。該綠時(shí),就綠;該休憩時(shí),休憩。
這輩子,如果不留下世俗的頑疾,也就好了。
都說生活需要存在儀式感。我在你的影子下打坐時(shí),風(fēng)從旁邊刮過去。一些塵埃,愛上了我的身體。
于是我重新變成了寶貝,聽到搖籃曲。
以前,我聽過隔墻有耳。現(xiàn)在,我堅(jiān)信地下有人。不同的是,走在路上我不敢發(fā)出異樣的聲音。好在小草蔥郁,掩飾了我的擔(dān)心。
關(guān)于命運(yùn),或生,或死,或生死之間。這三種想法,就像枝頭蹦跳著三只鳥。
我們迎著夕陽而行。風(fēng),吹開葉子的嘴唇:“好好活下去!”
——你說。那么多的美好,我們已經(jīng)錯(cuò)過。
哪怕一片葉子不剩,我也不想,不想就這樣被生活的綠色忽略。
我想要的,僅此一點(diǎn)。在一次次閃電中,我愿意
——燃燒自己。
把一只鳥放走
無聊之時(shí),隨手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
似乎自從買回來之后,它就一直在那兒。現(xiàn)在已被灰塵所掩映,書依然是嶄新的,灰塵是什么時(shí)候的,我不得而知。
現(xiàn)在看來,在此之前,這書根本就不屬于我。而灰塵卻常常與我相伴,就像隨時(shí)隨地涌出的丑陋的念頭。
看來一個(gè)人真的需要隨身揣面鏡子,空閑的時(shí)候掏出來,照照自己的臉,不知不覺就有了皺紋。時(shí)間久了,變黃的葉子好比時(shí)間,是記憶,也是遺忘。
在愛的一面,死亡的另一面,我們抱得很緊。
直到把一只鳥放走,剩下自由的鳥籠,仿佛空曠的老屋星光般般寂靜。風(fēng)刮著一片云彩,飄過大地最高的樹木上空。
我們把有夢(mèng)的男人,比做挖掘機(jī)。世界永遠(yuǎn)是一片青草地。青草還在那里,在記憶的廢墟和鐘聲里,不需要調(diào)解。
以玫瑰的刺去想起一些人,有疼痛最好。時(shí)間擁有我們,而生活是脆弱的——
余生擠出一些時(shí)間,多讀書吧。一行行文字就像一盞盞善良的燈籠,它會(huì)替你看見,許多正在移動(dòng)的事物……
當(dāng)風(fēng)停下來,安靜,來自遙遠(yuǎn),來自身邊。
命運(yùn)如雪
在哪里,你我都是異鄉(xiāng)人。
當(dāng)我們還沒有從心底愛上腳下這片土地時(shí),每一個(gè)時(shí)辰都充滿著微笑和假想,身體隨風(fēng)而飄搖,看一粒塵埃慢慢落下,用余生交換寧靜。
反復(fù)無常的春日里,相對(duì)于一場“疫情”的舉國之災(zāi),陽光顯得特別金貴。被困于房間的人群,和按捺不住的心跳,將希望寄予古樹之上的紅布條,為天地祈福。
天氣變暖,去南方貓冬的鳥兒還會(huì)陸續(xù)飛回來。在適合自己的枝頭,唱響完美的歌聲。至于它們分別叫什么鳥,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不重要了。
可貴的,它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至于今天清晨,我坐在臨窗的沙發(fā)上,懷抱可愛的小狗“曲奇”,任它在我的臂彎安靜地熟睡,均勻的呼吸仿佛就是愉快的問候;我望見窗臺(tái)上盛開的花朵,那些花瓣仿佛就是喜悅的詞語。原來我渴望的,竟是這輕盈的幸福。
而這一切,承蒙陽光的恩賜。此刻的景象,如同綠色填滿草地,萬般溫順。我突然幻想時(shí)間就此按下暫停鍵,我還有大把光陰,為各種意義呈現(xiàn)。
或許命運(yùn)就該像那厚厚的白雪,白雪象征著包容之善與純凈之美。大地被白雪覆蓋之時(shí),我一步一步地往家走,離故鄉(xiāng)越來越近,離炊煙越來越近,離童年越來越近。
雪化之后,我又一次變?yōu)楫愢l(xiāng)人。依然走在人間,每條道路還在這里,一如往常。
往前走,繼續(xù)走。以雪落的方式。
江城有霧
翁筱
最后一班駛向江北的船,是晚上九點(diǎn)。
我們穿過春夜的雨幕向著渡口走去。雖是春天,這個(gè)城市的港口卻異常陰冷。夜里航班是間隔半小時(shí)的,我們打算坐倒數(shù)第二班船,上岸后再等末班船過去接我們回江南。
售票處離渡船約500米,途中是露天的。我跟亦老師各撐一把傘,不緊不慢地跟著老李和江小天,也有一句沒一句的聽著他倆的談話。聽到有意思處,便用不高不低的嗓音打趣道:可以了可以了,悠著點(diǎn),也不怕風(fēng)大閃了舌頭。說完,我和亦老師相視而笑。
“舌頭倒不會(huì)閃了,你的腰可能會(huì),這叫‘閑靜時(shí)如嬌花照水,行動(dòng)處似弱柳扶風(fēng)。”老李回頭笑呵呵地看著我說。江小天一旁附和:就是就是。
隨著汽笛聲響,船從江北漸漸向我們靠近。
乘客們爭先恐后地朝船上涌去,就像在武漢封港前趕上漢口江灘往武昌中華路碼頭的最后一班船。我們也隨著匆忙的人群,變得躁動(dòng)起來,腳步自然而然加快了些。
一上船,我就雀躍著往樓上跑。因?yàn)槌丝捅容^少的緣故,樓上的燈并沒有隨著渡船的前進(jìn)而改變。它仍舊是黑乎乎一片,我們不說話,也看不見彼此的臉,仿佛空氣也是靜止的。我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近距離的海風(fēng)似乎并沒想象中的那么腥,它只是淡淡的和著初春的細(xì)雨,繞著我的鼻尖、耳垂、下巴,還有微動(dòng)的睫毛。
船到江心,借著南北岸的燈光,整艘船頓時(shí)變得明朗起來。
“大詩人李白,人稱‘詩仙,一生佳作逾千首。縱觀其流芳百世的詩作,‘明月和‘美酒是百用不膩的字眼,他的人生結(jié)局也和‘月與‘酒息息相關(guān)。”我首先打破沉寂。
“看來是酒成就了‘詩仙李太白,只可惜今晚沒有月亮。”江小天接茬。
“據(jù)《唐摭言》記載,這酒也毀滅了李太白。所以說,酒是個(gè)東西,也不是個(gè)東西。”老李搖頭感嘆。
“中國的漢字真是博大精深,此處這‘東西用得巧用得妙!”江小天伸出大拇指,不無夸張地說。
“話說回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比起李太白,屈原的投江倒是有意義的多。”江小天說。
“屈大夫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讒言與排擠,相繼被楚懷王、楚襄王驅(qū)逐,在被楚懷王逐出郢都,流落漢北期間創(chuàng)作的一些文學(xué)作品中,依然洋溢著對(duì)楚地楚風(fēng)的眷戀和為民報(bào)國的熱情。后被召回,卻在秦國大將白起揮兵南下,攻破郢都時(shí),帶著絕望和悲憤之心懷抱大石投汨羅江而死。”江小天繼而說道。
“那投江的愛國文人多了:商朝賢大夫彭咸,北宋丞相江萬里,還有唐代著名詩人駱賓王……”說起這歷史來,老李那是一套套的。
“閣下簡直是一本活的歷史名著啊!”這次換我夸張地豎起大拇指,且是左右手都用上了。
“那誰,來首詩吧!”對(duì)于這一點(diǎn),我是滿懷期待的。
“呵呵,你以為我們是曹植啊!不過,回去倒真是可以寫幾首關(guān)于咱一線醫(yī)護(hù)人員馳援武漢的詩歌。”老李的聲音劃過上空,瞬間銷聲匿跡。
“是啊,怎么著也要對(duì)回去的這趟末班船有個(gè)交代,你們說是不?”我扭頭看一眼身邊的亦老師和不遠(yuǎn)處倚著船欄桿的江小天。
“也對(duì),是得有個(gè)交代,我們仨傻乎乎被你騙上船,雖不是賊船,那也是船。”亦老師與我并排站在船欄桿旁,沒想到一向嚴(yán)謹(jǐn)?shù)乃哪惺恪?/p>
“這個(gè)提議好!回家后,我通宵完成作業(yè)。你倆呢?”我扭頭看老李和江小天。兩人離我們約有三四米遠(yuǎn),從半明半暗的火光判斷,兩人正猛吸剛點(diǎn)著的煙。
“一言為定,反正寫的不比江小天那《封城手札》差就行。”老李說。
“你這是謙虛還是驕傲?不過,我的散文還真不算好。就當(dāng)是非常時(shí)期的一個(gè)記錄吧。”此時(shí)的江小天,是謙虛的。
“武漢封城了。剛剛我們上船時(shí),輪渡碼頭的大喇叭也喊過幾嗓子了。等末班船回去后,就要面臨封港了。”老李嘆了口氣。
“機(jī)場、動(dòng)車站、高速路、國道都即將被封,港口自然也不例外。” 亦老師不無擔(dān)憂地說。
“封吧,只要能控制疫情的蔓延。一切我配合。”江小天接話。
“一起加油,為自己,為武漢,為中國。”大家異口同聲道。
“喂,前面那仨,我們能不能不去江北呀?我很累,不想走了。”渡船靠岸。封港的消息讓我有了莫名的緊迫感。
“再不走,我們拖你了!”江小天見我沒上岸,便催我。
他似乎永遠(yuǎn)一副笑嘻嘻的樣子,即便前方的路很難走。
“上不上岸都是江北,更何況來都來了,上去逛逛唄!”江小天不可思議地看著我。
“江北的夜景很美的,接下來也不知道多久才能來了。”老李接茬。
“走吧,一起!”亦老師做了個(gè)Lets go的手勢。
“你們?nèi)ズ昧耍飧哿耍揖驮诖系饶銈儼伞!蔽艺酒饋沓渡系乃麄儞]手。
“你一個(gè)人坐船回去也可以,包我就先背走了。”老李不懷好意地說。這才反應(yīng)過來,我的背包還被老李拽著,于是也顧不上地滑,拔腿就往岸上跑。
“小姑娘,雨傘掉了。”船老大在身后喊,追上來將雨傘遞給我。
“哦,謝謝大伯。”
“嘴挺甜,魂沒有,下次要是把人丟船上就好嘍,大伯撿回家去。”
小城市的人很會(huì)自得其樂,封港也好,封城也罷。或許,是追求自由的心跳動(dòng)得沒那么瘋狂吧!
夜晚的江北,并沒有老李說的那么讓人魂?duì)繅?mèng)繞。隨著春節(jié)的到來,老李曾經(jīng)工作過的廠子早已大門緊閉。似乎,這里并不歡迎我們。
“回望,是一種傷。”老李悠悠地說。
“不過,江北的街道寬了許多,地面也變得干凈,這證明老百姓的素質(zhì)越來越好了。”老李邊走邊看邊念叨著,仿若回到了闊別數(shù)年的家。
回江南的渡船上,江小天舉著手機(jī)朝江北“咔嚓咔嚓”拍個(gè)不停。
“你是準(zhǔn)備發(fā)朋友圈嗎?”我問。
“來時(shí)發(fā)過了。”
將近兩小時(shí)沒看微信,朋友圈多了好幾十條新消息,均是新浪、網(wǎng)易、搜狐、騰訊、澎湃等網(wǎng)站發(fā)布的“疫情最新信息”,以及微友們轉(zhuǎn)發(fā)的各種真假難辨的鏈接。人生無法預(yù)料下一秒會(huì)發(fā)生什么?就像人類這場史無前例的劫難。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將會(huì)是什么?幸福?背叛?死亡?多少年后,當(dāng)我們回想多年前在封港前結(jié)伴夜游的此刻,又該作何感想?
前段日子,有位詩人朋友走了,離開了這個(gè)在他眼里“骯臟”的世界,而他所向往的那個(gè)世界:沒有焦慮,沒有欺騙,不會(huì)有苦澀和罪惡。
之前,我們都沒有發(fā)現(xiàn)他也有抑郁癥,跟海子一樣:在海子的大量詩作中(《太陽·詩劇》和他至今未發(fā)表過的長詩《太陽·斷頭篇》等),他反復(fù)具體地談到死亡,鮮血、頭蓋骨、尸體,甚至天堂。我們天真地以為,他們都只是基于對(duì)詩歌的狂熱,而無時(shí)無刻地在用我們自以為變形的句子,演繹著一個(gè)詩人的情感。
1月23日之后,武漢成了一座“空城”,也讓圍城內(nèi)的人們終于有機(jī)會(huì)抱團(tuán)取暖。而除了網(wǎng)絡(luò),一個(gè)家庭與另一個(gè)家庭之間幾乎斷了聯(lián)系,包括父母、包括手足、包括朋友、包括兩地分居的戀人。空曠的街道上,斑馬線清晰得如亞當(dāng)?shù)囊桓吖牵耐迏s遠(yuǎn)在他鄉(xiāng)。誰不喜歡浮云般自在:不論何時(shí)何地,不論是否兩鬢斑白。可無聲的恐懼,一直蔓延,在每一個(gè)角落。
死亡每天都在發(fā)生,親人們已沒有了眼淚,因?yàn)榭奁鼰o法挽回逝去的生命,連靈魂也是虛空的,如年輕的肺葉迅速被病毒入侵,在影像中沒了色彩。盡管青春依然如芙蓉般絕美,卻匆忙間成了一部默片,壓抑、冗長。
記得托爾斯泰在一本隨筆集中闡述道:“在人死去的那一刻,點(diǎn)燃著一支蠟燭,在這燭光下他曾讀過一本充滿了焦慮、欺騙、苦澀和罪惡的書,此刻這蠟燭爆發(fā)出比以往任何時(shí)候都明亮的光,把以前隱沒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照亮給他看,然后噼啪響過,閃動(dòng)了一下,便歸于永久的寂滅。”我開始討厭托爾斯泰,討厭一切思想家、哲學(xué)家,包括尼采。尼采說:“女人學(xué)哲學(xué),既是女人的不幸,也是哲學(xué)的不幸。” 我討厭極了這種剖析人類的感覺。他們無法挽救生命垂危的人,就算剖析得一清二楚又能怎樣?病患還不是在病毒的侵襲中漸漸呼吸衰竭,嘴唇和指甲隨著血色素的降低而一點(diǎn)點(diǎn)變白。
魯迅在《墳·寫在(墳)后面》里提到:“我的確時(shí)時(shí)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就這一點(diǎn)而言,他是可愛的,同時(shí)也是可惡的。當(dāng)然,我也會(huì)時(shí)常解剖自己,因此,我有多喜歡他,便有多喜歡自己;我有多厭惡他,便有多厭惡自己。在疫區(qū)人人自危的關(guān)頭,是那些在請(qǐng)戰(zhàn)書上按下紅指印的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線醫(yī)護(hù)人員逆流而上,是他們點(diǎn)燃了生的希望。醫(yī)者仁心,心懷天下。倘若先生健在,棄醫(yī)從文的他能救回那么多條鮮活的生命嗎?他不能,我也不能。
隨著汽笛聲響,船從江北漸漸往江南靠近。
雨下得似乎更大了些。我回頭看一眼冒雨前進(jìn)的江小天,再看了看走在前邊各撐一把傘的老李和亦老師。乘客們爭先恐后地朝岸上涌去,我們也隨著匆忙的人群,加快了腳步。
是夜,江城有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