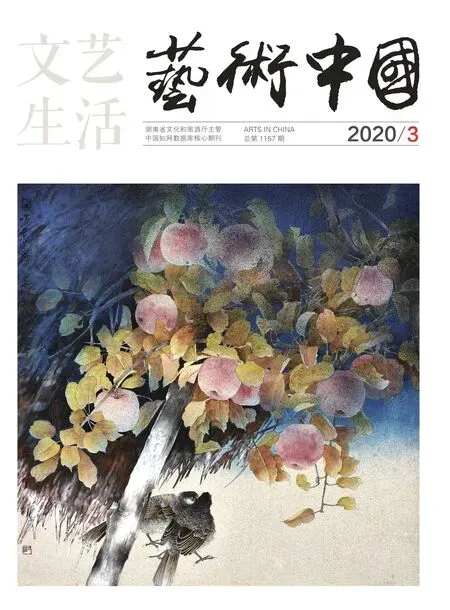弘仁山水畫幾何圖式的由來
◆譚金平(陽光學院設計學院)
一、緒論
在萬馬齊喑的明清山水畫壇,弘仁的作品與眾不同,既具有開創性,還意境高逸、哲理深邃。弘仁山水畫的繪畫特色從作品表現的韻味來講,不離“冷寂、靜穆、簡淡”這些取向特點,但具備這些取向特點的畫家前有古人,后也有來者。雖是高逸雅致的境界取向,但又都是抽象的取向概念,很多畫家的作品都可以如此形容。真正要表達弘仁山水畫獨到之處的特點,還得從構成、造型、筆墨等畫面表現形式上分析。以弘仁山水畫成熟期的代表作——現存于南京博物院的《黃山天都峰圖》和現存于廣州藝術博物院的《黃山始信峰圖》等作品來看,其最典型的面貌可概括為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整體構圖縱橫變幻,奇峰疊巒,陡壑空幽。
二是整個畫面石多樹少,山頂、山側、山腳偶有三五棵松點綴其間,姿態或橫或立。
三是畫面更顯平面化,主要由大大小小的幾何形體組成基本二維單元。點線用筆所構成的二維圖像單元是各種抽象的幾何形體,再由各種大大小小的幾何形體組成大大小小的山石以及山體的內部結構。大大小小幾何形體單獨看是基本看不出山石特征的,所以對于具象的山石來說是抽象的,但通過不同的排列組合它們就能形成各種疏密有致的具象的山石畫面。
四是在筆墨上即沒有用大片的墨,又多用堅韌折鐵的線條空勾,使其幾何形體的單元圖式更加突出,更加平面化。雖有少量坡腳及夾石內有皴筆或點染,但并不影響畫面幾何圖式的整體形象。反而因為幾何形體之間的淡墨互襯,更顯幾何圖式的突出形象。
但縱觀山水畫史,構圖縱橫變幻和石多樹少這兩個特點只能算是一般的畫面特點,算不得獨到之處,而且這兩個特點是黃山等自然景觀本身就有的“第一形式”之美。真正讓弘仁的山水畫冠絕古今的是其畫面中運用抽象的幾何圖式表現具象的山水形象,可稱為山水畫表現自然美的“第二形式”,這是屬于開創性的一種新形式,是其畫面最突出的特點。王國維在《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一文中提到:“而一切形式之美,又不可無他形式以表之,惟經過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而吾人之所謂古雅,即此第二種之形式。即形式之無優美與宏壯之屬性者,亦因此第二形式故,而得一種獨立之價值。故古雅者,可謂之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也。”也正是弘仁在其山水畫表現上提煉出了能表現自然景觀“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即畫中通過“第二形式”表現了“古雅”之美,遂成為清初最富個性的山水畫家之一。對于弘仁表現山水的“第二形式”——幾何圖式的出現,本文將結合他的畫作與史料,從時代背景、師傳統、師造化、個人氣質幾個方面來探討。
二、時代思想與精神背景
一個新形式的出現必然有新思想的支撐,繪畫中的抽象幾何圖式的出現,必然也有打破原有思想禁錮的思想準備。
1.破碎的時代有了打破原有精神枷鎖的需要和可能
明末南方社會經濟發達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社會思想相對開放,封建制度已顯露出氣數將盡的景象。在這個改朝換代“天崩地解”的時代,黃宗羲甚至猛烈的抨擊了君主專制的政體“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傅山全盤否定道學,提出“圣人為惡”“市井賤夫最有理”等等具有近代思想意義的理論。唐甄曾在《潛書》大罵:“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顏元在認識論上主張習行、踐履,認為:“吾輩只向習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語言文字上著力。”石濤也強調認識來源于對客觀事物的直接感受。王夫之、顧炎武等人,都提出很多抨擊理學的先進主張。這些甚至與近現代的先進思想契合,是超越當時時代水平的,這正是那個“天崩地解”的時代精神。同處這個時代的弘仁早年雖學儒,亦多多少少接觸或耳聞過這些新的思想,這為他開創新的繪畫圖式打下了思想準備。且后來事實證明,與整體時代的精神解放相同,明代已急劇衰微了的山水畫,在清初重新震起,以弘仁、髡殘為代表的遺民畫和以梅清、石濤為代表的自我派山水畫,都以開拓思辨的精神向前探索推進,大可媲美宋元,甚至超越。
2.佛教禪宗思想的影響
明清更替之際,弘仁已有36歲,雖然在明朝未能進入仕途,但他前期所學之儒學傳統仍然指引著他忠君報國,入世平天下。然而時事并不隨人愿,跟隨南明王朝抗清的志士在步步挫敗的過程中失去了牽掛的一切。最后他只有抱志守節,隱于空門。然空門不空,禪宗思想正于亂世再次興起,禪宗思想中的“空”“靜”正合弘仁清心寡欲的心境。如弘仁自題詩為證:“畫禪詩癖足優游,老樹孤亭正晚秋。”其詩中所表達的就是他正享受著通過繪畫表現禪理和寫詩抒發內心情感使自己悠閑自得的狀態。而且禪宗思想認為“空無”的心靈狀態至樂至美,自然界的空曠寂寥也被稱之為“空相”之美。而縱觀中國山水畫史,到明末清初畫面留白面積最多的就是弘仁的作品。而他的“空”主要體現在對所描繪景物的高度概括。黃山真景山石居多,偶有草木相間,弘仁正是通過洗練簡逸的構圖,勁挺渴筆空勾山石形成抽象的幾何體,重重疊疊,展現“空無”的禪學思想。而且禪學思想也為弘仁空凈的幾何圖式提供了繪畫內涵和理論的支撐。
三、從師傳統中去繁抽簡
弘仁山水畫幾何圖式的表現方式從師傳統中有無根源?當然有。從師傳統看,大凡有記載弘仁的文獻都有言其山水畫從宋畫入手,上追晉、唐,主修“元四家”,特別著力于倪、黃二家。例如明末周亮工《讀畫錄》云:“喜仿云林,遂臻極境”。清初馮仙等《圖繪寶鑒繼纂》記:“僧漸江……善畫山水,初師宋人,及為僧,其畫悉為元人一派,于倪、黃兩家,尤其擅場也。”清代張庚《國朝畫征錄》記云:“弘仁……山水師倪云林。新安畫家多宗清閟法者,蓋漸師導先路也。”清代李玉棻在《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云:“山水師云林……兼具大癡蒼厚。”其它文獻類似的記載還有不少,就不一一列舉。
山水畫中的幾何形體自有畫以來就存在,只是不夠凸顯。如倪云林的作品,其畫太湖一帶一河兩岸的景色,經常前景有一土堆或石塊,并用折帶皴的筆法表現石塊的結構轉折,大多是以方形或矩形呈現出來,只是倪云林的折帶皴更顯繁復曲柔,以至于凸顯的不是抽象的幾何圖像,而是更接近自然機理的具象。而弘仁學倪云林的畫雖都有倪云林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既似云林,又不似云林。其學倪云林淡而松枯的折帶皴又不似倪云林那般繁復飄逸,用筆造型更顯沉穩方剛;又學倪云林用墨清淡虛靈,更使弘仁畫面方剛的幾何圖像更加平面化,更加抽象化,亦更顯冷寂靜穆。正是有倪云林作品在前的指引,才有了弘仁后來糅進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化而為自己意中的筆墨技法所表現的空而白、方而剛。這正是弘仁提煉畫面幾何圖式的基礎模本。
弘仁學習元人繪畫中存在幾何圖像的證據還不止是倪云林的畫,還有黃公望的作品《九峰雪霽圖》。此幅作品相對以往歷代其它山水畫來說,幾何圖像的顯現更加明顯一些,只是沒有后來弘仁作品那么規則,因為它更像山水造型的剪影。
綜上所述,幾乎所有山水畫作品都有幾何圖像的出現,只是弘仁之前的畫家作品中不夠凸顯,經過弘仁在所學最著力的兩家提煉之后,其找到了自己合適的表現方式,即凸顯的幾何式圖式造型。
四、從師造化中提煉
明代唐志契言:“畫不但法古,當法自然。”又稱:“凡學畫山水者,看真山水極長學問,便脫時人筆下套子,便無作家俗氣。”弘仁作為新安畫派的宗師,山水畫能自成一格,除了師法傳統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能跳出前人范式,提煉出個性化的山水畫幾何圖式,開創新的局面。
1.師造化的地貌特征對畫面圖式的影響
“外師造化”的個性圖式的提煉與弘仁的人生游歷密切相關。查士標云:“漸公畫入武夷而一變,歸黃山而益奇。……嘗聞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乃足稱畫師。今觀漸公黃山諸作,豈不洵然!”丹霞地貌的武夷山常見一石為一山,或呈方形、矩形、三角形,結構疏朗明晰,石山坡陡光滑,坡陡處大多無以覆草,僅山頂平緩處可見零星草木為被。如此簡明的山石結構為弘仁的山水畫提供了簡潔大方的幾何圖式的原型。雖然“入武夷”時期的作品,現已無以睹見。然而不論是后來回皖后弘仁憑記憶創作的《武夷巖壑圖軸》與《武夷山水軸》,還是弘仁畫的大量黃山圖,都能夠看到畫面中簡潔大方如幾何圖式一樣的石山結構。弘仁后期師造化的主要對象是黃山,有不少都標有黃山實景的畫,如《黃山圖》《黃山天都峰》《黃山蟠龍松》《黃海松石圖》等等。即使有些未標明黃山某峰某山,對于熟悉黃山的人來說也可以看出它是黃山某景的變幻。他自己的詩最能說明其中真諦:“坐破苔衣第幾重,夢中三十六芙蓉。傾來墨沈堪持贈,恍惚難名是某峰。”他還說:“敢言天地是吾師,萬壑千巖獨杖藜。夢想富春居士好,并無一段入藩籬。”可見他的作品從師造化中提煉的成分是比較多的。但即使是畫黃山,他的畫也不是如照片般真實,也有其變幻的方面,這種變幻是結合了黃山地貌和武夷地貌特點的變幻。對黃山了解的人,都知道黃山為花崗巖質,雖然也是石多樹少,但與武夷山如巨石排列,且切面整潔不同,黃山怪石嶙峋的山峰,似無數碎石塊堆疊。雖然矩形、方形類的幾何體也很多,但大多不大,而且多是呈豎條狀。如《黃山始信峰圖》前景中的巨石橫列,卻更像武夷山的地貌特點。從這幾點看弘仁后期很多的山水畫是有黃山的特點,但又不完全是黃山的特點,這無疑是武夷地貌的影響給弘仁繪畫帶來的變幻。
2.師造化的筆墨提煉
弘仁既學宋人,又力追倪云林、黃公望等,卻又不同于宋人及倪、黃所具備的形式美。究其原因,既有描繪對象之不同,也因弘仁深知北宋畫家描寫北方雄強山水的筆墨不適于描寫黃山,及倪云林描寫無錫一帶一河兩岸三段式的表現方法更不足以寫武夷山與黃山雄奇深闊的景象。所以,弘仁在宋人與元人的筆墨基礎上根據自然對象的不同進行提煉,以求能適應并凸顯類似武夷山、黃山那樣的幾何形體的表現。弘仁的山水畫能推陳出新,就在于既能歸納兩地地貌特點,又能于前人筆墨中選擇并提煉符合表現對象的幾何圖式的筆墨構成,成就弘仁獨創性的帶抽象形式的幾何圖式風格。
五、精神氣質的表現
弘仁、梅清、石濤、石溪等人同樣是學倪云林、黃公望,也同樣是游黃山、畫黃山,但畫出來的黃山卻風貌各異。這是因為決定畫家繪畫形式風格的形成,最關鍵的是畫家的修養和精神氣質。這里借鄭板橋繪畫創作的三個階段來分析,其認為繪畫創作有“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個階段。“眼中之竹”是對自然的關照。“胸中之竹”是畫家“情”“景”契合而產生的審美意象,即意欲表達的圖像形式。“手中之竹”是畫家運用藝術技巧把頭腦中的意象加以物化,也就是畫面所呈現的審美意象、圖像形式。在這整個過程中包含了兩次飛躍:從“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是第一次飛躍,從“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是第二次飛躍。“胸中之竹”不等于“眼中之竹”“手中之竹”又不等于“胸中之竹”。在這個由兩次飛躍組成的創作的全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胸中之竹”的產生。“眼中之竹”只是啟發審美的對象,還不是審美意象,更不是表現的圖像形式。“胸中之竹”才是憑畫家的個性追求、精神氣質決定形成的審美意象,即意欲表達的圖像形式。有了“胸中之竹”,就有了藝術的本體和生命,然后才有“手中之竹”,即畫面的圖像形式。這也是鄭板橋認為的 “意在筆先”。弘仁在長期的繪畫實踐中發現了幾何形體的表現能更好地表達他精神中的冷、思想中的靜,且堅韌折鐵的線條空勾與淺皴淡墨間留白也更符合他追尋倪云林精神境界的表達。于是在抗清失敗,自覺復明無望之時,弘仁選擇了簡潔穩定、結構疏朗的幾何圖式表現山石主體,以表達冷寂、靜穆、簡淡的精神主題。
結論
弘仁早期學古人畫作,畫風平淡無奇,后在武夷山出家游歷,歸皖屢登黃山,甚至長期寓居黃山,以便日夜觀臨,并敢于實踐嘗試,終在地貌特征與畫面形式之間,找到了一種符合自身精神追求的表現形式,畫風為之一變,終成一派宗師。這種運用抽象幾何圖式表現具象山石的形式在繪畫實踐中的初步成功,鼓勵和堅定了弘仁在表現形式上的價值取向。弘仁將近乎抽象的幾何化山石以各式各樣排列組合布于畫中,建立了簡冷、靜穆的典范圖式,使觀者的視覺有了新的體驗。這首創性的幾何圖式成為他表達精神追求的最佳形式,為明清以來中國山水畫的發展注入了一股清新活力,促進了山水畫的進步與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