墻
張淑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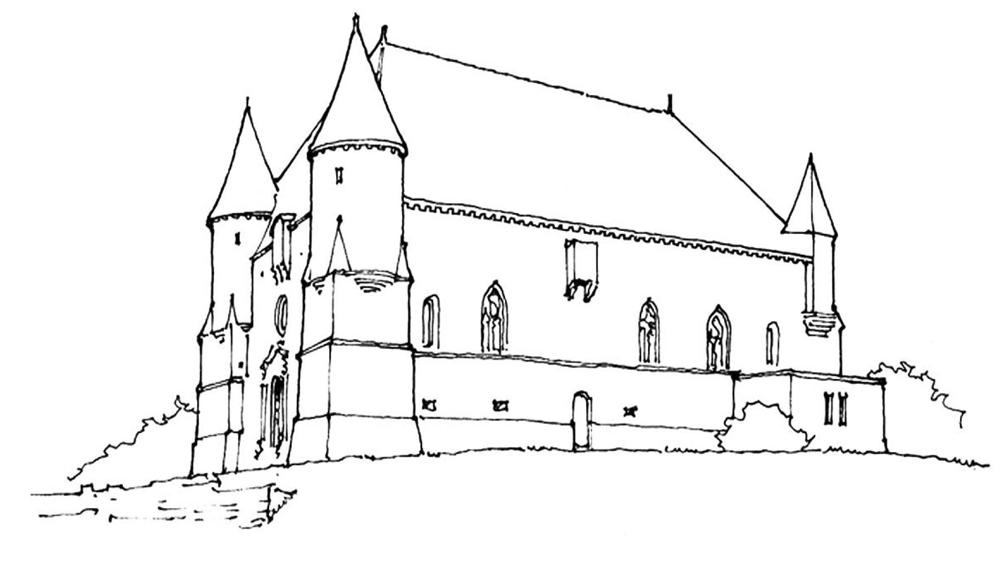
1
鳳姑的奔跑是緩慢的,她路過(guò)的街道,雞冠花正開(kāi)得臭不要臉。
鳳姑顧不了那么多,來(lái)不及欣賞花們,要是往常,她一定會(huì)蹲下來(lái),用心撫摸無(wú)數(shù)遍,這些花太可愛(ài)了,它們風(fēng)華正茂,滿巷子都是花兒們的世界。
可巷子沒(méi)有一個(gè)人影,就連一只流浪貓也沒(méi)有。雞鴨鵝狗這會(huì)子全不見(jiàn)了,鳳姑有些懷疑地停住了奔跑的腳步。
難道,人們都下田收割苞米了?她清楚記得昨個(gè)還看到鄰居老李在他家門(mén)口走來(lái)走去,目光伸在屯子那條街上,不斷地張望。
老李家昨個(gè)煙氣繚繞,屋頂?shù)臒焽瑁距焦距矫鞍谉煟ㄩ_(kāi)的風(fēng)門(mén)朝外噴霧氣。
鳳姑不知道老李家誰(shuí)來(lái)做客,反正,菜香肉香四級(jí)小風(fēng)一樣,在兩家的天空打秋千。
老李最后收回伸長(zhǎng)的脖子,是在晌午十二點(diǎn)半后,他把嘆息砸在地上,撞得屯子趔趄了一下。
鳳姑今天才想起,老李昨天和老婆熱氣騰騰拾掇飯菜,原來(lái)是他四十八歲生日。
老李沒(méi)有迎回兒子,兒子甚至連個(gè)電話都沒(méi)打來(lái)。
今天,老李家的煙囪沒(méi)反應(yīng),冷著臉坐在屋瓦上,旁邊的一族狗尾草倒是搖頭擺尾,不肯寂寞的樣子。
鳳姑管不了老李的遭遇,現(xiàn)在,鳳姑都無(wú)法保護(hù)自己,她要是稍微慢一拍,那長(zhǎng)了眼睛和腿腳的棗木扁擔(dān)就會(huì)追上來(lái),不問(wèn)青紅皂白劈頭蓋臉給她一下子。
那根扁擔(dān),鳳姑最熟悉它了。
鳳姑是去娘家,扛回來(lái)的一棵棗樹(shù),找老李鑿的。
老李是木匠,也是雕刻家。
老李可以目測(cè)一棵樹(shù)能打幾張桌子,幾把椅子,幾個(gè)箱子。
那時(shí)候,屯子的人不信老李有如此本事。
當(dāng)年老李還是乳臭未干,讀初二年級(jí)的學(xué)生,小李的父親請(qǐng)來(lái)一位南方來(lái)的木匠,給家里捌飭兩口立柜。
南方人細(xì)密的牙齒,一笑臉蛋上有倆酒窩,皮膚很白。
他在小李家堂屋地上,揮舞著刨子、鑿子,將一塊塊粗糙的木頭,鑿出藝術(shù)的氛圍,水光溜滑,還把斑駁的內(nèi)質(zhì)層雕刻成一條條鯉魚(yú)。
小李就目不轉(zhuǎn)睛地看著南方人認(rèn)真雕琢的杰作,有那么一瞬,他愛(ài)上了經(jīng)過(guò)木匠一雙手變得活色生香的物什。
簡(jiǎn)直是傳奇,他突然生發(fā)了一個(gè)決定,他要拜師學(xué)藝。
這個(gè)想法一經(jīng)發(fā)出,不可遏制地噴薄起來(lái),他丟開(kāi)平素的膽怯,撲通跪在南方人面前,連威嚴(yán)慣了的父親,也質(zhì)疑是不是在夢(mèng)境之中。
以至于小李子的頭磕在泥地上,咚咚咚作響,他才意識(shí)到,兒子要拜師學(xué)木匠活兒。
小李子書(shū)不讀了,一門(mén)心思跟師傅學(xué)藝,三年后出徒,技藝超過(guò)師傅。
他做出的木活,堅(jiān)固耐用是一方面,外觀精美,大部分刻有五谷豐登,花香鳥(niǎo)語(yǔ)的圖案。
小李子變成了老李,鳳姑沒(méi)想到和他做了鄰居。
老李其實(shí)不老,屯里的人叫順嘴了,就老李長(zhǎng)老李短地喊他,他四十八周歲,今年是本命年。
老李和鳳姑,兩家隔著一堵青石墻,這院炒什么菜,一聞就品出來(lái)了。那房蹦出幾句私房話,也能聽(tīng)個(gè)清晰。
新農(nóng)村建設(shè)刮進(jìn)北部灣屯,鎮(zhèn)子上此起彼伏冒出幾家家具店,人們?nèi)⑵藜夼?gòu)置的家具,基本都在店里買(mǎi)。
早先木匠是香餑餑,誰(shuí)個(gè)請(qǐng)來(lái)木匠做家什,好酒好菜款待不說(shuō),小雞掉脖,汽酒吐沫,少一樣,木匠就使詐。老李的手藝再精湛,架不住新浪潮的沖擊。他依舊自信滿滿,不放棄刨子鑿子。
他說(shuō)過(guò),做木活就像一個(gè)人與大自然交流,與靈魂對(duì)話。
老李木匠偶爾也做木活,但請(qǐng)他的人越來(lái)越少,門(mén)庭冷落車(chē)馬稀。
大家埋汰他死蝎子,怎么不開(kāi)個(gè)屬于自己的家具城,老李又有手藝,又能吃苦。
老李搖頭,他不喜歡參與競(jìng)爭(zhēng),但他會(huì)無(wú)償給娶媳婦的北部灣父老做家具,衣櫥書(shū)柜餐桌等。
他不想手藝失傳,問(wèn)題是孩子們考上大學(xué),都燕子似的飛離老巢,畢業(yè)后,留在城市,每次回來(lái),不厭其煩地勸父母去樓里住,姐弟在一座城,老李兩口子搬到他們那,也有照應(yīng)。
老李不去,去不了。老李的手藝派不上用場(chǎng)時(shí),說(shuō)來(lái)也是機(jī)緣巧合,鳳姑的婆婆前年冬天突然得了疾病,人在去市醫(yī)院的路上,就不行了。
老李是鄰居,自然不能袖手旁觀,他第一個(gè)跳上救護(hù)車(chē),抱著病人的頭,不敢有一絲松懈。
鳳姑的婆婆彌留之際,握著老李的右手,氣若游絲地說(shuō),“我有個(gè)……心愿……能幫我……蓋一間……漂亮的房子……嗎?”鳳姑在婆婆左邊坐著,老李在右,他們的位置給人的錯(cuò)覺(jué),倒像老李是病人的家屬。
那一刻,鳳姑的丈夫貼到跟前,“媽,你想說(shuō)什么?德利在!”
鳳姑的婆婆用眼睛拒絕了兒子,直直地盯著老李要一間房子。
老李咬著牙,沒(méi)說(shuō)話,只是雕刻慣木頭的手被老人抓得生疼。
老李早先就給自己立下規(guī)矩,只做大件的家具,鐵锨把、鐮刀柄一概不做。
師傅在沒(méi)回南方之前,就告訴老李,什么都可以做,唯獨(dú)一樣堅(jiān)決不做,那就是棺材。
老李從出道以來(lái)遵照師傅的話,還真就沒(méi)打過(guò)一口棺材。
因?yàn)檫@事,北部灣的人對(duì)他有想法,認(rèn)為老李只認(rèn)錢(qián),不認(rèn)鄰里之情。
北部灣就老李一個(gè)木匠,一百戶人家,老少輩兒,誰(shuí)也不稀罕木匠行當(dāng)。
老李不打棺材,不是嫌晦氣,師傅的話不能不聽(tīng)。北部灣的人都說(shuō),南方人早離開(kāi)這里了,死守著破規(guī)矩頂毛用?
老李訕笑下,不吱聲。
北部灣老喪人,用的棺材基本是從六十里外的市內(nèi)運(yùn)回來(lái)的。
所以,老李和大家拉下了恨意。不是仇視,可也是一道不好逾越的鴻溝。
那天在鳳姑婆婆咽氣前,趕去陪護(hù)的人眼巴巴看著老李。令在場(chǎng)的人意外的是老李居然答應(yīng)了,老李是在鳳姑投來(lái)的求救眼神中,把自己的腦殼點(diǎn)了一下。
鳳姑的男人德利,心底長(zhǎng)著荒草似的,哪顧得上鳳姑的那抹秋波,事后,老李喝著鳳姑端來(lái)的一碗荷包蛋,站在鳳姑家堂屋地上,老冬的陽(yáng)光,明晃晃地泊在炕上,德利才發(fā)現(xiàn),鳳姑和老李似乎有點(diǎn)什么。
有什么故事呢?德利也搞不清楚。
2
老李到哪家打家具,都有一個(gè)一成不變的規(guī)矩,家什快收尾時(shí),東家必烙四個(gè)荷包蛋犒勞老李,寓意是四平八穩(wěn)。
無(wú)論是東家抑或老李,對(duì)平安都是極其講究的。
老李打家具有三不準(zhǔn),第一,他在做工期間,不許打擾思路;第二,一定要在堂屋打家具,原因是他喜歡家的氛圍;第三,一杯鐵觀音茶。你木料品種是什么不要緊,再次的木頭,經(jīng)他的手一打磨,沒(méi)有不精彩的。
工錢(qián)掐頭去尾可以省一吊子,獨(dú)獨(dú)一杯鐵觀音茶不能少。
老李喝茶也有講究,熱氣騰騰最好,他舌尖一舔,試試溫度,再將嘴唇上下對(duì)折,翹起來(lái)發(fā)出噗噗噗,吹茶聲。
抿一口茶,很愜意地閉上眼,足足有一分鐘,陶醉在茶香里。
北部灣就老李一個(gè)木匠,老李就像北部灣的老佛爺,轟轟烈烈,威風(fēng)八面了二十年。這幾年,老李被冷落下來(lái),鎮(zhèn)子上的家具店,不但賣(mài)琳瑯滿目的家具,還送貨上門(mén),服務(wù)到位。
老李仿佛一棵晚秋的柿子,被遺忘在樹(shù)上。
突然被鳳姑婆婆又從低谷拽了上來(lái),他有一種重生的感覺(jué)。
老李把打造他在北部灣的第一口棺材,做為涅檗的開(kāi)始。
他認(rèn)真地鑿好木板,并在木頭上刻出最美麗的鳳凰,鳳和凰,蓮花簇?fù)怼K目痰蹲哌^(guò)的地方,立起一個(gè)春天。
他想讓鳳姑的婆婆,走得幸福,住在這么一間鳥(niǎo)語(yǔ)花香四季如春的房子里,那是上蒼的恩惠。
老李更多的是感恩,鳳姑婆婆把他從沉寂了幾年的枯槁時(shí)光中復(fù)活。
老李邁過(guò)德利探尋的眼神,在淡泊的光影里,吧唧吧唧著荷包蛋,卻扯出一串雞屁股的臭味。
孝子德利悶聲不響把老娘入土為安后,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大病了一場(chǎng)。
德利的病不是癌癥,也非不治之癥,而是心病。他拿著鋤頭去田里除草,晌午趟著鳳姑飯香回院子,鳳姑發(fā)現(xiàn),鋤板上連一點(diǎn)泥土都沒(méi)有。
德利風(fēng)擺柳似的,晃進(jìn)房間,照著炕上的被垛倒頭就睡。
鳳姑叫他吃飯,他睜開(kāi)一只左眼,說(shuō),“吃飽了。”
鳳姑說(shuō),“你吃西北風(fēng)了?”
德利說(shuō),“你拿四兩棉花,自北部灣東頭紡到西頭,問(wèn)一問(wèn),聽(tīng)一聽(tīng),保準(zhǔn)你一年不吃飯也不會(huì)餓!知道劉海家的騾子怎么瞎了右眼嗎?那是外路精神遭的。”
鳳姑也不和他磨嘰,德利是心里不舒服。鬧情緒,不好治。
鳳姑踩在土街上,耳根子全是撲面而來(lái)的流言蜚語(yǔ),中國(guó)人什么都缺,就不缺想象力。
他們將老李再度出山,歸結(jié)為是與鳳姑的暗度陳倉(cāng)。
北部灣人在犄角旮旯,也能把老李和鳳姑的故事描繪得花枝招展。
有的說(shuō),鳳姑早先就是老李的初戀情人,兩個(gè)在同一所中學(xué)讀過(guò)書(shū)。
那時(shí)候,鳳姑是班花。
老李是體育委員,他高高的個(gè)子,仿佛一株北方的白樺樹(shù),栽在很多女孩的心底,也扎根在鳳姑的靈魂里。陰差陽(yáng)錯(cuò),鳳姑嫁給德利。老李在三十里鋪為何家打一只檀木柜子,就被何花相中了。
何花沒(méi)有荷花的亭亭玉立,濯清漣而不妖,生得粗枝大葉,臉盤(pán)子像一顆向日葵。
大腳板走路虎虎生風(fēng),面色紅潤(rùn),猶如一穗熟透的高粱。
何花有意,老李無(wú)意。
老李那時(shí)還不想結(jié)婚,他心心念念的是鄉(xiāng)里電影院賣(mài)票的姑娘,草蘭。
草蘭的俊俏是語(yǔ)言難以企及的,白的正好,身材窈窕。真是多一寸浪費(fèi),少一寸可惜。
老李不止一次問(wèn)過(guò)大地藍(lán)天。問(wèn)過(guò)門(mén)口的荷塘,問(wèn)過(guò)連綿起伏的坨坨山,草蘭怎么這么好看。
老李為了得到草蘭的芳心,讀初中時(shí),經(jīng)常曠課,撒謊要了父母的錢(qián),說(shuō)買(mǎi)學(xué)習(xí)資料。結(jié)果,擠進(jìn)電影院,排隊(duì)買(mǎi)票,就為了多看一眼草蘭,多和她待一會(huì)兒。
電影演的是什么,老李一點(diǎn)印象不存,只記得影院里的嘈雜聲,以及三兩對(duì)情侶耳鬢廝磨親嘴聲,啪啪啪,老李聽(tīng)著啪啪聲,面前海市辰樓的幻覺(jué)出現(xiàn)他同草蘭緊緊相擁接吻的場(chǎng)景。老李后來(lái)被父親揪出電影院回到家,一頓暴揍。
從此,就和學(xué)校無(wú)緣了。
但是,父親對(duì)老李拜師學(xué)藝,表現(xiàn)得很熱忱。
父親的熱忱是他挖掘到了一絲希望,這個(gè)逃課撒謊的李家后人,終于把目標(biāo)鎖定一件有意義、受益一生的事情。
以至于老李因?yàn)槭炙噹Щ貋?lái)夾著一只藍(lán)布包,包內(nèi)幾件換洗衣裳的何花,父親真正地舒了一口氣,他豎起大拇指對(duì)老李,他的兒子李顯貴說(shuō),“你比老子牛叉!”
老李的父親叼著大煙袋,把住到北部灣的人家坐遍了,一路吐沫飛濺,邀請(qǐng)對(duì)方來(lái)喝喜酒。
當(dāng)天,請(qǐng)了北部灣的響嘴媒婆,帶上八樣禮品,水果糖茶,煙酒糕點(diǎn),最沒(méi)忘的是攢了十幾年的人民幣。
響嘴媒婆一張嘴,叭叭叭,把死的說(shuō)活了,石頭縫也開(kāi)花。何花爹娘,看著老李的父親很有誠(chéng)意,彩禮也帶來(lái)了,加上何花的哥哥,媳婦卡殼在彩禮上,正用這筆錢(qián)將兒媳婦討回家。
就掄起掃炕掃帚,掃掃炕面,“親家,來(lái),上炕說(shuō)話,何花她媽,你把那只公雞殺了,燉了。招待客人!”
老李實(shí)際上對(duì)何花不太中意。
他腦子里走不出賣(mài)電影票的草蘭。
可何花義無(wú)反顧地跟自己來(lái)了,老李又不忍拒絕。
但是,老李遺憾的是這輩子沒(méi)遇到愛(ài)情。
鳳姑嫁來(lái)的那個(gè)秋天,他記得很清晰。
九月初三的北部灣,天藍(lán)得一塵不染,坨坨山楓葉紅似一片瑰麗的晚霞。
尤其是白云,白得純粹,白得讓人妒忌。
老李,李顯貴,自己翻出一套平時(shí)舍不得穿的西裝,打上紅花領(lǐng)帶,皮鞋擦得锃亮。頭發(fā)噴了摩絲,收拾得很精神的老李,被何花損了一通后,訕笑著去給德利幫襯。
老李是德利的發(fā)小,他不去說(shuō)不過(guò)去,雖然大家各過(guò)各的日子,低頭不見(jiàn)抬頭見(jiàn),怎么也要伸伸手,拉一把。
德利也沒(méi)有別的想法,就讓老李給新娘子挑蓋頭。山區(qū)有一個(gè)習(xí)俗,新媳婦下車(chē)進(jìn)屋時(shí),在風(fēng)門(mén)口,要新郎的兄長(zhǎng)把蓋頭挑起扔房頂。
德利就一個(gè)姐姐,沒(méi)有兄弟。恰好老李大他一歲,也剛巧李顯貴一身筆挺的灰色西裝,儀表堂堂。
德利就坡下驢,吩咐他掀起鳳姑的紅蓋頭。
在紅蓋頭像一只興致勃勃的蝴蝶落在屋檐上時(shí),鳳姑在一陣早生貴子的祝福中,就被一張棱角分明的臉吸引住了。
確切地說(shuō),當(dāng)時(shí)的鳳姑,夢(mèng)幻似的錯(cuò)覺(jué)到,這個(gè)男人才是她的新郎官。
她怔怔地盯著老李很久,直到主持婚禮的人叫鳳姑改口喊婆婆叫媽。
老李就是在一瞬間,聽(tīng)到兩雙目光碰撞的聲音,擦出的滋滋啵啵的火苗。
也確定無(wú)疑地意識(shí)到,他的生命里,有一道風(fēng)景造訪。
3
老李心里始終橫著一堵火墻。
這堵墻很執(zhí)拗地橫了二十年,他的心邁過(guò)去無(wú)數(shù)次,腿則沒(méi)有動(dòng),不是不想動(dòng),而是他害怕那堵墻。
一旦拆了那堵墻,會(huì)有什么發(fā)生呢?
老李在天高云淡的季節(jié),或者夕陽(yáng)西下的黃昏,時(shí)常坐在院子的棗樹(shù)下,望著墻發(fā)呆。
他在搜索著同樣的一雙目光,就像多年前他用一根細(xì)細(xì)的竹竿挑起她的紅蓋頭,一瞬間,眸子的交集碰撞。
鳳姑躲著他,躲著內(nèi)心的一個(gè)隱私。
她情愿囚在思想里,讓一份情變成一只蝴蝶,守著一眼望不到邊的滄海,也不肯背離初衷。
德利的暗疾就是在結(jié)婚那天埋下的,怎么也不好,他試圖忘掉老李,李顯貴伸給鳳姑的眼神。
但是,他不可以,做不到忘記。
他最不濟(jì)就是曬一個(gè)脊背,對(duì)著鳳姑撲過(guò)來(lái)的夜晚。
有時(shí)候,德利的目光含著刀子,在鳳姑與李顯貴身上游來(lái)游去,卻不出聲。
德利就如溺水者,找不到一棵救命的稻草。
李顯貴呢?隔著一堵墻,沒(méi)有聽(tīng)到廝打聲,哪怕?tīng)?zhēng)吵聲,他也有理由邁過(guò)這堵墻。
許多年里,兩家有個(gè)大事小情,還是不斷聯(lián)系的。
素常日子,借個(gè)鐵锨、镢頭、剪子、刻刀,都是兩家孩子跑腿兒。
老李的女兒小鹿,比德利的兒子慕白大兩歲。
他們對(duì)火墻沒(méi)有任何概念和想法,哧溜哧溜,爬上爬下,像喝面疙瘩一樣順暢。老李家那棵小棗樹(shù)就依在火墻這邊,興高采烈地把枝蔓蔓延到德利家的菜園子上空,拋下一片林蔭。
晴朗的日子,棗樹(shù)被風(fēng)吹出一股股柔情似水的曲調(diào),密密匝匝的葉子,摟抱著德利的目光。
德利就在心里磨過(guò)砍刀,磨得鋒利無(wú)比,豎在日影里,就像一面鏡子。
照著李顯貴一張得意忘形的臉,這張臉從小時(shí)候穿開(kāi)襠褲摔泥巴玩時(shí),就一直笑盈盈的,好像沒(méi)有愁煩似的。
兩家人夏天,捧著飯碗聚在門(mén)口那口水井臺(tái)上吃飯,李顯貴的白瓷碗不是兩塊雞腿肉,就是白得耀眼的麥粉春餅。
德利的塑料碗內(nèi),躺著玉米糊糊或者高粱米飯,最好的是一疙瘩青椒炒雞蛋。
讀書(shū)的時(shí)候,德利和李顯貴一個(gè)班。
李顯貴做了學(xué)習(xí)委員,每天早晨收作業(yè)的時(shí)候,德利就在心里種下一千個(gè)愿望,他憤憤不平地說(shuō),李顯貴,遲早有一天,我要活得比你精彩,你等著。
德利揣著恨,又不得不向李顯貴妥協(xié)。
李顯貴和德利,兩家隔著一堵墻,僅僅是一堵墻。小孩子又是頑劣搗蛋的年齡,這邊干架,不到十分鐘就和好如初。主要是德利需要一個(gè)玩伴,德利的姐姐喜兒在家紡線,一梭子一梭子的白花花的繭線,擺在她閨房的床頭,紡來(lái)天邊朵朵彩霞,紡走窗欞疲倦的月牙。
德利不找李顯貴,他也會(huì)在某一時(shí)刻一顆腦袋趴在火墻上,朝那院撒目,揪幾聲口哨,一般是三聲。德利在第二聲口哨余音裊裊時(shí),就挪開(kāi)木板門(mén),把自己放了出來(lái)。
那當(dāng)兒,喜兒的紡車(chē)發(fā)出吱吱呀呀的呻吟,搖出沉淀在歲月里,谷物的香氣。
李顯貴就知道,德利會(huì)在第二遍口哨時(shí)出來(lái),就像他同樣在月亮地里,守著母親養(yǎng)的兔兔,感覺(jué)盛大的寂寞,鋪天蓋地而來(lái)一樣。
他們兩個(gè)清楚,彼此都被需要。
但德利不明白,大人們?yōu)槭裁丛诩?xì)枝末節(jié)的小事上不親力親為。譬如,母親借一根五號(hào)繡花針,也吩咐德利做她的腳。
哪一天同一個(gè)園子飄蕩的菜香,德利與李顯貴必能在飯口都可以吃到。
他們只有一堵墻的距離。
別看一堵墻,土墻也缺乏暖色調(diào)的鋪陳,更沒(méi)有建筑的音樂(lè)美,卻阻隔了心的交流。
有時(shí)候,德利和李顯貴在一起玩滾鐵環(huán),或者溜冰車(chē)。兩個(gè)就不約而同問(wèn),父母之間為什么不說(shuō)話,好像陌生人,又似乎被一層網(wǎng)網(wǎng)著,誰(shuí)也出不去,別人也休想進(jìn)來(lái)。后來(lái),德利去讀技校,學(xué)的是汽車(chē)修理。回來(lái)后就把廈子簡(jiǎn)單收拾了一下,抹了白灰,鋪了瓷磚,門(mén)口掛了修車(chē)的牌子,鼓搗起修車(chē)生意。
德利不單修大車(chē),誰(shuí)的獨(dú)輪車(chē)、自行車(chē)壞了推來(lái),照舊修。換小零件什么的給個(gè)本錢(qián),笑盈盈地接了,不嫌少,多了也不要。充氣筒充一下氣,要一毛。這是規(guī)矩,德利立的規(guī)矩,大伙一開(kāi)始有意見(jiàn)。細(xì)細(xì)一咂磨,一毛錢(qián)擱那時(shí),買(mǎi)十塊水果糖,一根小豆冰棍,一支麻花。
后來(lái),日子越發(fā)好過(guò)了,德利的兒子慕白滿大街跑,拎著瓶子打醬油了,充一次氣一毛的規(guī)矩也沒(méi)變,鄉(xiāng)親們就不吱聲了。
李顯貴靠手藝吃飯,德利也是。但李顯貴的木匠活兒被家具店搶了風(fēng)頭后,他的生意門(mén)可羅雀。
德利的修車(chē)行心靈感應(yīng)似的,日落西山。為嘛?屯子的年輕人都往城市奔。花了血本買(mǎi)一間火柴盒一樣的房子住著,寧肯租十幾平米的斗室,也不愿在北部灣侍弄土地,留守的人,養(yǎng)著零星幾臺(tái)農(nóng)用車(chē),即便來(lái)修理,哪能喂飽德利的修車(chē)行?
修車(chē)行空曠,可以塞進(jìn)整個(gè)村莊,一天之中,難得見(jiàn)個(gè)人影,倒是鳥(niǎo)兒常常光顧。
4
鳳姑奔跑的速度慢了下來(lái),大街上突然熱鬧起來(lái),有眼睛靠在樹(shù)后,或者柴草垛旁,瞄一眼,又瞄一眼。鐵锨和犁鏵都停止運(yùn)動(dòng),很有雅興地咀嚼著鳳姑。
終于出現(xiàn)一條狗,草狗。不是什么名犬,它一開(kāi)始比較警惕,用黑豆似的小眼珠盯著鳳姑,身上褐色的毛發(fā),被火苗舔過(guò),一片一片凹凸不平,就像掛著一張世界地圖。
鳳姑不再奔跑,跟她的一個(gè)意念密切相關(guān)。為什么奔跑?難道是對(duì)謊言的助紂為虐?
她想起德利掄過(guò)來(lái)的扁擔(dān),棗木扁擔(dān)經(jīng)不住歲月的盤(pán)剝,中間地段彎曲著,像一支拉不開(kāi)的弓。
這只扁擔(dān),先是在德利手上踟躕了一會(huì)兒,然后才不情愿地飛了過(guò)來(lái)。那時(shí)候,火墻一角正有目光在探尋。
扁擔(dān)驚飛了棗樹(shù)上的一對(duì)喜鵲,驚得火墻晃了幾晃,險(xiǎn)些跌倒。
鳳姑奔跑的原因很簡(jiǎn)單,也許,鳳姑還沒(méi)來(lái)得及思考先邁哪只腳合適,幾根神經(jīng)被割羊草似的,擼得生疼,就慌不擇路地射了出去。
扁擔(dān)在修車(chē)行屋檐下活了二十年,第一次被扯上戰(zhàn)爭(zhēng)的煙火。它有些興奮,也在想落在女主人頭上,肩膀一側(cè)會(huì)起什么效果?畢竟,扁擔(dān)的價(jià)值不是打人,而是挑著德利一家的天空。
停下來(lái)的鳳姑才發(fā)現(xiàn)自己赤著腳,好在花兒都開(kāi)了,在路邊的草坪上,蝴蝶也翩翩起舞了,幾朵白云棉花一樣飄來(lái)飄去,鳳姑的思想在蕩秋千,去哪兒?娘前年走了,沒(méi)有娘的老家是別人的,過(guò)完娘百日,爹就把一個(gè)女人領(lǐng)回家來(lái)。
鳳姑偶爾回去,拎點(diǎn)爹愛(ài)吃的豬皮凍,蒸一圈發(fā)酵饅頭,那次,爹生日。鳳姑就帶著這兩樣?xùn)|西走家。
放在炕桌上,繼母瞅了一眼,從喉嚨內(nèi)擠出一個(gè)哼音。
鳳姑就覺(jué)得饅頭也飄起雪花了,冷飯好吃,冷臉難受。爹不遮風(fēng)不擋雨的,鳳姑掃了一遍堂屋,墻壁上娘的相片,不知什么時(shí)候取下來(lái)了。
鳳姑扒拉一口飯,就匆匆忙忙折回了,爹哎哎了兩聲,像被噎著似的,卡殼了。
鳳姑的心被泡在鹽缸里,打磨得生疼生疼。
那天,鳳姑將娘家和婆家的路,拉長(zhǎng)再拉長(zhǎng)。
鳳姑知道,自己沒(méi)有真正意義上的娘家了,她看著爹,寵愛(ài)繼母的眼神就像春天里談戀愛(ài)的少男少女。
現(xiàn)在,鳳姑漫無(wú)目的,走著走著居然來(lái)到了坨坨河的上游。
下午的坨坨河,安靜得不像話。河面上平展得像一面鏡子,幾只潔白的鸕鶿仿佛點(diǎn)綴在畫(huà)軸上的云。河畔百年生的楊樹(shù),寧謐地佇立著,如一思想中的智者。
鳥(niǎo)兒的喧囂恰恰畫(huà)龍點(diǎn)睛,讓藍(lán)天更遼闊,大地更蒼茫,鳳姑第一次驚覺(jué),原來(lái)坨坨河可以美得徹骨,精致到靈魂。
許多年來(lái),鳳姑生長(zhǎng)在坨坨河,卻忽略了它的絢爛驚艷。
鳳姑坐在河邊的一塊青石板上,水面上映出一塵不染的藍(lán)天,樹(shù)影,以及自己一張有些憔悴的臉。那張臉還有一絲生動(dòng),素面朝天,不施粉黛,眉眼清秀,尤其是右眼下面一顆豆粒大的紅痣,娘說(shuō),美人痣。娘不止一次說(shuō),這美人痣不好,鳳姑問(wèn)了無(wú)數(shù)遍,鳳姑也不知道美人痣到底做錯(cuò)了什么?它寸步不離跟了幾十年,還在堅(jiān)守著,今天,鳳姑看著它有些扎眼。
一只布谷鳥(niǎo)挺著灰白的羽毛,扇動(dòng)著翅膀落在一坨巨大的磐石上,與鳳姑用眼睛交流,沒(méi)有飛走的意思。
瞧,它不僅以眼神傳遞對(duì)鳳姑的喜悅,又撩起迷人的歌喉,在一聲一聲編織人類(lèi)和鳥(niǎo)兒之間的友情。
娘在的時(shí)候說(shuō)過(guò),布谷鳥(niǎo)是很靈性的,它的造訪會(huì)給人帶來(lái)喜慶。
奔跑讓身體熱量暴增,虛汗淋漓,歇息后衣衫緊緊貼在前胸后背,鳳姑不由自主地苦笑,哪來(lái)的喜慶?慕白在學(xué)校寄宿,就讀的一中在市里,周末回家一趟,搬走下周的生活學(xué)習(xí)所需。
慕白每次出現(xiàn)在坨坨河,胳膊上必吊著小鹿。
坨坨河居住的人戲謔慕白和小鹿,一對(duì)小夫妻。
討他倆的喜糖吃,慕白靦腆,咬著嘴唇,不說(shuō)話。小鹿咯咯咯甩來(lái)一串百靈鳥(niǎo)似的笑聲,面包會(huì)有的,喜糖也會(huì)有的,還早著呢。
李顯貴對(duì)著女兒蕩秋千樣地吊著慕白沉默著,李顯貴不開(kāi)口,屋里的婆娘也噤聲,他女人低眉順眼,四間瓦房就是她的羊圈,但李顯貴家的門(mén)是敞了懷兒的。
李顯貴有理由相信,他女人何花,活在唐詩(shī)宋詞的炊煙里,不肯醒來(lái)。何花舞文弄墨,田間地頭成了她的書(shū)桌,寫(xiě)著寫(xiě)著,何花就招來(lái)了市電視臺(tái)的記者,也有了豆腐塊文章,一篇篇貼在各地報(bào)刊雜志上。
何花呢,對(duì)李顯貴除了床上的活兒,打理好家務(wù),收拾利整李顯貴和小鹿父女的衣食住行,一頭扎在寫(xiě)作中,鮮衣怒馬。
何花不動(dòng)聲色,守著李顯貴與家。把自己站成一棵樹(shù),她明明清楚李顯貴心底住著另一棵樹(shù),不說(shuō)。
她將李顯貴看得很重,比生命還燙手,沉甸甸地生長(zhǎng)在脈絡(luò)里,呼吸一下都是李顯貴身上的木屑味兒。
一個(gè)人在靈魂的層面扎根了,那是怎么努力也拔不掉的。
何花學(xué)會(huì)在一種自我消化的環(huán)境下,游弋。她允許李顯貴心中住著另一片陽(yáng)光,也是出于自信。李顯貴只是想想而已。
但是,何花沒(méi)法預(yù)測(cè),事物在不斷地發(fā)展,變幻莫測(cè)的節(jié)奏,能絆倒一個(gè)堅(jiān)強(qiáng)的人。
就如何花無(wú)法在火墻那邊揣摩一根扁擔(dān)扔出去后,接下來(lái)的故事,是喜是悲。
李顯貴捏著一柄月牙鐮出去割青草喂豬,何花收回停留在火墻那方的目光,進(jìn)房間打開(kāi)臺(tái)式電腦,為一篇小說(shuō)結(jié)尾,她猶豫不決,該是喜劇結(jié)束,還是留白?
何花小說(shuō)中的男主角,暗戀著堂弟的媳婦,此刻,男主角朝村莊的泉水河走去,河畔上密密麻麻遍及著蓊郁的青草,他要給家里的幾十只羊割大批的嫩草,還有三只母羊準(zhǔn)備產(chǎn)崽了,必須營(yíng)養(yǎng)跟得上。何花寫(xiě)到這里,抬頭望望窗外,院內(nèi)的一棵丁香樹(shù)盛綻著七色的花瓣,書(shū)上有記載,介紹過(guò)七色丁香,稀有罕見(jiàn),誰(shuí)擁有這種七色丁香花樹(shù),將有一段桃色故事。
何花突然想起,丁香樹(shù)是李顯貴從外地給人雕刻時(shí)帶回來(lái)的。
再繼續(xù)收尾,男主角在泉水河上源,鳥(niǎo)鳴山澗,水流潺潺。陽(yáng)光熾熱地貼著他,他想洗個(gè)澡,然后,割草。大片大片的青草,嫩生生的可以掐出湯兒,羊十分喜歡吃呢。
男主角脫了上衣,剛要拉開(kāi)褲帶,冷不丁發(fā)現(xiàn),白楊樹(shù)掩映下的陰涼處坐著一個(gè)人,確切地說(shuō),是個(gè)女人。
男主角盯著女人的背影,似曾相識(shí)。
難道是做夢(mèng)?這泉水河上游古木參天,又地處山脈環(huán)繞,誰(shuí)家女子敢獨(dú)自來(lái)這里?莫非是傳說(shuō)中的白狐?
男主角謹(jǐn)慎地挪了過(guò)去。
此刻,鳳姑面前的坨坨河上,多了一張棱角分明的臉,鏡子打了一個(gè)擺子,開(kāi)始呻吟起來(lái)。
5
李顯貴把木匠那套家什在院子里砸得稀碎的上午,五月的北部灣就像一塊質(zhì)地柔軟的綢子,被突然的雜音劃出一道裂痕。
在田埂堤壩忙碌的手掌,下意識(shí)地攥緊鋤頭和镢頭,它們配合著耳朵和心臟,朝著劃過(guò)絲綢的聲響,張望。
李顯貴為什么要砸掉跟隨他半生時(shí)光的工具?
誰(shuí)也不清楚,李顯貴究竟哪根神經(jīng)出了毛病,也許是逃避坨坨河沿岸的父老鄉(xiāng)親請(qǐng)其做棺材?
就在大家將好奇的心揣著,一路跟頭把式地涌向李顯貴家門(mén)前,老氣橫秋的土街上,步奏穩(wěn)妥地開(kāi)來(lái)一輛墨綠色越野車(chē)。
越野車(chē)就像一只疲倦的甲殼蟲(chóng),喘著濃重的粗氣,吱的一下,泊在李顯貴門(mén)口。
李顯貴木制的家什被投進(jìn)火堆,還在燃燒。青煙暴怒地抽打著空氣,一股子棗木的香氣,撲面而來(lái)。火苗忽閃著眼睛,委屈地看著世界。
那幾塊尚未被火勢(shì)吞沒(méi)的木頭,對(duì)這個(gè)凡塵充滿了依依惜別的眷戀。
木頭的一生,在火苗的切割中,化作一縷煙霧,在空曠的天際消散。
越野車(chē)上下來(lái)的人,目睹了李顯貴燒毀木匠家什的現(xiàn)場(chǎng),他的身子不禁一踉蹌。三十年前的夏天,他寄宿在坨坨河的生產(chǎn)隊(duì)閑房?jī)?nèi),月色朦朧的夜晚,叩開(kāi)他木板門(mén)的少年,手中躺著兩枚又大又紅的桃子。
那時(shí)候的蘋(píng)果、桃子比豬肉金貴。少年捧著桃子,送來(lái)一臉月亮般的微笑。
一瞬間,他的心豁然開(kāi)朗,感到生命里,驟然遍及著美麗若水的月光。就是兩枚桃子打開(kāi)了他和少年交流的窗戶,更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或者少年與他的父親也蒙在鼓里。
坨坨河接納了他一個(gè)異鄉(xiāng)人,也為他暗戀的種子找準(zhǔn)了一片肥沃的泥壤。
月朗風(fēng)清的坨坨河畔,天做鋪蓋,地當(dāng)床。
桑葚大紅大紫的季節(jié),唧唧鳥(niǎo)在蘆葦蕩里一聲一聲編織的小夜曲,撩撥得他骨節(jié)粗大,心靈的城池兵荒馬亂。柳梢頭,月兒笑瞇瞇地?fù)еβ┮曋蟮亍?/p>
他的歌哨在那家院墻外幽怨傾訴時(shí),一扇窗滅了一盞燈。
這樣的偷,令他忐忑不安,收下關(guān)門(mén)徒弟之后,他一心一意把畢生所學(xué)傳授給月光下叩門(mén)的少年。
后來(lái),他離開(kāi)坨坨河,原因是夢(mèng)里女兒在呼喚,爸爸回來(lái)吧,奶奶生病了。
似乎一切皆是天意,兩個(gè)原本不同軌道的人,在地球的一隅遇見(jiàn),偶然地擦出火花,但彼此都固守著一座責(zé)任的喜馬拉雅山,所以,他選擇了回程的車(chē)票。今天,他捋著嘴巴上攀附的幾根白胡須,仿佛捋著一段段悲歡離合的光陰。
他盯著一攏火光,情不自禁地苦笑了一下,在和當(dāng)年的少年眸子對(duì)接時(shí),淚居然不假思索地滾落出來(lái)。
李顯貴先是皮笑,接下來(lái)肉笑,筋骨也隨著情緒的變化,轉(zhuǎn)換成春夏秋冬的標(biāo)識(shí)。冷,熱,暖,愁。猛地,李顯貴碰觸了何花驚慌失措的表情。
這張表情,李顯貴在電視劇里經(jīng)常讀到,沒(méi)曾想,活在電視劇中的表情走下熒屏,在硬邦邦的現(xiàn)實(shí)版圖,給了李顯貴一瓢涼水。
李顯貴絕對(duì)相信,此時(shí)的何花,就是一位很有演技的明星,不愧是坨坨河畔被炒來(lái)炒去的鄉(xiāng)土作家。
李顯貴被自己驚出一身冷汗,他張巴了半天嘴,愣是沒(méi)喊出師傅二字,何花卻用一個(gè)請(qǐng)進(jìn)的姿勢(shì),結(jié)束了不尷不尬的重逢儀式。
坨坨河的人明白,這坨大地上,會(huì)有一場(chǎng)花事上映,亦如多年前,流淌在桑葚樹(shù)叢里的戀曲。
鳳姑呢?橫亙?cè)趦杉抑虚g的一堵墻,這一天不知為什么被德利掄起的鋼釬捅個(gè)大窟窿,石頭稀里嘩啦,打亂的算盤(pán)珠子似的,落在雙方的菜地上,德利沖著坨坨河上空,甩出鞭子般的嚎叫,“我就是個(gè)王八蛋……”
坨坨河不復(fù)往昔的平靜,這是枯燥了很久的坨坨河人,從骨髓到靈魂都長(zhǎng)出腳的場(chǎng)景。
他們就連吃飯的工夫,端出飯碗,蹲著站著倚著,在某某的大街上,一邊吞咽著谷物,一邊繪聲繪色地講述著那堵火墻牽引出來(lái)的故事。
每張嘴巴在捌飭米粒與蔬菜的過(guò)程中,將坨坨河昨日的沉寂撕開(kāi)一條豁口,一系列關(guān)于幾位演員,誰(shuí)是主角,誰(shuí)是配角的爭(zhēng)論,比露天電影走街串巷演出還熱鬧。
一場(chǎng)大雨,讓北部灣街上汪著一泡泡雨水,雨過(guò)天晴,一顆日頭,展開(kāi)激情的臂膀,熱烈地?fù)肀е@片土地上的一花一草。
螞蟻上樹(shù),蝴蝶扇動(dòng)翅膀繞著花花草草飛舞。
一串喜慶的煙花爆竹聲,在坨坨河岸畔盤(pán)旋。
李顯貴春風(fēng)滿面,伸著剪子,在兩名禮儀小姐扯著的紅綢布中央,剪彩。
一塊龍飛鳳舞刻著李章木器加工城的牌子,高高坐在李顯貴家新壘起來(lái)的大門(mén)樓上。
大伙像提前過(guò)年一樣,穿戴一新,來(lái)看西洋景。
很多人在議論,牌匾上那個(gè)章字是緣何而來(lái)的?
這時(shí),人們吃驚地發(fā)現(xiàn),德利竟和李顯貴一左一右戳在李顯貴的師傅身邊,儼然沒(méi)有了仇視和隔閡。
接著,有人爆出,牌匾上的章字,其實(shí)是李顯貴他師傅的姓。
德利被任命為李章木器城的副總經(jīng)理,負(fù)責(zé)隨章師傅去南方進(jìn)貨,洽談業(yè)務(wù)。
李顯貴是經(jīng)理,主要是對(duì)各種款式家具進(jìn)行加工創(chuàng)作。
剪彩儀式完畢后,德利召集幾個(gè)男勞力,徹底拆了那堵墻,騰出自家院落,廈子,放置家具,招攬生意。
鳳姑對(duì)周末回來(lái)住的慕白說(shuō),“好好和小鹿相處,以后考上大學(xué),你倆能不能走到一起,就看上天怎么安排了。”
慕白啃著娘燉的糖醋排骨,只覺(jué)得唇齒間都是肉香,他面前晃動(dòng)著一個(gè)女孩清純的笑臉,每個(gè)周末下午二點(diǎn),女孩必到學(xué)校的圖書(shū)室看書(shū)。
慕白只知道她是城市女孩,父親是物資局局長(zhǎng)。
一陣丁香花的芬芳沿著窗戶卷了進(jìn)來(lái),慕白抬眼瞅了瞅,今年的丁香花唯獨(dú)紫色的花瓣不是七色丁香花。
責(zé)任編輯/董曉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