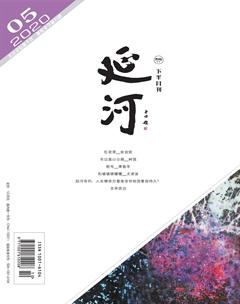陽坡坡曬暖暖(外二篇)
春天說來就來,搭眼望去,村東小河兩岸的柳樹枝梢,似乎一夜間就上了色,淡淡的、黃黃的,河里也響起了汩汩的流水聲。
春一到,莊稼人便忙開了,蟄伏了一冬的小麥起了身,鋤草、施肥、澆水、滅蟲,各種農活一樁接著一樁。抽穗、揚花,南風一起便麥浪滾滾,“算黃算割”鳥兒又飛了回來,不停地在濃密的樹葉間鳴叫著,莊稼人沒黑沒明,收割碾打,龍口奪食。這邊揮鐮割倒了麥子,那邊又吆牛犁開麥茬地,施肥、耱平,撒下苞谷、谷子、豆子籽種。又是一番番鋤草、澆水、施肥、滅蟲,直到把各類秋莊稼一一收回,再種下小麥,那風就寒了,霜也降了,空中飄起了雪花,地就上了凍,這大半年里,一天也不敢休息,更不敢耍奸溜滑,舍不得出力;否則,你哄地皮,地皮就哄你的肚皮。日子,歲月,就在這一天天、一年年、一輩輩中輪回著。
只有入了冬,才是莊稼人的休閑日,懶覺可以睡,直睡到日上三竿;那早飯自然就吃得遲,吃畢飯,紅彤彤的太陽艷艷地照著,百無聊賴的人們就三三兩兩聚到了陽坡坡地界,曬開了暖暖。
叫作陽坡坡,其實未必有坡,只是村巷間避風向陽的地方。靠墻矗立著一溜苞谷稈,身著黑粗布棉褲棉襖的莊稼人,一個個依偎在苞谷稈上,瞇著眼睛,享受著冬日暖暖的陽光。
曬暖暖的陣容看似雜亂無序,隨意蹲坐,實則大有講究,大體分為男女各一堆,不太混雜。這男人又按年齡來劃分,年輕人一群,拄拐棍的老漢們一伙,至于娃娃們則不分性別,大人窩子里竄來竄去,相互追逐嬉鬧。
秦地天高土厚,造就了秦人生冷蹭倔的性格。同時,秦地封閉,秦人又封建,尤其是那女性,還是姑娘時,把那身體發膚看得金貴;即使酷暑三伏天,也是長衫長褲,連腳面也不輕易示人,遇到陌生男人同他說話,未言開,臉先紅。但艱苦的農家日子,繁重的農活卻一樣不比男人少干,還要經管屋里老小的一日三餐、縫補漿洗;待到結了婚,有了娃,便粗放豪爽起來,再無昔日的羞澀靦腆,眾人面前敢解衣敞懷露乳,給娃娃喂奶。這不,冬閑曬暖暖,也基本上人手一個針線笸籃,不是縫衣連襪,就是納鞋底子,要不就是織毛衣。手不閑,嘴更不閑,從兒女到公婆,從小姑子到小叔子,夸贊著,抱怨著。當然,時不時還要說幾句連男人都不敢說的葷話;所以,婦女窩里最熱鬧,嘻嘻哈哈,哭了笑了,就像搭起了一個戲臺子。
男人們閑下來最喜歡耍的游戲是丟方、狼吃娃,就地用樹枝劃幾個方格,一方用土坷垃,一方用短柴秸,你布一子,我跟一子,類似于現在的五子棋。但下的人往往做不了主,周圍看熱鬧的反而常常越俎代庖,因而丟方、狼吃娃攤子前,從一開始就吵吵嚷嚷,喊聲叫聲抱怨聲不絕于耳。
這一切,老漢們都看在眼里,但也只是微微一笑,更多的是抽著旱煙鍋子,揣著心事,懷想著久遠的過去,從年輕后生們的身上,回憶著當年的自己,相互間說的都是幾十年前的陳芝麻爛谷子,因為耳聾,常常是問東答西,各說各話。也怪,人老了,夜隔黑吃得啥飯都想不起來,但童年時的某件小事卻記得清清楚楚。每年的冬天,對老人而言,就是一道坎,這不前幾天,還在一起曬暖暖的一位老弟兄,一夜之間,卻再也沒醒過來,現在已躺在了北溝的黃土下了。唏噓過后,竟然流著長長的口水,睡了過去。忽然間,覺得身上有什么東西在蠕動,于是迷迷糊糊地伸手抓撓癢癢處,竟捉住了一只肉乎乎的虱子。頓時,睡意全消,正好此時周身也曬得熱乎乎的,于是索性脫掉棉襖,光著上身捉起了虱子。捉完了自己身上的,還會把小孫子、小孫女叫來,躺在自己腿上,再為他們捉虱子。
莊稼人平時沒啥零食可吃,時令的桃杏李棗此時早已過去。冬天里,只是偶爾將苞谷粒用鐵鍋炒熟了當作零食,奢侈些的,還會炒些黃豆、黑豆。起先是一個人偷偷從衣兜里往外掏,趁人不注意了往嘴里放幾粒,但咯嘣咯嘣聲又怎能瞞得了大伙;于是,眾人一擁而上,從口袋里硬是統統掏了出來,散給大家分享,沒分到的,還罵著逼其再回家拿些來,一大鍋炒苞谷豆就這樣給分食了。偶有那掉在地上的幾粒,恰被在人窩空間處趾高氣揚昂首踱步的大公雞給叼了去,但自己卻不舍得吞下,而是嘴里發出一陣“咕咕咕”的叫聲,召喚在附近覓食的母雞來食。
幾只跑出圈的豬,也跑來陽坡處湊熱鬧,偶有哪個碎崽娃子拿樹枝為其撓癢癢,便立馬躺在地上,瞇縫著眼睛,盡情地享受著陽光,享受著撓癢癢的舒爽,嘴里哼哼著,流著長長的涎水。
這暖暖一曬,就到了午后二三點,直到天上堆起了云層,地面刮起了大風,人們這才意猶未盡地四散回家。
清泉心中流
飲食二字,飲為先,食在后。雖說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但人三天不吃飯,絕無性命之虞;若三天不喝水,結局不堪設想,足見水的份量之重了。
自古八水繞長安,河流縱橫,水源豐沛,但昔日鄉村吃水,還是以掘井為主,村村也必有幾口老井,村民就近按片絞水。世世代代,人吃馬喂,羊飲雞喝,都是取自井中絞上的水,那石板砌嵌的井沿,自然就被絞水用的繩索,生生勒磨出了一道道深痕,一道道歲月的印跡,猶如老人臉上的皺紋,硬是日子苦熬出來的滄桑。過去人們出外謀生、求學、當兵,就叫背井離鄉,游子歸來,端碗必言:“又喝到家鄉的水了,真甜吶!”
秦人性直,不善甜言蜜語,更不會虛情假意,言語聲高,唱戲似吼,顯生冷蹭倔,但實在、厚道、本真。像那渭北旱原,水極金貴,地下水深,打井困難,動輒就得幾十丈下掘,靠镢頭挖,藤籠提土,稍不留意,塌方、傷人、折人的慘劇便常常發生。待費盡千辛萬苦掘得一井,不是不出水,就是又苦又咸,無奈,眾多莊戶人家只好平地挖窖,將雨水引入,將冰雪儲之,日常生活用水全賴于這窖水。窖水色如鐵銹,存儲久了,里面還生有紅線線蟲。平時惜水如油,早上起來洗臉,也是一盆水先盡老的洗,再讓小的洗,最后才是漢子、媳婦洗,都洗完后,再給雞羊豬狗飲。若是天旱久了,窖水吃完,還得翻山下溝底,來回上十里的往家挑溝里的水。盡管如此,若有路人進門,一聲:“有人嗎?討碗水喝。”家中無論誰在,都二話不說,將碗拭凈,一碗滾燙的開水遞到眼前,“嫑著急,小心燙著,不夠再倒。”喝多少眉頭都不皺一下,但討水者若將喝不完的水順手倒掉,對不起,立馬會翻臉,攆你出門。
農家生活清苦,來了親戚朋友,甚至鄉黨串門,沒有糖果、瓜子招待,進門首先問:“喝水不?”不管怎么回答,一碗白開水必端過來。不是舍不得放茶葉,而是家中實無茶葉可放,平日間自己也是喝的白開水,頂多就是到竹園采些竹葉,或是摘些沙果樹葉子晾干,充當茶水,說這東西清火、開胃。只有遇到紅白大事了,這才稱上二斤磚茶,招待客人和幫忙的鄉黨。誰家若有在外干事的人買回幾兩香片,那就寶貝的不得了。說白了,那不過就是茉莉花茶,若有幸喝上,至少會在鄉黨們面前炫耀半年。從不請你“在這把飯吃了吧”,那都是客套話,所謂“讓人是個禮,鍋里沒下米。”但只要飯時一到,必先給來客盛滿吃飽,哪怕飯不夠了,自家人空著肚子哩。
莊稼人苦,每天起雞啼,睡半夜,精心侍弄那土地。天還麻麻亮,就起身下地了,干糧可以不帶,必用黑陶罐盛滿開水,拎著到地頭。不論耕、耱、刨、扒、種、收,都是出大力的下苦活,一會兒工夫,那汗水就順著尻渠子往下淌。這時,就得到地頭歇一歇,先喝水,再抽袋煙,然后接著再干,也許還未等到收工呢,那罐水就先喝完了。回到屋里,農具一放先絞上一桶水,舀一瓢,美美地咕嘟灌上一氣,爾后再給同樣出了大力的牛馬端半盆,還不忘撒上兩粒青鹽,那牛馬同樣干渴極,頭低到盆里,眨眼間,一盆水就喝干了,這才打著響鼻,舒適至極。
莊稼地附近若有河溪,就省卻了帶水的麻煩,下地前,先到河邊沙灘挖一小坑,讓那河水慢慢滲入,待到人困馬乏時過來,那坑里就滲滿了水,經過沙子的過濾,清清亮亮,澄澈至極。用手掬著喝,或是低頭飲用。流動的河水一般不喝,因水面漂浮著枯枝敗葉,雞毛蒜皮,還有其他臟發。
喝水最不愁的還是進終南山里砍柴、采藥,滿山青翠的林木,涵養了條條溪河,累了,渴了,餓了,啃幾口干饃,捧幾口山泉水,再擦洗一下頭臉,困乏、饑渴頓解,那山泉水還性硬,就著干饃喝下去尤其頂飽,半晌也不會肚饑。
到了生產隊時,土地收歸集體,干活也都是以鐘聲為令,社員統一下地,這時便有專人負責絞水,擔著送到地頭,因為人多,需求量就大,一晌要送好幾趟水呢。送水時,桶面最好放片荷葉,沒有荷葉的,南瓜葉、蓖麻葉也可代替,目的就是防止水漾灑出來。有些條件好些的生產隊,還會從供銷社買些糖精,苦焦的莊稼人見了糖精水,忍不住就要多喝幾口。
只有家中的老人娃娃身體不美氣了,或是媳婦來那個了,肚子疼痛,這才舍得往開水里沖些白糖、紅糖,喝著甜滋滋的糖水,是那年月最奢侈的享受。而莊稼漢自個兒若不美氣了,卻從不舍得喝糖水,把那野菜涹的漿水,舀上半碗,咕嘟嘟下肚,說那東西清火祛毒,口舌生瘡、耳鳴目赤、頭痛發熱,你還別說,真見奇效;漿水喝完,炕上蒙頭睡上一覺,第二天起來,癥狀全消,身子立時輕快了許多。
盼? 歸
一棵粗大的老槐,蔭庇著這座小院,小院門口,蹲一塊碌碡般的石頭,橢圓、面平光滑,正好坐人。石自村東河中撈回,不知何年蹲于門口。院里的房子,由胡基蓋起的廈房,變成了鞍間房,又由鞍間房變成磚砌的二層樓,但那石頭始終沒動、沒變。
從屋內到門口,也就十余步,若放幾十年前,一抬腿的事兒。那時,一走便是數十里,不喘不歇,每周從單位到小家,都要走幾趟。每年從小家到老家,也要走幾趟。或許正是年輕時走得太多了,如今,雙膝受損,一移步,膝關節便“咯嘣”作響,針刺般疼痛,只能一手拄拐,一手扶墻,艱難地挪至門口,坐于石上,靜靜地、呆呆地瞅著門前的小路,天陰、天晴,花開、花落,葉綠、葉黃,只要無雨無雪,老漢必定坐在石頭上,雕像般,半晌或一天。
往來的人腳步匆匆,幾乎無人與老漢說話,偶有招呼的,老漢也聾得聽不見,問東答西,各說各話。只有村里的一條小白狗,時常跑到老漢面前,搖搖尾巴,蹭蹭褲腿,臥于老漢身旁,與之為伴。
老漢坐在門口,無人知其用心,只有老漢清楚,是在等城里工作的兒女回來。其實兒女只有在周末才能回來,但老漢只有坐到石頭上,眼瞅著這條小路,心里才有了期冀,心中也才踏實。人,遠遠地走來,近了,才看清不是,又一人走來,依然不是。坐著坐著,老漢就睡著了,涎水長長地順著嘴角,順著雪白的胡須淌下。依稀間,那小路的盡頭,一位年輕人闊步如飛,朝這邊走來,直到近了,老漢才看清,那年輕人,竟是當年的自己。
老漢離開村子,離開這座小院時,還是一個半大小子,要到省城學徒去了。臨行時,滿頭秀發的母親,給兒子塞滿了連夜烙出的鍋盔,又裝了一罐漿水菜。母親知道兒子愛吃漿水菜,扭著小腳,一直將兒子送上大路。兒子幾次讓她回去,她口里答應著,依舊遠遠地跟在后邊,直到看不見了,這才返回,癱了般一屁股跌坐在石頭上,放聲大哭。這之后,母親就常常坐于石上,眼睛瞅著小路,盼著兒子的身影。
當雛鳥剛剛長出羽毛之時,最常做的動作就是揮動、忽閃著翅膀,急欲離開巢窠。年輕時的老漢也是如此,打走出家門,來到省城后,這座小院,便在他的心里。變成老家了,也只是在與外人交談時才偶爾提及。那時,一年也回不來幾趟,愈是如此,母親坐在石頭上的次數便愈多,時間也愈長。
老漢在城里成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兒女,忙于工作,兒女無人帶,這才想起了老家,便領回來讓母親幫著帶,此時也才感到母親住的老家,才是天底下最溫暖、最安全、最可依賴的家。待兒女到了上學的年齡,又一個個帶離老家,回城上學。這時的母親頭發已花白,走路也拄上了拐,一擰一擰,送兒子、送孫子到大路上,直到遠去,瞅不見了,這才又擰回屋前,坐在石頭上,悄悄抹淚。一年又一年,不論何時回來,都遠遠地看到母親坐在石頭上,靜靜地等,默默地盼,待走近,才發覺母親已靠在墻上睡著了。一聲“媽!”驚醒了母親,用袖口擦拭著渾濁的雙眼,半天才顫著聲回應:“終于把俺娃等回來了!”雙手緊緊地攥住兒孫的手,生怕他們離開。
掏出帶回的各種吃貨,母親總是抱怨著:“屋里啥都有,花那錢干啥?”兒子一一攤開,而母親一口也舍不得吃,又一一收好,抬到板柜里,留著給孫子孫女慢慢吃。聚少離多,聚短離長,臨別時,又把小米、苞谷糝、紅豆各裝上一小袋,還要再裝上一罐漿水,硬讓兒子帶回城里慢慢吃。
那年冬天,早起,母親又往門口石頭上走時,一個爬撲跌倒,再也未能站起來。待兒子聞訊匆匆趕回時,門口的大石頭上空空蕩蕩,母親靜靜地停放在屋內的床板上,最終都未能聽見那一聲聲“媽,媽”的哭喊。而兒子的耳旁自此總響著“俺娃回來了”的聲音,永遠也揮之不去了,以至常常于夢中答應著醒來。
兒子終于也成了老漢。兩年前,老伴也先他而去,老漢便堅持從城里回到了當年急欲離開的老家,似要陪伴母親,更似彌補自小離開母親的缺憾,因為母親就埋在老屋門前的那道溝坡下。已成家立業的子女,也是帶著自己的子女,定期回來看看。有時因各種原因未按時回來,老漢便涹上些漿水菜,拄著拐,搭上長途車,磕磕絆絆地送給城里的兒女后,返身又回到老屋,每天就這樣坐在石頭上,默默地獨自等著、盼著兒孫的歸來。“爸”,“爺爺”,幾聲呼喊,將老人從睡夢中驚醒,老漢睜開昏花的老眼,一個似乎年輕時的自己立于面前,這才意識到:“哦,俺娃回來了。”這聲已哽咽,眼已潮濕。
一夜之后,兒孫們又要走了,老漢拒絕了兒孫的勸阻,拄著拐杖,艱難地扶著墻,挪到了門口,目送著他們漸漸遠去,這才坐到石頭上,又開始了等待……
尤凌波,陜西商洛人,現供職于西安日報社。出版散文集《風從場上過》《隨風不遠去》《溝底有人家》等,曾獲第五屆柳青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