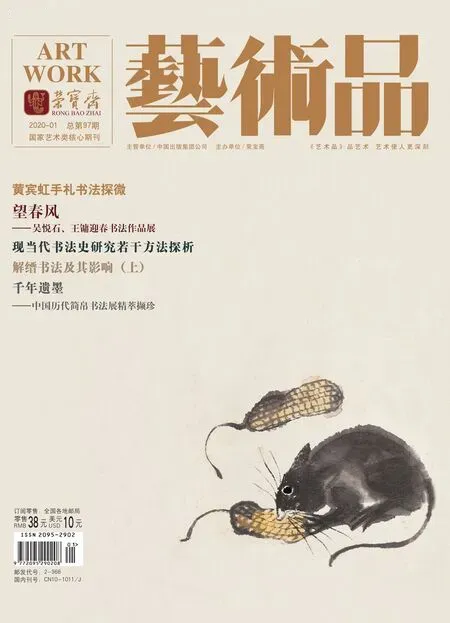民國時期的北京書風·馮恕
文/鄒典飛
馮恕(1867—1948),字公度,號華農,室名“蘊真堂”(“蘊真”取自光緒帝所賜“蘊真愜遇”匾額1),原籍浙江慈溪,寄籍直隸大興。宗室載洵任海軍都統時,馮恕先后任海軍部參事、海軍部軍樞司司長、海軍協都統等職。庚子之變(1900)后,馮恕與史履晉、蔣式惺倡議創辦京師華商電燈股份有限公司。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參與創辦京師華商電燈股份有限公司,任總辦,后任協理、總理等。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隨載洵赴英、法、日、美等八國考察。1921年,在北京司法部街開辦電氣學校,任校董。
馮恕是中國近現代著名的實業家、書法家、文物收藏鑒賞家。輯有《馮氏金文硯譜》,刻成《蘊真堂刻石》《馮母纂懿流光錄》等。民國時期,馮恕以擅寫匾額馳名京城書壇,前門大柵欄的“張一元”茶莊、西四的“同和居”飯莊、“中華大藥房”等匾額均出于其手,坊間有“無匾不恕”“有匾皆有恕,無腔不學程(程硯秋)”之美譽,馮恕與擅寫匾額的山東京官領袖王垿齊名。如今馮恕題“張一元”茶莊匾額已為董石良所書者取代,馮題匾額現藏于首都博物館。“同和居”飯莊、“中華大藥房”匾額則因年代久遠不知去向。而前門大柵欄一帶的民國舊建筑中至今仍存有一些馮題匾額,可見昔日馮恕在京城書壇的影響力。
除活躍于政商兩界外,馮恕還是京城著名的文物收藏鑒賞家。他常年活躍于琉璃廠、隆福寺等地的書肆和古玩鋪,以購藏古物為樂。馮恕曾賦詩云:“平生嗜好惟金石,鐘鼎圭璋四壁陳。山腳水湄通燥潤,花文篆體辨精神。時猜虞夏商周漢,浸別銅鉛血汞磷。共羨蘭閨雙白璧,居今稽古養天真。”2他的藏品包羅萬象,不乏稀世奇珍,其中包括著名的秦穆公敦、克鼎、虢季子白盤等一百四十多件青銅器。他曾與葉恭綽、鄭洪年合資購買西周青銅重器毛公鼎。同時,馮恕也是京城著名金石社團“冰社”的重要成員之一。他所藏《玉敦齋所藏吉金》24 器由“冰社”副社長周康元制作拓片,輯錄成書,對外發售。
1921年至1927年,馮恕主持刻成私家《蘊真堂刻石》,內容選自元代之前未曾刊刻或刻石不存作品39件,共計54方。刻石每塊長92厘米、寬30厘米、厚8厘米,此刻石至今仍鑲嵌在北京市西城區羊肉胡同73號馮家祠堂的東廂房內(原陸潤庠舊居)。《蘊真堂刻石》頗能反映出馮恕的書法品位和好尚,他在刻石末尾自題:“恕學殖荒落,功業無聞。垂老值鼎革,居閑處獨,于人海嗜好泊然無染,惟潛心于書畫鼎彝,以消歲月,所聚漸多……”3此刻石之所以聞名,還在于馮恕出資聘請陜西關中雕刻家郭希安刊刻。郭氏刻石工藝精湛,深得京城各界名流的推重。馮恕贊其技藝:“指腕齊力,精入毫芒,弄刀如飛,神合古人,冥入無間。”4郭希安還為馮恕刻成《馮母纂懿流光錄》。馮恕之母俞太夫人逝世后,馮氏遍請京城各界名流所作哀誄傳贊詩文共計47 首,撰文書丹者皆為一時俊彥名流,如李經畬、陳寶琛、奭良、曾習經、張鋆衡、曹廣楨、王樹枏、趙世駿、張權、柯劭忞、朱益藩、劉若增、宋伯魯、寶熙、袁勵準、許湛儒、吳士鑒、閻迺竹、葉恭綽等。
1927年至1929年,馮恕將其所藏青銅器銘文和鑒賞、考證文字,請郭希安刻于古硯之上,歷時七年之久,編成《馮氏金文硯譜》。此譜由李經畬題簽,宋伯魯、馮汝玠、孫壯、葉恭綽作序,后有柯昌泗題跋。時人贊之曰:“先生此譜開著錄之別裁,定鑒別之標準。”5馮恕逝世后,其家人按其所囑將他所藏文物全部捐獻國家。
目前關于馮恕的生平和書法資料流傳不多,筆者所知者有馮恕曾孫馮肅元先生編《公度馮恕書法》、劉季人撰《馮公度二三事》、北京市西城區文物管理處編《蘊真堂石刻資料集成》等。《公度馮恕書法》中收錄有馮恕書《公度自挽詩》,此詩可對其生平略作增補。
“貸賒質劑平生恥,艱苦辛勤志不灰。假館課徒供菽水。曾就沈立山、徐仲文、蹇宣甫、葛杏坡、孫仙舟、韓寅生六家西席,駢文小札佐鹽梅。余為立玉甫、瞿子玖、楊蓉浦、宋芝田作通套信,每封當十錢二千,數年之久,扇聯書罷饑寒減。每逢鄉試考官出京皆寫聯扇,為在外應酬之品。余每代書百扇十二金或十六金,百聯亦如之,余一日能書二百聯,連日書之,可以有一二百金入門,諛墓文成布粟來。一碑銘寫作得二三十金。堪嘆衰親共勞瘁。老母時年六旬,為恕磨墨伸紙恒至夜分,追思往事有余哀。”6
從詩中可知,馮恕早年頗為勤苦。他以“貸賒質劑”為恥,不得已“假館課徒”于沈立山(沈維誠)、徐仲文、蹇宣甫、葛杏坡、孫仙舟、韓寅生諸家,曾為立玉甫(立山)、瞿子玖(瞿鴻禨)、楊蓉浦(楊頤)、宋芝田(宋伯魯)等做通套信,還代鄉試考官書扇面及對聯,此舉或迫于生計,而其母俞太夫人年高六旬仍為其磨墨伸紙至夜深時分。這是馮恕追憶其早年生活的一些片段,雖吉光片羽,亦彌足珍貴。
“祖考科名甲第宗,下臨不肖墮家聲。余小試三次未冸,辛卯癸巳甲午丁酉四次鄉試未中試,庚子后遂停科舉矣。鹿鳴黌序全無兮。司馬黃堂僅具名。先保同知又保知府,分省補用三品銜。歐美遍參君相府。隨洵邸歷聘英、法、意、奧、德、俄、日本、美國諸邦。頭銜叨晉大臣榮,征塵甫卸逢奇變,天意何居厄有清。”7
從詩中可知,馮恕祖父、父親均通過科舉制度取得舉人以上功名,而馮恕的舉業似乎頗為不順,他參加四次方考中秀才,之后鄉試四次(1891、1893、1894、1897)未中,后逢科舉廢除(1905),對此馮恕頗引以為憾。從《蘊真堂刻石》馮恕于刻石末自題“恕學殖荒落,功業無聞”亦可作為補正。隨后馮恕“先保同知又保知府,分省補用三品銜”,受到宗室載洵賞識,供職于海軍部,隨載洵赴英、法、日、美等八國考察,一度仕途頗為順利,后值庚子之變,國事日蹙,其事業或受到一定影響,馮恕對此感慨良多。
《前二首尚有未盡之義,再賦三截句》:“不遂名流尋雅興。詩社文會從不列席,忍教寒士窒生機。李毓如、蔣乃勳、祝椿年皆以賣字為生,三人故后才出潤格,今四年耳。滿懷利濟成虛愿,留待兒曹繼述之。”8
此詩馮恕談及自己早年很少參加詩社文會,可能由于其科舉功名不高,詩社文會參與者多為“翰苑”中人,故他很難融入其中。但從前詩中可知馮恕的書法很早即頗為出名,詩注中還記錄了同時期鬻書的李毓如、蔣乃勳、祝椿年等人窘困的境遇。
“福薄平生甘淡泊。一生食不兼味,戊戌年雞鴨魚蝦蟹未嘗入口,家貧矢志遠金錢。壯年創辦北京電汽公司,成本四百五十萬元,強仕于役,崇陵充監修監督,洵邸命余管收支,堅辭謝卻,邸憂容之。入民國辦順直大振亦二三百萬,自知窘人子,從未經手銀錢。只今垂老雖貧乏,魂夢皆清體氣堅。未受官刑未招謗,戰兢七十七春秋,深埋淺葬隨兒輩,全受全臨汔可休。”9
馮恕是深受科舉制度影響的士人,他對取士受挫之事念念不忘,后雖受命參與創辦京師華商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等事宜,但馮恕并不以此為榮,反而說出了“未受官刑未招謗,戰兢七十七春秋”,表達了一種士人從商的無奈之感。
《癸未憶舊詩》:“幼逢青眼張淵靜,不薄寒微白侍郎。卓庵策勵忍勤苦,芝田誘掖規鍾王。沖霄有心泥曳尾,抜置云漢使我昂首酌天漿。向非廠齋具神力,安能至今天際容翱翔。嗟予一生知己五人耳,豈意紛紛振翮回仙鄉,只有廠公隱北海,藏身書窟□□光,屈指七十七年事,歡樂苦短徒多感慨悲傷。”10
此詩提及的五人,均為馮恕關系頗為緊密的知己之朋。張淵靜為張曾揚,名臣張之洞同族侄曾孫,官至浙江巡撫,曾捕殺革命志士秋瑾。張淵靜對馮恕頗為青睞。白侍郎不知何許人也,他并不以馮恕出身寒微為嫌,與之交往。卓庵或為顧元昌,清末官員,為著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書法家顧廷龍之父,顧元昌對馮恕時常策勵之。芝田為宋伯魯,清末官員、著名書法家,宋氏在書法上對馮恕有所影響,馮恕早年曾為宋氏做通套信。廠公不能確定其人,但對馮恕亦有幫助。從詩中可略窺知馮恕的交游情況。
《公度自挽詩》對了解馮恕生平有一定的補充作用,明確了他早年出身寒微,參加過科舉考試,但僅取得秀才功名。亦可知馮恕書法很早即為時人所重,他曾鬻書解決生計。
對于馮恕的書法,民國時人的評價并不多見。琉璃廠韻古齋掌柜韓少慈曾記:“馮恕,字公度,書法家,寫顏體字,他寫的字很像劉墉寫的。”11學者莊嚴記:“馮恕,寄居北平,其書專學劉石庵,能榜書,略傷肥俗,頗有收藏。”121935年刊行的《老北京旅行指南》中《文化藝術之部—書畫雕刻》記:“馮恕,字公度,河北人,為當代名書家。筆力蒼老,氣勢雄渾,既張顏軍,復樹歐幟,平市大商店匾額多出其手筆。”13馮恕生于同治年間,早年習書受到館閣體的影響,應臨習過顏、歐、趙諸體,遵循帖學一路,氣格與清人劉墉相類。通過前文提及的《公度自挽詩》,可知馮恕早年書法曾得到一些士人的推崇,但其科舉功名不高,在館閣體盛行的時代,書法和科舉制度緊密相連,“書家出翰林”的傳統頗為世人所認可,社會中亦盛行著“翰林書家才是真正的書家”的說法,因此馮恕書法可能并未得到士人階層的普遍推重,其交游圈也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客觀地講,馮恕的書法基本功扎實,受到京城市民階層的喜愛。馮恕書法最為見長者為榜書,故其所題匾額頗多。他深諳書匾之法,北京傳統的匾額一般喜用正統的顏體或歐體楷書,一是楷書容易辨認,二來飽滿的楷書象征著物阜年豐。而匾額對字體也有嚴格要求,一般為榜書,書寫時要注意三個要點:一是筆畫要粗,顯得飽滿;二是要橫、豎、撇、捺相對寸楷要短而有力;三是字體中心部分比例要大。這樣的字體雄壯、凝重,適宜匾額書寫要求。馮恕書法契合了題匾的需要,加之他常年書寫擘窠大字,將歐、顏、趙三體結合,用筆寬博而內斂,含蓄而生動,整體大氣磅礴,墨色飽滿,蒼勁雄強,取顏楷之間架,輔之以節奏的變化,在陽剛體魄中蘊含著陰柔之美,展現出顏體書法中浩瀚勁健、中正內斂的一面。馮恕楷書看似平和,卻是常年臨池和學養積聚所至,他的楷書雖有千字一面、體態豐腴的不足,但也有其過人之處。馮恕還經常創作一些手卷、冊頁、扇面等作品,字體厚重娟秀,技法嫻熟,頗具韻味。誠然,馮恕的書法囿于帖學,雖然他喜購藏三代商鼎周彝,但對于碑學書法似乎是涉獵不多的,甚至不及清末諸多學者書家視野之寬闊。
民國時期,京城中聚集著一大批守舊官僚,他們對于清朝有著特殊的感情,面對朝代的更迭,表現出一種茫然和無奈,馮恕即屬于此類人物,從其《公度自挽詩》中即可窺見一斑。他還曾輯錄《庚子辛亥忠烈像贊》以憑吊庚子、辛亥中殉難的清室人物。馮恕這種感情也反映在其書法之中,他雖未能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進一步仕進,但對于科舉制度還是頗為眷戀和期許的。馮恕的書法繼承了清朝帖學傳統,代表了清末民初的復古書風,他似乎以書法為寄托,完成其未竟的“翰苑”之夢。
注釋:
1 劉季人《馮公度二三事》,《京華奇人錄》,312頁,北京出版社,1992年。
2 劉季人《馮公度二三事》,《京華奇人錄》,311頁,北京出版社,1992年。
3 北京市西城區文物管理處編《蘊真堂石刻資料集成》,322 頁,文物出版社,2016年。
4 吳夢麟、劉衛東《序》,北京市西城區文物管理處編《蘊真堂石刻資料集成》,5頁,文物出版社,2016年。
5 劉季人《馮公度二三事》,《京華奇人錄》,313頁,北京出版社,1992年。
6 馮肅元編《公度馮恕書法》,184 頁,沈陽出版社,2008年。
7 同6。
8 馮肅元編《公度馮恕書法》,185 頁,沈陽出版社,2008年。9 同8。
10馮肅元編《公度馮恕書法》,186頁,沈陽出版社,2008年。
11陳重遠《韻古齋的興起》,《文物話春秋》,128頁,北京出版社,1996年。
12莊嚴《六十年來書家簡介》,《前生造定故宮緣》,306頁,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13馬芷庠《老北京旅行指南》,352 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