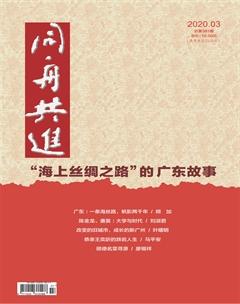嶺海“船”奇:明代廣東的財富鑰匙
張嵚


16世紀初葉,那些乘著大航海時代的東風,漂洋過海來到中國沿海的歐洲人,首先在自己日記里描繪的就是他們看到的“廣東船”。明朝正德年間,當葡萄牙船隊初次造訪東南亞時,就在當地見到了大批來自廣東沿海的中國商船。葡萄牙殖民者、《東方諸國志》的作者皮萊斯以繪聲繪色的筆墨,描述了數千艘帆船在廣州港聚集的盛大景象。嘉靖年間,一度客居廣州的葡萄牙人克魯茲也記錄了廣州河道上的各種船舶,有“無風時以巨槳驅動”的大船,還有鳥嘴型可以裝載很多貨物的單層甲板帆船。單是每天在河邊看“蓬帆蔽日”的景象,就“足令人享受一番”。這些他們滿懷新鮮感記錄下來且曾在歐洲大陸引發火熱風潮的文字,不止還原了當時中國的航運生活,更讓古代廣東制造的一件標志性產品——“廣船”,悄然浮出歷史水面。
中國古代造船業有“四大船型”之說,即蘇船、浙船、福船、廣船。而放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風云變幻史上,廣船不但是老資格的見證,更是一代代國人劈波斬浪,征服萬里海域的先鋒。
海禁下的造船業
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史上,廣東的角色十分特殊:西漢“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徐聞古港,此后的兩千年里,王朝更迭,但廣東的海上貿易地位卻扶搖直上。盛唐開元年間,地理學家賈耽就把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貿易網絡譽為“廣州通海夷道”。這條航線分為“東路”和“西路”,“東路”可達今伊拉克地區,“西路”可直達紅海沿岸的東非地區,連接起亞非的海路航線。
在大唐“安史之亂”后,這條海上貿易航線蓬勃發展,成為中晚唐重要的財富通道。廣州的經濟也突飛猛進,從此“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植根于如此“黃金地帶”的造船業進入了繁榮期。也同樣是唐代起,廣州與泉州成為中國兩大海船建造基地,以“首尖體長”和“吃水深”著稱的廣船脫穎而出,與福建的福船一道成為中國海上貿易的標志。
無論是在唐宋年間的中國典籍還是阿拉伯旅行家的筆記里,該時代的中國船都是亞非海洋上神奇的存在:船體大,續航能力強,能把中國的寶貨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四方。由于船體太大,當中國船抵達波斯灣時,甚至無法直接進港,只能換成小船。而廣船更是中國船中的佼佼者,比如出土于印尼的南漢王朝沉船就是那個時代廣船的代表,其先進的船體設計與船上巨額的財富,無不驚艷世界考古界。
也正因為名聲在外,所以,當大航海時代到來,歐洲船隊終于踏上了夢寐以求的東方航線時,他們對于傳說中的“中國船”抱有滿滿的好奇心。明朝正德三年(1508)六月,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發出訓令,命令即將遠航東方的葡萄牙艦隊必須要用各種辦法,弄清楚中國船只的噸位與性能,然后才有了上文皮萊斯筆下對廣船的各種生動描述。
當然,葡萄牙國王的訓令絕非出于純粹的好奇,葡萄牙船隊遠征東方的背后,是勃勃的殖民野心。皮萊斯在對廣船進行了一番描述后,發出了狂妄的判斷:“(葡萄牙)船隊中的一艘船便可以輕易擊潰二十艘中國帆船。”在他看來,廣州港口那上千艘帆船,也不過是一堆“肥肉”。
曾經享譽世界的廣船真是如此脆弱嗎?其實,彼時正是廣東造船業的低谷期。明朝從開國起就關閉了國門,嚴厲的海禁政策給了造船業重重一擊。雖然大明朝曾有“鄭和下西洋”的盛況,也曾擁有技術水準登峰造極的“寶船”,但對于曾經旺盛的民間造船業,朝廷掐得很緊,民間的船舶被嚴格限定尺寸。特別是永樂二年(1404)起,民間船舶一律改成適應內河航運的“平頭船”,以“尖底”為特點,而適合遠洋破浪的廣船幾乎絕跡。
曾締造“鄭和下西洋”輝煌的官營造船業也隨著“下西洋”的終止而日益裹足不前。官營船廠的技術工藝在15世紀下半葉幾乎是一代比一代倒退。明朝弘治年間,當大洋彼岸的達伽馬哥倫布們一撥撥啟航去探索未知領域時,最強的官營船廠龍江船廠受命制造大型海船,結果花費白銀一萬五千兩,卻造出了“不堪駕遠”的殘次品,貽笑大方。
明正德十六年(1521),對葡萄牙殖民者忍無可忍的朝廷決心調集廣東地區的主力船隊去清剿盤踞屯門的葡萄牙艦隊,但此時廣東水師的賬目上有的只是一份慘淡的家當:大型戰船不過20條,剩下的多是臨時征調的民船;就連參戰士兵也大多是從沿海漁村征調的民兵;即便是“大型戰船”,比起葡萄牙艦隊的船舶也是不堪一擊。當時葡萄牙艦隊乘坐的船舶被中國人稱為“蜈蚣船”,即歐洲人常用的槳帆船,這種船只長度40米左右,能裝載大小火器30多門,無論火力還是航速都遠遠優于明軍戰船。
僥幸的是,在接下來的戰斗中,由于葡萄牙艦隊里的華人工匠楊三等人幡然悔悟,冒死來到明軍軍營,帶來了葡萄牙的火器制造技術。臨時換裝新式火器的明軍才憑借著兵力優勢,將葡萄牙艦隊艱難地逐出屯門。
其后,在“嘉靖倭亂”里,同樣獲得西方新式造船技術的倭寇們也迅速升級了自家的船舶,甚至對沿海“正規軍”水師形成了絕對的海上優勢。“倭寇王”汪直在廣東高州(今茂名市)建立造船基地,將傳統的廣船技術與西方造船技術相結合,造出了新式的“巨艦”,其主力戰艦甚至“方一百二十步,客兩千人……可馳馬往來”。憑著一支強大的艦隊,汪直一度縱橫中國東南沿海,甚至在日本薩摩洲松津浦建立領地。
迎來重生
就在這樣一個倭亂深重、走私活動猖獗的年代,萎靡已久的廣船產業卻在悄然復蘇,愈發發達的海上活動成了廣東民間造船業的催化劑,沿海的民間船廠,無論是工藝水平還是規模,都在直線升級。曾在明王朝森嚴限制下淪為“小船”的廣船,終于迎來重生。
當時的廣船往往被稱為“烏艚船”,分為“尖尾船”“橫江船”等多種型號。“廣船原系民船,由于明代東南沿海抗倭的需要,將其中東莞的‘烏艚、新會的‘橫江兩種大船增加戰斗設施,改成為良好的戰船,統稱‘廣船。”廣船的帆形如張開的折扇,與其它船型相比最具特點。為了減緩搖擺,廣船采用了在中線面處深過龍骨的插板,此插板也有抗橫漂的作用。為了操舵的輕捷,廣船的舵葉上有許多菱形的開孔,也稱開孔舵。廣船在尾部有較長的虛梢(假尾)。
廣船多用熱帶硬木,如鐵力木(柚木)制造,堅固耐用,壽命有達60年之久的。不過,《武備志》對廣船的缺點也有客觀評價:“廣船若壞須用鐵力木修理,難于其繼。且其制下窄上寬,狀若兩翼,在里海則穩,在外海則動搖,此廣船之利弊也。”
即使與“高大如城”的福船相比,廣船的體魄與堅固性都占絕對優勢,廣船堅硬的船體,不但能在海面上撞碎對手,更適合配備重型火器。《明史·兵制》對廣船的評價是:“廣東船,鐵栗木為之,視福船尤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球。”對于肆虐中國沿海的倭寇船只,廣船更是天然的克星,很多時候,廣船遇上倭船,甚至連開火都省了——直接撞過去就能把敵船碾碎。
于是,明王朝痛定思痛,開始重建沿海水師,民間船廠出品的廣船也越發得到重視。大量廣東民間船廠制造的廣船被編入明軍水師的戰斗序列里。比如抗倭名將戚繼光麾下就有大量廣船助戰;單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就有180艘廣船受命北上,參加浙江沿海的剿倭戰爭。
由于水師的重建,嘉靖晚期的明王朝改變了以往的海防思路,在廣東沿海組建了五大水寨,配備大小戰船數百艘,形成了一道強大的“海上長城”,堅固且火力強大的廣船成為水師主力。強大起來的明朝水師終于令肆虐數十年的倭亂銷聲匿跡。
更讓人震撼的是,在16世紀晚期的萬歷朝鮮戰爭中,明代將領陳璘率領上萬廣東水師決戰日本艦隊。在露梁海戰中,生猛的廣船成了急先鋒,將500艘規模的日本艦隊切割得支離破碎,450艘日本軍艦葬身露梁海。這一仗,打出了東北亞海洋近400年的和平。
與廣船縱橫海疆相對應的,是海禁政策的松動。在此之前,雖然廣東的對外貿易已經十分火熱,但商船出海依然被嚴厲限制。終于,隆慶元年(1567),史稱“隆慶開關”的國策推行,福建月港放松了對船舶出海的限制,廣州隨之跟進。雖然依然要經歷苛刻的盤查,但當地的商人終于可以駕著中國船正大光明地出海了。在海洋上大顯身手的廣船也有了新的使命:賺全世界的錢。
“帆綽二洋,倏忽數千里”
對于倭亂結束后的廣東來說,“走出去”有多重要?可以先看看當時的廣東蘊藏著多少“寶貨”。
雖說中國古代的東南海上貿易航線常被統稱為“絲綢之路”,但放在此時的廣東,能在國際市場上做“硬通貨”的,并非只有絲綢一種。明朝民間就有“蘇州樣廣州匠”的俗話,意為廣州手工業的技藝冠絕天下。很多在中國看似尋常的產業,當時都有著高額的國際貿易利潤,比如蔗糖業。明朝中后期,由于“黃泥水淋糖法”的推廣,以及甘蔗等作物在廣東的普及,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重要的制糖中心,各種品牌的“廣糖”暢銷大江南北。而在同時代的西方,由于制糖技術落后,白糖是價值不菲的奢侈品。在英國,王室貴族只有在生病時,才能享受一口白糖。
由于制糖業的繁榮,連帶制糖所需的鐵鍋也成了一項重要產業。以佛山鐵鍋為代表的“廣鍋”,長期以過硬的質量馳譽天下,甚至在與北方韃靼部落的“互市”里,被明朝首輔張居正列為“專用貨物”。放在海上貿易航線上,鐵鍋是名貴的產品,一口佛山鐵鍋賣到日本,價格就翻成一兩白銀。
這樣的寶貨如果可以直接走出國門,必然能帶來高額利潤。于是,廣船就成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從明朝中期起,官營造船業日益衰退,就連明朝水師的戰船乃至冊封屬國所用的“封舟”,也都“轉包”給了民間船廠建造。“隆慶開關”后,財源滾滾的海上貿易給造船業帶來了無限商機。許多有眼光的廣東商人往往采取“合股”的方式湊錢打造民用商船。這些商船往往是“千斛以上”的巨型船舶,造價不菲。以萬歷年間學者張燮的估算,同樣訂購自民營船廠,一艘明軍水師主力戰船的造價往往只是民用商船的1/3,還不包括商船的維護費用。
下血本的建造換來的是豐厚的收益。正如明末清初的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所說,當時滿載著鐵器、白糖等貨物的廣船來往于日本琉球、呂宋、南洋等地,“帆綽二洋,倏忽數千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
“大贏”是多少?萬歷年間,單是在西班牙人控制下的菲律賓,每年上百艘中國船只能從西班牙人手中賺走價值100萬比索的財富。以至于到了1598年時,馬尼拉大主教向西班牙政府叫苦:“這些錢都流入了中國人的口袋。”以當代西方學者弗蘭克《白銀資本》里的估算,從明朝中后期至明亡,全世界至少1/4至1/3的白銀流入了中國。
明朝“隆萬中興”的輝煌乃至白銀貨幣在明朝中后期的重要角色,幾乎都來自這場貿易熱潮。而乘風破浪的廣船,亦是這個火熱時代里公認的財富鑰匙和強國標志。雖然17世紀下半葉起,中國再度走上閉關鎖國的老路,但廣船以及與廣船有關的“海上絲綢之路”故事,卻依然是歷史上一抹別樣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