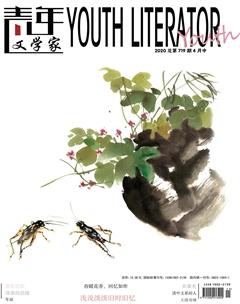車站
作者簡介:馮歌迪(1999-),女,漢族,廣東東莞人,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專業本科。
“這個假期,你跟你媽一起去旅游吧。”
……
裝修得很寬敞的車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擠爆了售票廳。排隊取票的隊伍雖說沒有買票的長,卻仿佛永遠也輪不到自己。四周黑壓壓的腦袋一次又一次抬起,罵罵咧咧之聲不絕于耳。我不曉得他們丹田里哪里來的中氣,居然能驅動人嘴像噴氣式飛機一般一瀉千里不間斷地罵。
離上車還有大半個小時,我們兜兜轉轉總算撿了兩個還算干凈的位子。坐下后,母親一時憤懣難平,還在絮絮叨叨地罵著某位插隊的阿姨,我心底的不耐煩早就膨脹得爆出心窩,狠話不經意便露出了口:“可是你連個取票機都不會用,說你老怎么了?”她突然愣住了,下一句即將說出口的話還沒來得及收回。隨后,她吸了下鼻子,眼里的光渙散了,緩緩地把頭垂得很低很低,整個人佝僂地坐著,愣愣地看著地板。我驚覺自己傷到她了,但怒火仍在心頭燒著,倔強讓我不愿低頭認錯,只得默默將身子背過去不再看她。
車站來往穿梭的人越來越多,行人掠過的風有股塵土的味道。我們兩個坐在人群里,卻仿佛與世隔絕,空氣里一片死寂。
其實,我很討厭她。
母親從來都是要強的人,她永遠像是在跟這個世界較勁一般發狠地對自己,對身邊的人,對與她有關的所有事。父母常常不避我地大吵大鬧到半夜,最后往往發展到鍋碗瓢盆摔了個干凈,父親奪門出走……此后,我的陽光被關進黑匣子,暴雨和陰沉成為生活常態。
我越長大,就越討厭母親,甚至一度認為是她毀了我,毀了我的家。
等到我已經年紀接近成年時,逐漸知道多了些關于母親從前的故事。命運讓她從小背負著沉痛的枷鎖長大,支撐著年幼的她活下去的目標,就是想盡一切辦法逃離這個地獄。于是,她與家人不斷抗爭,并執意嫁了父親遠走他鄉。婚后的母親也沒有過上想象中幸福的生活,婆家依舊重男輕女,但她為了保住我這個女兒做了更多的抗爭……
母親的要強,幾乎是生活逼出來的。
我開始理解她變態一般的執著,和刻骨的剛強。但成長過程的傷痕已經存在,每每痛起來都讓我無法真正放下心去接受她。
車站里黑壓壓的人群依舊在涌動,抬起眼四下都是急匆匆的腳步,或是滄桑麻木的臉。我沉沉地嘆了口氣,早就知道跟母親出來會是這樣尷尬,也不知我們是什么時候變得這樣無話可說,變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即將開往華山的列車GZxxx開始檢票!”
高鐵車站的廣播尖聲響起,強勢撕裂了我們之間的沉默。母親很快站起來,輕松地說:“開始檢票了,我們走吧。”一邊說著一邊手腳麻利地收拾好了東西看著我,我也同時站起來應和著她,一起走向檢票口。
人流一下子就擠滿了小小的出口,大大小小的行李箱和行李袋不僅堆疊得比人還高大,走的還飛快,不仔細看還以為是箱子自己要坐高鐵,旁邊只是碰巧掛了個人。我過了檢票口走出大廳時隊伍正好輪到她。母親一碰到現代化的機器就頭疼,我想她可能又不會了。果不其然,母親手里緊緊捏著淡藍色的車票,眉頭緊鎖地盯著眼前的自動檢票機,將手里的車票使勁塞進去卻怎么都失敗,著急地整張臉都皺起來。我仿佛是冷漠的旁觀者,但不忍和揪心卻混雜一起不停翻攪,雙腳生了根,明明想著應該要去幫助她,但又遲遲無法踏出哪怕是小小一步。在我的印象中,母親一直在處理任何事情上都游刃有余,永遠要求完美永遠優秀。
這尷尬得面紅耳赤、一臉迷茫無錯的人是誰?
這拼盡一切努力想要追上時代卻仍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是誰?
她不是我的母親,卻又是我的母親。
隊伍后面越來越多人抱怨,母親的處境越發尷尬了,她面紅耳赤,額頭上擠滿了密密麻麻的汗珠,神色慌張卻又迷惘地聽著旁人教她用機器的話。她根本聽不懂,卻又裝出聽得懂的樣子不斷附和點頭。最終,在乘務員和四五個熱心乘客的指導下,她終于成功了。霎那間,母親整張臉都亮起來,好似初升的太陽將光灑進了她的雙眼和笑窩,看見我就直直沖了過來,眼里流光四溢。
“其實也不難,高科技我還是搞得懂的。”得意的語調與她的嘴角、眼角一齊上挑。我本應該表現出高興的樣子,咧開嘴角后發現喉嚨被哽塞住了,最后只是生硬地張了張口。
我又想起之前的一件小事。母親的身體每況愈下,最后不得不辭掉了工作。她在家的時間更多了,發呆的時間卻也更多,疏松的生活朝她展現出可怖的模樣。母親開始很有干勁地每天打掃衛生;到后來她的病逐漸加重,打掃得也不那么干凈了,但依舊很賣力。某天晚上,她告訴父親和我她今天又做了好多事,但見我跟父親興趣缺缺,說著說著就喃喃自語,然后很快地收拾碗筷鉆進廚房去了。弄完廚房后她換了副模樣,神采奕奕地出來看電視,拉著我繼續聊她今天干了什么。我插了一句:“整天那么辛苦弄也不干凈,你身體不好,還是歇著吧。”說完我就繼續敲打電腦完成工作。她突然愣住,臉色黯淡了下去,頭垂得低低的,呆呆地坐著,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輩子要強的母親,真的老了。而她卻仍未察覺到自己的凋零,這,恐怕就是她眼里最深的迷茫吧。
誰又能一輩子在青春的車站里等候呢?在我還捏著淡藍色的車票,隔著人群遠遠地向車站外眺望時,母親在我不經意時已經過了檢票口,坐上了不知通向哪里的列車。
“這是到哪兒了?”靠著車窗睡了一會兒的母親突然問到。
“沒到呢,我們還有很多站。”我看了看她,笑著說。
“哦——那還好,我以為這么快就到了。”她露出了心安的笑容,“我剛剛夢見自己在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被列車丟下了,抓了抓頭發還發現全白了!然后立刻嚇醒了。”她有些嗔怪地皺眉,嘟嘟噥噥不知又說了什么,頭一歪,靠著我的肩繼續睡了。
我心里一陣酸楚,吸了吸鼻子,抑住涌上眼眶的熱流。
母親,我們還有很多站,很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