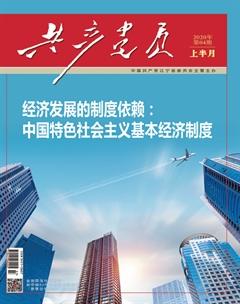班超的和平外交思想
孫寶鏞
班超(32—102年),是東漢時期著名的軍事家、外交家。他在青年時期,不甘于抄寫文書終此一生,毅然投筆從戎,隨竇固出擊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31年時間里收復了西域50多個國家,為西域回歸和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貢獻。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了解他“絕域輕騎催戰云”壯舉的同時,要充分認識他的和平外交思想。
班超未侯漢,誰識烏孫客
東漢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隨軍北征,得到竇固的賞識,被委派出使西域。當時,班超只帶了36個人隨行。這說明他壓根沒想以武力征討的方式溝通西域,而是以和平外交的思想,指導自己永載史冊的外交活動。
班超善于戰爭,卻不輕言戰爭,而是以戰爭促進和平。比如他在西域發動的第一次戰斗——鄯善之戰,率36人夜襲北匈奴使團,目的就是爭取與鄯善國的和平友好。再比如他在西域的最后一戰,調發龜茲、鄯善等8個屬國的部隊共7萬人,完成了對焉耆、危須、尉犁的包圍。此后,班超采取勸說、物質獎勵、該殺不殺,幾乎窮盡了各種手段;還帶了1400名文官和商人隨行,爭取和平的意圖十分明顯。但是三國仍然頑固不化,玩弄花招,班超這才通過武力收服了三國。
班超經營西域31年,促使西域50多個國家派遣使者親附漢朝,阻塞了五六十年的絲綢之路重新開通,西域南道出現了“大漠無兵阻,窮邊有客游”的和平景象。其間,朝廷曾下詔召回班超,疏勒國舉國憂恐,于闐國王和百姓都放聲大哭,不少人還抱住班超的馬腿苦苦挽留。班超便上奏朝廷,繼續留在西域。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班超的和平外交思想,在他的時代,有深厚而堅實的文化基礎。
“協和萬邦”的中華傳統治國理念。《尚書》第一篇《堯典》記述,帝堯向他的接班人提出要求: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大意是,要明了別人的優點美德,從而使得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了,又可以辨別、彰明更多的人的優點美德,使更多的國家和平相處,勁往一處使。這樣,所有的人都會過上和諧安寧的日子。
《尚書》及其某些篇章如《堯典》的真偽,歷來存在爭論,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這個問題的闡釋。在班超所處的時代,這種治國理念是社會的基本認識。班超受到這種思想理念的熏陶,是不可否認的。
諸子百家的思想影響。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孔子“仁”“愛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孟子“仁者愛人”的思想,有子“和為貴”的思想,墨子“兼愛”“非攻”的思想,等等,都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傳播。班超家學淵深,又曾以抄寫書籍為謀生手段,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并不奇怪。他投筆從戎,正是要通過這條路實現他的這些思想。他說:“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傅介子和張騫都是西漢時溝通西域的著名人物。特別是張騫,通過絲綢之路,使中原文明迅速向西傳播。班超以他們為榜樣,也打算通過溝通異域來建立功勛。
中華文化的巨大包融性。“炎黃子孫”說法的廣泛流行,是近現代的事情,但是它的由來卻很久遠。《國語·周語》中說:“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后也。”大意是,那些已經失去原來姓氏的人,并不是沒有人眷愛他們,他們都是黃帝和炎帝的后代。此后,古人關于自己是黃帝或炎帝后代的說法,也多有記載。炎帝和黃帝本來是兩個敵對部落的首領,三次阪泉之戰后,黃帝戰勝了炎帝。但是,后世的中國人,還是把自己看成炎黃的共同后代。這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深入人心不無關系。《論語·顏淵》中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班超所處的時代,《論語》不但是最重要的經典,還是重要的教材。這在《史記》中也有所反映。《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而夏后氏是黃帝的后代。《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說:“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有些民族在他們的歷史中,也宣稱自己是炎黃的后代。《遼史·太祖紀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炎黃子孫”的說法,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巨大包融性。
和平外交的思想存在于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頭腦中。在以后的長期歷史中,中原地區統治者建立的朝代,沒有對外發動大規模以擴充疆土、消滅國家為目的的戰爭。唐、宋、明的對外戰爭,多是防御性、自衛性的。明朝還在修筑和完善長城,就是明證。
而中原某個政權的滅亡,并不表示中華文化的滅亡。中華文明是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那些外來的入侵者,如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雖然有強大的武力,可是他們要在這塊土地上站穩,就必須自愿或者被迫地接受中華民族的文化。正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
班超的和平外交思想,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和治國理念的核心思想。中國文化最本質的特點,在于它的核心是向心的、包融的,它的趨勢是融合。
當然,國家甫一出現,只能是小而分散的部落、城邦。統一治理是有限的。但是,生產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要求國家的規模要與其相適應。而“協和萬邦”“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恰恰適應了這種趨勢。
先秦時期,兼并戰爭不斷。而兼并,不過是統一的另一種表述。周初分封800多諸侯國,到西周末年只剩下100多個,到戰國中期就只剩下7個主要大國了。隨著秦完成統一,“中國”的雛形基本形成。班超用和平友好的方式,讓偌大的西域加入中國的版圖,在中外歷史上沒有第二例。這塊土地,在以后近兩千年的歷史上,基本上都在中國版圖內,直到今天。在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上,還形成了相同的語言和文字。當今,我國14億人的交流基本沒有障礙,也為世界僅有。
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
澳大利亞《悉尼時報》財經主編、華裔學者程超澤近年來出版了《第二次起飛——中國經濟為什么能》,書中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巨國效應”。“巨國”這個詞匯,反映了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現實,“巨國效應”使我們在復雜的國際斗爭中穩坐釣魚臺。
西方則在尋求新的理論和解決之道。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稱,因為有文化文明之間的沖突,世界才不得安寧。而包括中國儒家文明在內的一些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提出了威脅和挑戰。美國已經用這種理論搞得伊斯蘭世界戰火連連、難民如潮,又把矛頭指向了中國。
然而,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我們看到:當亞投行以超預期的速度和規模成長起來,發展中的“窮朋友”們開懷了,他們期待已久的基礎設施有指望了;當肯尼亞蒙內鐵路的女司機坐在駕駛座上時,她驕傲了,她將為祖國運來繁榮;當數千列中歐專列到達歐洲的時候,人們放心了,他們不用去封鎖邊界,滾滾而來的不是難民,而是更快捷更便宜的東方貨物……
“新殖民主義”“債務陷阱”,這些潑向“一帶一路”的污水,必將化成潑水者的眼淚。“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我們黨對人類的巨大貢獻。它們與包括和平外交思想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必將為全人類締造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