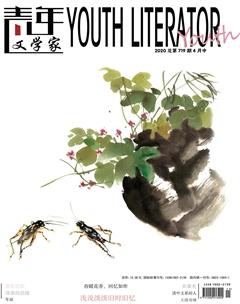他們
杜李昊
她
她本來以為,自己是不屑于張小雨那些新奇玩藝兒的。扭過頭,不理會自己的同桌,心無旁騖地看著窗外或書本,如優雅的天鵝般保持著高傲的姿態,就像昨天一樣。昨天,小雨炫耀自己那五彩的輕盈的新筆盒,說是華僑阿叔帶回的,塑料的。她撇嘴說太花哨,不耐用。小雨尖銳地回應,那是因為你自己的筆盒,不,一坨灰不拉幾的鐵塊,是你爹幫你做的吧?她氣得跺腳,心里卻知道小雨是對的。于是她決定不理小雨了。那天,全班同學都圍著小雨轉,小雨成了明星,獨她一人沒有被“圈粉”。
然而,今天她并沒有。當小雨從袋子里掏出一臺遙控汽車時,她就淪陷了。天哪,多么精致的玩具!她悄悄瞥一眼,忍不住說出了聲,盡管自己是女生。她終于卸下矜持的高冷的面具,趁著小雨上廁所的空當,偷偷地把汽車拿過來把玩。她是如此投入,以至于小雨回來時把她逮個正著。
“玩吧玩吧,你也就玩玩別人的東西了。”小雨很大度地擺擺手。
她一愣,臉霎時漲成柿子紅,二話不說把玩具扔回給同桌,抄起書包就往外跑,跑過瓦楞房,跑過石板路,跑到松口街。時值日暮,大街上人潮洶涌,喧囂的市井聲把黃昏生生地吞了,給人以壓抑的虛無感。她跑累了停下來喘息,而她的臉頰已經被淚洗過一遍了。
擦干眼淚,她這才注意到自己跑到了鎮上的父親的店鋪前。
他
他知道,她遇了難處。女兒很懂事,文文靜靜的,嘛也不說,但他就是曉得——不然,天都黑了,往常早已回家寫作業的她,怎么還留在店鋪里,出神地瞪視著來往的人流呢?他自認為自己是細心的男人,這大概是因為孩子他媽在搬運站,很辛勞地和那些壯漢拼體力,24小時工作制,所以教育孩子的擔子摞在了自己的肩上。
但他自己,又何嘗不是遇了難處呢?
一兩年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糧產大豐收、停薪留職被批準……再憨再木訥的打鐵匠人也看到了商機。他摸著腦袋想,干嘛不搏一手,放膽子去經營一個自己的作坊?反正虧本了可以回原來的五金廠做工。說干就干,他每天打制白鐵糧倉,竟真的富裕起來,索性成為全職小手工業者。
他怎會想到,糧倉的需求很快達到了飽和。他試著改做些日用品,敲敲水桶打打臉盆,但塑料制品的進軍壟斷了這條財路。他生悶氣,他發無名火,他經常喝完酒把罐子摔得粉碎。他變得孤僻,只要顧客說一點產品的壞話,他就擺手拒賣,不管出多少錢。
鋼鐵雖然滯重,但畢竟穩定啊。然而這終究是一個塑料般輕盈易變形的時代了。
他有點憨,但并不傻。他曾經用一包中華煙,掙來了同行李叔的指點:“我告訴你,轉型懂不懂?要轉型,別爛泥扶不上墻在那兒倔著。轉型可以很靈活的嘛,最近,定制類制品不就頂吃香?塑料品攻不到這一塊兒。你問我嘛是定制?就是自個兒要按客人要求做,他讓你做廟燈,你就甭做花籃……”
原來轉型才是出路。但他隨即被另一個問題折磨:
“我慣來沒做過新玩意兒。沒有模具,沒有經驗,咋辦?”
他收回思緒,向女兒走去。
她
當父親蹲下來注視著她的眼眸,她猶豫著要不要說實情。最終,孩子素有的攀比心性占了上風,她嗚嗚咽咽把事情全說了,又哭起來。
他于是伸手,用那只滿是老繭的大手掌給她擦淚。他心想,小乖乖,你一個女孩子家要什么汽車玩具呀?但話到嘴邊又變成:“爹理解你,但張小雨有一個華僑阿叔,你爹我卻不會做汽車啊。”
“鎮上那么多車,你盯準一輛看,把它縮小不就行了?”她囁嚅著,臉上卻欣喜地笑。她知道他會給她摘星星送月亮的,何況一臺小車。
就是那么戲劇。歪打正著,他剎那間找到了那個問題的答案。
他大笑起來,抱起女兒為她歡呼。
他
面對手繪的尺寸圖,他頓了頓,這怎么看也不像呀?但他又有了底氣,鎮上那臺吉普我照著筆畫一整天了,不會錯。裁出鐵片,他發現粘合不上,比例尺全亂了。他只好妥協地笑:“我一個匠人會看圖紙,畫起來卻拙得很。這活兒不是一日之功啊。”
他放下工作,第二天再去看,第三天……有時候他看著看著,會無緣無故皺起眉毛,覺得一切都很荒謬而陌然:“我在哪兒?我在干啥?”這時候他發起無名火,見人就罵。但更多時候,他想起的是女兒那雙嬌滴滴的小眼睛……他畫廢了半箱稿紙,用斷了一袋鉛筆。終于,他可以把吉普車一五一十地搬進紙上了。
接下來是老本行了。他瞇縫著眼,照圖紙裁出鐵皮,日夜趕工。夜晚,他的鋪里燈火通明,敲打聲喧騰,鋪外寒風呼嘯,月明星稀。他很謹慎,先用小模型試手。方法很土,但他愿意這么慢慢來。一比十的、一比五的、終于到一比一的……他敲敲打打三天后,一輛漆著綠漆、內置踏板和方向盤的紅星號吉普車落地啦!
要不是為女兒,他打死也不會做這種沒有模具、從沒做過的玩意兒。不過經驗有了,他以后對付任何定制品都不慌了。他覺得好笑又好氣:“應該說第一個定制訂單的顧主是她呦,我的小心肝。”從那以后,他的生意果然又紅火起來,每天都排有長長一隊,要么取成品,要么求新單,鋪里鋪外洋溢著快活的空氣。
她
她坐上紅星號,在街道上疾馳,乘著風向著旭日。背后有一大批狂熱的追隨者,位列其首的,是張小雨。那天,她玩得很瘋很嗨,蹬起來腿仿佛不知道累。
時光飛逝,孩子的興致也變得快。幾個月后,她騎得厭了,便把車安置在父親的庫房里。但她從此懂了一個理兒:自強不息,對,有本事才能不叫人看扁!當初父親要是沒做成這車,自己該被小雨笑話一輩子吧?
她打心底里感激他,她的父親。
高中住校以后,她漸漸覺得,周圍那幫同學,面子上是同齡人,里子內是三歲孩子,長不大。他們仗著自己年紀輕,肆無忌憚無憂無慮地活著,絲毫不去理會人生的抱負和擔子。男生都調皮,好一點的滿腦子想著打球踢球,一下課就竄沒影兒;壞一點的拉幫結派,打架斗毆,把校園染得烏煙瘴氣,像黑社會。女同胞也不好,整天像群居動物似的手拉著手上廁所,手拉著手回家,閑下來也不管學業,倒是男女愛戀、八卦新聞這些婆婆媽媽的破事兒嚼得有滋有味……于是她反而用學習來隔離這些喧囂,建立起護城墻。她很用功,她從中等生到尖子行列不到半年,最近已經包攬了兩處年級第一。對那些“自暴自棄者流”,她心底里是蔑視的。
她清醒過來,踉踉蹌蹌地走出校門,看到了他和母親。他們像是已經知道了,都沒說話,似乎害怕驚擾什么。“孩子他媽,你幫女兒拎書包,我和她叨磕幾句。”他先開了口。
“今兒夜色不錯,你說呢?”他突然來了句。
“……”
“我說,別給自己整成這個孬樣子!第一天砸了,不還有第二天嗎?就算高考砸了,也別變成蔫兒了的蘿卜干。人,要有個人樣。”他似乎想營造很鄭重很肅穆的效果,但實在有些失敗。
“像你當初和王叔吵架那樣血氣方剛?”她被逗樂了。
“不不,那不是人樣,那是狗樣。”他說,“人樣兒,是說你甭管眼前的坎兒,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
“父親,我沒想過你這么有智慧。”她說。
“這智慧不是我的,是毛主席的。爹今兒把它告訴你,是想說,這個時代,你也知道的,一天一個樣兒。今兒興的是日用品,可能明兒興的就要定制了。反正金鳥兒多的是,憑有本事一定能抓著,一時的失誤不算事。”他說得唾沫星子飛濺,“就算你沒抓著,別怕,你爹娘都能供你。”
她這下是真的樂了:“爸,你還不知道你和媽的工作都是夕陽產業?”
“什么夕陽產業,我看是日出產業!”他說著,那語調就如十年之后的世紀鐘聲一般莊嚴。
這時候,母親、她和他都大笑起來。
他們
她最后還是上了一本線大學,然后成為一名作家——她也許沒有抓著金鳥兒,卻真的去了“外面的世界”。她在深圳成了家,過著雖不富裕、卻很充實的生活。他則堅守崗位,直到手工匠人沒落的最后一刻。接著,他選擇留在那個鎮里,慢慢老去。
“真不走嗎?”她問他。
“走?東一個西一個都走球了,我這個老木頭還是在這兒呆著吧,和你媽一起。”他說。
“年過完了,那么,就這樣啦?”她收拾好回深圳的行李,望著窗外的夕陽慢慢沉入遠山的懷抱。
“就這樣吧。”他點點頭,揚起山核桃一般已經松弛的臉,“那么多年來,咱父女倆互相攙扶著,你幫我我幫你的,多少坎兒都過去了,對不?生活是很難,但咱可以挺住的。”
她一愣,眼眸溫潤起來。
松口鎮的街燈亮起來了,卻少了喧囂的市井聲。不過,她仍記得若干年前的一個傍晚,自己哭著跑到父親鋪前的彷徨和虛無感。
不知為何,她突然想寫一部小說。寫什么呢?寫她的成長,寫他的守望,寫她的自強,寫他的堅持,寫他們互相幫助,以助對方度過難關的廣闊人生。她不打算使用真名,因為她想寫的,其實是已經遠去和正在遠去的兩代人。
她打開電腦,敲下那個標題——
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