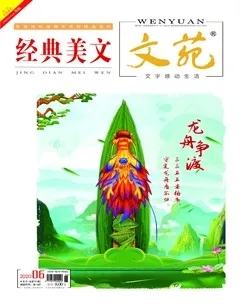陌上桑
苗連貴
小時候愛養(yǎng)蠶,一見桑枝綻出綠芽,回家趕緊用棉花包蠶籽,貼在胸口孵,睡覺也不離身。剛孵出的蠶寶寶又黑又小,螞蟻似的,故又稱“蟻蠶”。螞蟻給人以張牙舞爪的感覺,蠶則是溫良的,只知趴在桑葉上默默地吃。蠶長大變白后,模樣更可愛。
蠶的歷史悠久,軒轅黃帝之妻嫘祖,據(jù)說是養(yǎng)蠶織絲第一人,她“養(yǎng)天蟲以吐經(jīng)綸,始衣裳而福萬民”。自此,蠶桑成為男耕女織社會的美麗風俗。
古代養(yǎng)蠶人很辛苦,楊維楨《采桑詞》云:“吳蠶孕金蛾,吳娘中夜起。明朝南陌頭,采桑鬢不理。”為忙著采桑,女人連簡單的梳妝都顧不上。一到養(yǎng)蠶季,“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窗風雨響。三眠蠶起食葉多,陌頭桑樹空枝柯……”繁忙的蠶事活動,歷歷如在眼前。
養(yǎng)蠶自然離不得桑。除為養(yǎng)蠶、造紙外,桑樹還結有桑葚,三五個一簇,躲在枝葉間,與孩子們捉迷藏。桑葚青而紅的酸,顏色發(fā)紫、發(fā)黑就成熟了,熟透的桑葚甜,勝似棗,我們小時候就親切地把它叫作桑棗,至今想起桑棗的甜美,依然回味無窮。
養(yǎng)蠶于我自然是好玩。我常守在蠶盒旁看它們吃桑葉,發(fā)現(xiàn)蠶吃桑葉很有規(guī)律。它們總是沿著葉子的邊緣一圈一圈地吃,吃相也雅,不爭不搶,忙而不亂。蠶盒里如果有很多蠶,環(huán)境安靜,可以聽見它們嚙咬桑葉的聲音,嘈嘈切切,下小雨似的。蠶的食量大得驚人,它們幾乎一天到晚都不停嘴,桑葉像鋪棉絮似的蓋上厚厚一層,轉眼間便吃得只剩下些筋脈葉梗。我那時候常為桑葉發(fā)愁,附近的桑樹采光了,到遠處去,遠處的沒有了,省下早點錢買,看到蠶寶寶們吃得香,比自己吃飽還高興。
蠶不吃桑葉昂起頭尋找什么時,意味著它要“上山”了,蠶農會扎些草把子,供其爬上去結繭。我的蠶養(yǎng)在紙盒里,一夜之間,盒子的四角、邊沿,白的黃的,蠶花累累。蠶“上山”后,以驚人的勇力“作繭自縛”,完成生命形態(tài)的嬗變。蠶只有極少數(shù)為留蠶種得以羽化,而“魂歸天宇”,絕大部分都不得“終天年”。蠶活一生,吐出大約1.5公里長的絲,這是它生命恒久的價值。
蠶桑是農耕社會的風俗畫,是一首傳承千古的田園詩,歷來在社會經(jīng)濟中占據(jù)重要地位。如今,絲綢業(yè)式微,桑林已不多見,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江南還是桑樹遍野,與稻麥平分天下。雖然如此,不掩其昔日的輝煌,那條曾經(jīng)響著駝鈴、穿越漫漫黃沙的絲綢之路,至今仍是中華文明的象征。
摘自《西安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