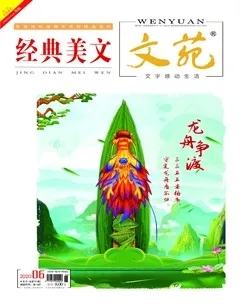站在時間之外的人
潘云貴,90后作家,高校中文專業講師。十四歲開始發表作品,曾獲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大獎、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等獎項。已出版《人生海海,素履之往》 《如果你正年輕,且孤獨》《我們的青春長著風的模樣》等十余部作品。
我認識的大部分作者在年輕的時候都跟詩打過交道,或寫詩、或看詩、或念詩。詩緩解了很多人在青春期無處排解的孤獨、敏感、困惑、焦慮,是一種尤其屬于少年的文體。
在詩的海洋中徜徉,我們會發現古今中外的大詩人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可能就誕生在他青少年時期。他們有特殊年紀里專屬的情緒、心思和對外圍世界的觀察,一雙雙眼睛里仿佛都住著“神”。便如梁文道先生所說:“詩仿佛是一種文學中特別與靈魂、天上某種神秘力量相關的一種文學,真的像希臘人講的要有繆斯女神的祝福才能詩情勃發。”
作為00后,王近松的詩歌有超過同齡人的成熟度,是被繆斯眷顧的孩子。薩特曾在《存在與虛無》中提到“時間明顯地是一種有組織的結構。過去、現在、將來這所謂的時間的三要素不應當被看作是必須湊合在一起的‘材料的集合”,他認為理解和研究時間“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把時間性當一個整體去加以剖析”,即“對時間性整體的直覺”。
王近松在《深夜隨想》一詩當中,是有這種直覺的,這種直覺與他的體驗,對世界與自我關系的感受,緊密相關。詩是經驗的回返和營構,出生在貴州山區的王近松,詩行里滿是自我的在場感,如腳踩大地般厚實。小鎮上的自然風物和祖輩傳說都形成他詩歌的背景,在深夜,他由耳邊的“犬吠聲”開始發散,想到世間虛無的能指與所指,落腳處是“時間”及其帶來故土上人們的命運,“過著同一種生活,過節回家/節后搶票、擠車/又回到城里,模仿著昨夜的動作”。通過對生活細節近似白描的書寫,卻已將人的宿命感呈現出來,如推著巨石往前的西西弗斯。“而我們,都走不出死亡的柵欄”一句尤顯得無力、悲涼,但也透出少年在暗中對這世界思考的光亮,有一份直面現實的清醒。
全詩所表達的主題較為深沉,但也有輕盈的部分,體現著詩人青春的痕跡。如他寫“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這是南方的故事,像梅雨/有人發現,記錄下來/慢慢也會變成北方的故事”。風雨是世間流動的事物,常被少年人捕捉,因為少年人太想要一種自由、無所羈絆的狀態,于是他們的悲喜都藏在風雨中,隨處飄蕩,情感也在詩的跳躍間流動。“南方的故事”隨著人的遷徙、交流,也會成為“北方的故事”,無論在何處的生命,總有一些相似性。
作為年輕的詩人,王近松的詩卻不顯輕松與簡單。他已經懂得在生活和現實中扎根,開一朵名為文學的花。他以個體感悟進入詩的內部,打造自己獨特思考的場域,文字中有想象與超越的力量,但更多的是一種坦誠和樸實,呈現少年人正經歷的世界。正是這樣的姿態,讓他能夠站在時間之外,去探尋、靠近生命的本質,處理著詩與思之間的關系。在人世感懷中,切己及人。
在青春的詩歌森林里漫步,我們每個人都在與真實的自己重逢,或是與內心的“神”相遇。
祝福每一個執筆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