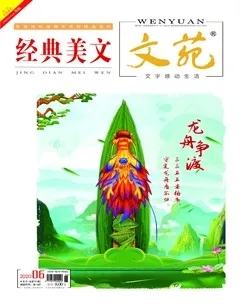月之思
李谷雨
李谷雨,云南大學英語系學生,作品在《文苑》《書屋》《思維與智慧》等多家刊物發表。好讀“三書”:有字之書、大千世界之書、己與他者靈魂之書。心素如簡,包裹對文字和生活的縷縷情思。
幾日前夜晚外出,偶見窄窄的一道彎月,像用眉筆描的蛾眉,泛著淺金的光澤。不由感嘆,人們多愛圓月,其實缺月何嘗不有其美處。
豐子愷先生曾作一幅《人散后,一鉤新月天如水》的水墨漫畫。陳設簡單、筆觸簡潔,唯一桌、兩椅、一簾竹屏風、桌上一套茶具、屏風下方一彎新月而已,卻顯得意境悠遠。輕誦此畫標題,仿佛沐浴唐風宋雨的低吟淺唱,腦中滑過那些詠月的古老句子。
詩人筆下的月不乏多種狀貌多種情。讓我頗感遺憾的是,以“一鉤新月”入詞的名句,無論是納蘭容若的“一鉤新月幾疏星”,還是秦少游的“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字句固然動人,卻都透著思念情人的哀怨和感傷。連樂觀曠達的蘇東坡也感慨“明月明年何處看”,為圓月的稍縱即逝發出嘆息。
只有李商隱在《月》詩中論調不同:“初生欲缺虛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意思是,人們沒有必要為了月亮的不圓滿白白地失落,因為縱使它圓滿了,也未必就是對你有情。這兩句哲理詩既突破了一貫以情景交融手法寫新月和弦月惹起的愁思,也超越了前人借月抒發的懷鄉、孤獨等常見情感,別有一番深意。
呂本中的《采桑子》也寫得很有意思:“恨君卻似江樓月,暫滿還虧。暫滿還虧。待得團圓是幾時。”分明是同一輪月,卻在詞人眼中生發出兩種截然相反的意義,又契合月相無處不在以及滿月稍縱即逝的特征,讓人不由驚嘆“何處想來”。細想又覺得那其實是自然不過的流露,月被觀月人涂抹上濃厚的“我之色彩”,對月的考量也像對心上人的思念那樣心思縝密。在《幽夢影》里,張潮將少年、中年與老年三個人生階段的讀書分別比作“隙中窺月”“庭中望月”“臺上玩月”,又補充說“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顯然改變的不是“月”,而是觀者。由此看來,重要的不是月本身,而是諦聽月語的那顆心啊!
月夜,不惟在古人那里是個容易觸動心靈的情境。張愛玲少年時在對好友傾訴“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的深情厚誼時,為自己設的前提是“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個寫小說的人”;郁達夫和初戀四目相對的情形,同樣是“她只微笑著看看我看看月亮”;席慕容也在《有月亮的晚上》中寫到,她常將白晝的事遺忘,而“月亮下的事情卻總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在有月光照耀的夜晚,我常去住處附近的湖邊散步。月影和云影交疊著倒映水中,仿佛沉淀著來自遠古的深邃寂靜的夢。大多數時候,底層的天空先是呈現一種介于香檳和淺橙之間的顏色,往上則是淡淡的藍灰。隨著時間流逝,它們緩緩隱去,由墨色取代。這時天幕下的近樹和遠山,由于月光不似日光明亮,看得不真切,只能捕捉大致的輪廓。但在這樣的夜晚,靈魂在月光和月影里淘洗,收獲了白日里沒有的超然和平靜,眼睛看不真切,心卻可以看得很遠。
人在世事里經歷一次次浮沉,看過圓月缺月數不清的輪回,終會在心中修得一輪明月。人生不可能時時處處“花枝春滿,天心月圓”,但只要心中的月完好無缺,豈會不是“明月耀天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