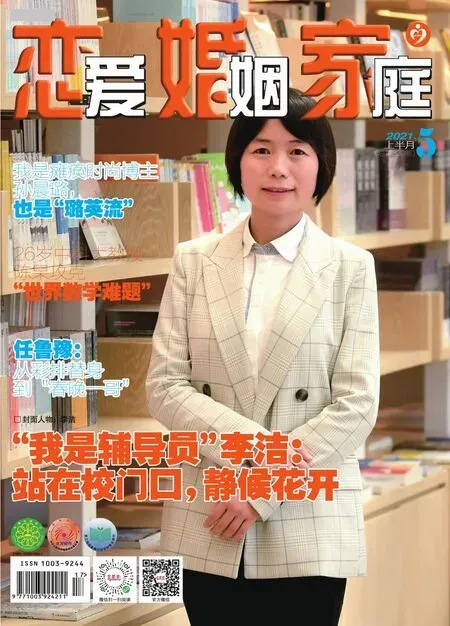退役『空軍大校』謝彬蓉的『空中課堂』
●文/三月河

大涼山上的『鏗鏘玫瑰』。

本文主人公
她在內蒙古偏遠地區服役20年,2013年自主擇業回到重慶,過著安定的生活;然而在2014年,她卻離開舒適溫暖的家,前往四川省涼山州的教學點做一名支教志愿者。
她是誰?她就是先后榮獲“最美退役軍人”“中國好人”“全國三八紅旗手”“第七屆全國道德模范”等榮譽稱號的謝彬蓉。2020年2 月12日,被新冠疫情阻隔在重慶家中的退役“空軍大校”謝彬蓉,惦記著千余里外的學生們,她用一臺電腦和兩部手機架設起一座“空中課堂”,為四川大涼山的26 個彝族孩子“空運”去“知識的甘露”。
留下來! 支教大涼山!
謝彬蓉1971年10 月出生于重慶市忠縣的一個小村子,父親是一名抗美援朝老兵,母親是一名鄉村小學教師。謝彬蓉從小有兩個夢想:像父親那樣成為一名保家衛國的軍人;像母親那樣成為一名教書育人的教師。
1993年7 月,謝彬蓉以優異成績從四川師范學院畢業,并獲得教育學學士學位。是投筆從戎當一名軍人,還是教書育人做一名教師?謝彬蓉彼時陷入兩難。這時,恰好空軍某部基地來學校特招,憑借過硬的計算機技術,謝彬蓉被特招到內蒙古額濟納旗空軍基地。
內蒙古自然條件十分惡劣,但不管條件如何艱苦,訓練科目如何繁苛,謝彬蓉堅持咬緊牙關刻苦訓練,最終以優異成績通過各項考核。在隨后的軍旅生涯中,謝彬蓉潛心鉆研專業知識,取得多項軍中技術成果,多次受到嘉獎。從軍戍邊摸爬滾打20載,謝彬蓉通過自己努力和部隊培養,最終成為一名技術七級、大校軍銜的高級工程師。
2013年,謝彬蓉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她放棄地方軍轉辦安置的機關干部工作,自主擇業當了一名支教志愿者,圓她小時候的教師夢。2014年初,謝彬蓉從四川省涼山州美姑團縣委網站上,看到“苦蕎花開支教團”的社會公益信息,了解到大涼山彝族地區長期缺乏能吃苦、有愛心、負責任的支教志愿者,她決定去四川大涼山彝族地區支教。
“到艱苦邊遠的彝家山寨支教,是我退役后報效國家、回報人民的最好方式!”謝彬蓉對丈夫、女兒以及父母這樣說道。家人都非常支持和理解她,表示愿意做她堅強的后盾。2014年2 月22日,謝彬蓉離開重慶的親人,只身“飛”往海拔3000 多米的大涼山彝族地區,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她的大涼山支教之路。
盡管心里早有準備,但當謝彬蓉雙腳踏上大涼山后,當地的貧苦和環境的惡劣還是讓她大吃一驚。謝彬蓉所支教的古拖村小學是很破舊的土坯房,共有兩間,一間是教室,一間是老師的宿舍、辦公室兼廚房。山村里經常停電,一停就是數天,晚間要用蠟燭照明。學校沒有水,生活用水需要謝彬蓉和學生們到山下的小溪里,用塑料壺一壺一壺地往回背。為了節約用水,謝彬蓉半個月洗一次衣服,一個月洗一次頭發,從未真正意義上洗過澡。
學校環境衛生極差,各種病菌滋生傳播,學生們經常感冒,拉肚子。謝彬蓉決定整治學校環境衛生,自掏腰包買來消毒粉、消毒液進行噴灑。數周后,學校衛生狀況徹底改觀,謝彬蓉又出資幫助學校修繕了教室,購置了一批教學器材。
2015年8 月,謝彬蓉結束了美姑縣古拖村小學的支教服務,來到更加偏遠的扎甘洛村支教。扎甘洛村小學當時只有一個六年級的班,共有10 個孩子。由于長期缺乏老師,孩子們只是斷斷續續上過幾天課,10 個孩子當中竟沒有一個能講出一句完整的普通話,有的孩子甚至連兩位數加減法和乘法口訣都不會,他們的考試平均成績只有十幾分。
那一刻,謝彬蓉感到自己肩上壓力巨大,同時胸膛里又升騰起一份責任:“留下來!至少要把他們的平均分提高一倍,一定要把他們教到小學畢業,一定要從一年級開始教他們的弟弟妹妹,讓他們將來可以用知識改變命運,用知識反哺家鄉、建設家鄉!”
就這樣,一年后,六年級的10 名小學生在小升初考試中,平均成績從十幾分提高到了30 多分,有7 名小學生升入到鄉初中繼續學習。
謝阿莫! 謝謝您!
2016年9 月,謝彬蓉送走六年級10 名畢業生后,又迎來了26 名一年級新生。令謝彬蓉頭疼的是,這些新來的彝家娃兒從小自由隨性慣了,沒有一點學校的規矩意識,想來學校就來學校,不來也不和老師請假,甚至正上著課呢,一個轉身的工夫,座位上就沒人影兒了——不是跟小伙伴到小溪邊玩石頭去了,就是到山上樹林里掏鳥窩去了。
有一個叫阿果的孩子,生性調皮貪玩,經常在謝彬蓉寫板書時偷偷溜出課堂。有一天,外面下大雨,阿果又跑了出去。謝彬蓉發現后,冒著大雨出去找,等找到阿果時,阿果渾身濕透、滿身泥污,還險些被暴漲的溪水沖走。謝彬蓉語重心長地對阿果進行了課堂紀律和生命安全教育,阿果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自那以后再也沒有逃過課。
怎樣才能讓孩子們懂規矩、守紀律呢?謝彬蓉想到了城里的大學生軍訓,她決定對26 名彝族孩子進行一星期的“軍訓”——她把提前準備的洗漱用品發給他們,教他們洗臉刷牙洗頭,訓練他們站“軍姿”,然后在鏡子前看自己的新模樣。除此之外,她還教孩子們見面鞠躬問好、臨行揮手道別,組織孩子們走隊列、練廣播體操……慢慢地,孩子們懂規矩有禮貌了,再沒有人逃課。
為了讓語文課堂更生動、更有趣,謝彬蓉把課文改編成情景劇,讓孩子們在表演中學習語文知識。為了調動孩子們學習數學的興趣,謝彬蓉在講10 以內數字加減法時,創設了“小猴子掰玉米”的故事……
孩子們逃課、不愛學習的問題終于解決了,可家長們拖孩子學習后腿的問題又接踵而至。經常有家長來到學校,把正在上課的孩子帶回家,讓他們去喂豬、放羊或者干農活。那個阿果的父母竟然不讓阿果來學校讀書了。
當晚,謝彬蓉帶著一個“翻譯”,去阿果家里做他父母的思想工作。謝彬蓉對阿果的父母說:“阿果年齡這么小,人又聰明,如果不讀書,真的太可惜了!他是家中老大,只有好好讀書,以后有出息了,他才能幫助弟弟妹妹,一個幫一個,家里的孩子才有可能走出大山,日子才會好起來……”阿果父母深受感動,于是又讓阿果來學校讀書了。
那段日子,謝彬蓉常利用晚上時間一家一家地家訪,給孩子們的父母講學習的重要性,講“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有一次她走夜路還摔進深溝里跌傷了小腿。漸漸地,村民們的思想意識有了很大提高,不再拖孩子學習的后腿了。
謝彬蓉不僅在教學上費盡心思,對孩子們的生活更是關懷備至。看到孩子們每天帶鋁飯盒中午吃涼飯,她就自掏腰包從山下商店為26 個孩子買了26 個保溫飯盒。孩子們吃著熱飯,感激地說:“謝阿莫(阿莫,彝語:媽媽),謝謝您!”
有一次,一名女生不小心扭傷了腳踝,謝彬蓉拿出紅花油給孩子涂抹上,放學后又背著這名女生回家。到了女生家中,女生的父母還沒有回來,謝彬蓉就幫著女生做好飯。謝彬蓉準備離開時,背后傳來女生的聲音:“謝阿莫,謝謝您!”看著孩子依戀的目光,謝彬蓉的眼淚情自禁地流下來——這是一種被需要、被信任的淚水,也是一種幸福的淚水。
孩子們對謝彬蓉越來越依賴,每年放寒暑假時,都依依不舍地看著謝彬蓉:“謝阿莫,您下學期還來嗎?”假期里孩子們更是接二連三給她打電話問:“謝阿莫,什么時候開學?您還來不來?”謝彬蓉堅定地回答:“來!大涼山是我的第三故鄉,你們都是我的孩子,我怎能不來?”
疫情不怕! 駕起“空中課堂”!
2020年1 月,學校放寒假,謝彬蓉從扎甘洛村回到重慶渝北區的家。1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突發,謝彬蓉最牽掛的還是遠在大涼山的孩子們,她雖然身在重慶,心卻早已飛到了千里之外的扎甘洛村。
開始,謝彬蓉想著孩子們聽不聽話,有沒有待在家中不出門,有沒有學會正確的洗手方法,后來,她又開始惦記孩子們待在家中有沒有好好學習,寒假作業有沒有完成,課程會不會被落下。她多么希望這場疫情快點過去,她好早一點回到孩子們身邊。
然而,疫情當時還沒有結束的跡象。謝彬蓉意識到,如期開學是不可能了,那怎樣讓孩子們在家中也能上課學習呢?謝彬蓉忽然想到了網絡,她決定為扎甘洛村的26 個孩子搭建“空中課堂”。
為了尋找到合適的網絡學習資源,謝彬蓉在網上摸索了很久才最終鎖定了幾個優質的在線教育平臺。2020年2 月12日,謝彬蓉的“空中課堂”正式開課了。然而,第一堂網課上過后,謝彬蓉感到課堂效果并不理想。因為在線教育平臺上的老師講課節奏太快,彝族孩子們聽網課比較困難。
“孩子們聽不懂網課,那我就先替他們聽課,然后再教他們。”謝彬蓉決定自己“先當學生,再當老師”,她一邊觀看視頻學習,一邊結合課本做筆記,備好一堂課,至少花費兩天時間,寫滿六七張紙的筆記。
備課過程中,為了能讓孩子們聽到標準普通話朗讀的課文,謝彬蓉特意準備了兩部手機,一部播放音頻,一部錄音保存,然后轉化生成文件后,再發給孩子們聽學。
“即便不能確保百分之百讓孩子們理解課文的意思,但至少可以讓孩子們提前熟悉課文,為以后開學上課做準備。”謝彬蓉說。
每堂課上和課后,謝彬蓉都通過語音與孩子們進行互動,她將課堂的內容重點講給孩子們,再將學習資料分發給孩子們。
“阿牛,你看看你的作文,老師已經把錯別字給你標出來了,你把這些錯別字再抄寫一遍,不懂的再來問我。”“阿布,你這次作業完成得非常不錯,一定要堅持。”“阿西,你要記住哦,‘埋’這個字是多音字……”
除了在“空中課堂”給孩子們講課,謝彬蓉還會給孩子們普及防疫相關知識,告訴孩子們防疫注意事項:在疫情期間守護好自己和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玩耍,提醒家人做好防疫措施等。
從2020年2 月12日至現在,這個專屬于謝彬蓉和大涼山26 個彝族孩子的“空中課堂”一天也沒有中斷過。謝彬蓉每天守著她與26 個彝族孩子們的“空中課堂”,將知識和希望傳給大涼山渴求知識甘露的彝族孩子們。
如今,謝彬蓉已在大涼山支教6年,為彝族山區的孩子們送去了知識和力量,被彝族鄉親們稱為大涼山上的“鏗鏘玫瑰”。謝彬蓉也因此先后榮獲“最美退役軍人”“中國好人”“全國三八紅旗手”“第七屆全國道德模范”等榮譽稱號。謝彬蓉滿懷激情地說:“只要我身體允許,我就不會離開大涼山。大涼山的孩子們離不開我,我也離不開大涼山的孩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