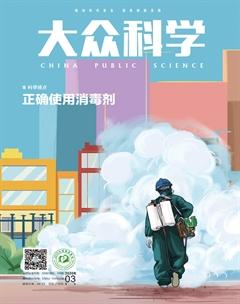“毒庫”蝙蝠為何還好好的活著?
敖顯奎

新冠病毒爆發期間,蝙蝠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一個五十多歲的女性曾一臉嚴肅地跟我說:蝙蝠就是耗子,耗子吃鹽巴吃多了就變成蝙蝠了。說話的時候她信誓旦旦。當然,從科學的角度而言,老鼠吃鹽變蝙蝠是不可能的,而蝙蝠自古就給人一種神秘感。此次疫情,人們的聚焦點放到了它身上的病毒,說是一個活體“毒庫”完全不為過。它們帶著那么多病毒,卻又依舊安然的活著是怎么做到的呢?
“很像”老鼠,不是鳥類
短毛、尖嘴、細牙、小眼睛、一對能豎立的耳朵,這些外形蝙蝠與老鼠都有,并且個體大小相似,都喜歡夜間出沒,都會發出“吱吱”聲。這些共同點容易讓人將蝙蝠與老鼠聯系在一起。不過,對二者稍作觀察,也容易發現它們的不同之處:蝙蝠有翅膀會飛,老鼠不能;老鼠有大長尾巴,蝙蝠尾巴極短;蝙蝠主食昆蟲,老鼠則是雜食性動物。
雖然會飛,但蝙蝠也不是鳥類,而是獸類。確切地說,它是哺乳動物中唯一能夠真正飛翔地獸類。提到獸類,更多人想到的是老虎、獅子,它們四肢發達。蝙蝠雖不善奔跑,但它們同樣有四肢,不過它的前肢變化了,指骨特別長,后肢及尾間生有一層薄薄的翼膜,這就是人們說的“蝙蝠翅膀”。然而,蝙蝠的翅膀與鳥類的翅膀在構造上也是不同的,它不是鳥類——蝙蝠是胎生的,鳥類是卵生的。說出來可能讓人大跌眼鏡,研究人員在將蝙蝠的基因序列與許多動物對比之后,發現與蝙蝠最近親的竟然是馬。
“毒庫”免疫的各種猜測
蝙蝠棲息的山洞,洞頂每平方米可以聚集多達1800只成年蝙蝠和超過5000只的幼年蝙蝠。而在洞底也可以堆積一層厚厚的代謝物和蝙蝠尸體。陰暗、悶熱、潮濕,如此環境,于病毒而言堪稱完美。蝙蝠還真“不負眾望”,身上攜帶著多種讓人聞風喪膽的致死病毒,其中包括:狂犬病病毒、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重癥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也被稱為“新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等等。而此次新冠病毒,也很可能就來自于蝙蝠身上。
讓人不解的是,這些病毒的“致死性”卻只對其他物種管用,蝙蝠自己活得好好的。這是為什么呢?目前有如下幾種猜測:
猜測一 高體溫抑制病毒活性,蝙蝠在飛行時其代謝加強,消耗的能量可達其他同等體型哺乳動物的3倍,其體溫也相應的升高,最高可達48.5攝氏度。這樣的高的體溫可以抑制、甚至殺死病毒。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蝙蝠活動的時間可能僅占其生命的十五分之一至二十分之一,其余的時間都在睡眠。他們在睡眠的時候體溫并沒有那么高,體溫并不是他們對抗病毒的唯一方法。
猜測二 “聰明”的免疫系統。人類在對抗病毒啟動防疫機制的時候會出現一種叫“炎癥因子風暴”的問題——免疫系統在對抗病毒或者藥物時出現的過度反映,無分敵我,導致自身的機體受損。然而,蝙蝠卻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它們體內關于這一反應的基因出現了突變,阻止了炎癥因子風暴。更讓人驚嘆的是,人體只有在發現病毒入侵時才能形成對抗病毒的干擾素,而這種干擾素在蝙蝠體內是長期存在的。也就是說,蝙蝠的身體一直處在一個免疫系統激活狀態。
不可殺,不能碰
蝙蝠類動物全世界共有900多種,分布于世界各地,數量非常強大。或許有人曾想過將蝙蝠消滅,以除后患,但這樣是不可取的。榴蓮、龍舌蘭、猴面包樹這些舉足輕重的植物都需要蝙蝠來授粉。很多蝙蝠還擅長捕食害蟲。

同時,想要消滅蝙蝠也是不可能的。蝙蝠在地球上已經存在了5000萬年,除了南北極之外都有他們的身影,單輪個體數量而言,它們甚至超越了老鼠。我們沒有消滅老鼠,自然也沒能力消滅蝙蝠。
所以,面對蝙蝠,人類最應該做的是遠離他們,當然,這其中就包括了禁食野味,因為我們無法控制的那些野生動物,很可能成為蝙蝠身上的病毒的中間宿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