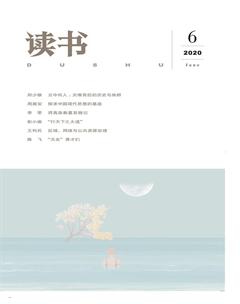中日交流可以從什么地方寫起
張詩洋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中日交流始自漢朝,積厚流光,涉及文學、思想、宗教、民俗、律法、藝術、科技、典籍等方方面面。其中,學人交往與書籍流播無疑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竅要,不僅涉及時段長,涵蓋面寬,并且對兩國文化均產生過深遠影響。百年來,留日學者代不乏人,相關的個體及群體研究也很豐富。而政權易手、兩國交戰(zhàn)中痛失典籍的經歷,則一直是國人心底不愿觸碰的瘡疤。吳真的《勘破狐貍窗》從書人書事入手,不但展現(xiàn)出女性學者的敏銳、細膩和靈動,而且在審視民國期間的學人往事和侵華期間的中日書籍交流時,保持著學者尊重史料的客觀態(tài)度,對于中日密切的現(xiàn)實聯(lián)系和歷史恩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探索和書寫。
吳真的學人散文總能找到好的角度,牢牢抓住讀者眼球。從《一份申請失敗的日本民俗調查計劃》《仁井田陞遭遇的學科鄙視鏈》《一九四0年,見鄭振鐸一面有多難?》這些輕松幽默的文題中,已經不難看出,作者有意省去艱深莫測的學術筆法。但每個“也許”“如果”的大膽假設,又何嘗不是建立在嚴謹?shù)哪框灆n案、考索文獻的基礎上呢?
造訪福井縣的藤野先生紀念館時,作者聽到日本友人提及魯迅先生的另一位老師敷波重次郎在魯迅筆下“消失”的遺憾,于是,抱著對于“歷史書寫中的失蹤者”的敏感,查閱了金澤福井等地的地方檔案,隨之牽連出一系列魯迅先生留學仙臺期間的往事。在《藤野先生》文中,魯迅將所有的敬意都給了藤野這位“善良的失意者”,卻有意省去了“男神”級別的另一任課老師敷波的存在。不過,被忽略并非因其渺小,反而是因其強大。魯迅懷著一份“弱者的共感”,遠遠地懷念藤野那份樸拙的“師者本心”,有選擇性地忽略了敷波教授。作者返回歷史現(xiàn)場,體察到魯迅求學時和成名后心態(tài)的變化,還原了“被魯迅記憶抹去的敷波先生”,也發(fā)現(xiàn)了一種文人筆下作為藤野先生對立面的“無形”形象的符號意義。
類似的發(fā)現(xiàn),還見于書寫留日學生鐘敬文的求學生涯,以及晚清旅日官員的博物館游覽經歷等文章中。中日文化交流的龐大話題,被分解為多份人事個案,加以體貼入微的觀察、模擬、再現(xiàn),讓大時代里的各色人物、場景和細節(jié)成為敘事的主角。這既是作者“有邊界”地解決問題的學術習慣使然,也是其長于還原事件始末、把握人物內心的反映。
書中一些體悟與收獲,來自作者考據文獻之外的田野調查經驗。如《一份申請失敗的日本民俗調查計劃》,聚焦于鐘敬文一生從未向人提及的向日本外務省申請項目資助的一份申請書,于鐘氏本人回憶錄與民俗學史的研究之外,補充了許多東渡時期的治學細節(jié)。透過鐘敬文夫婦與他們的留日朋友,也看到中日民間交往“蜜月期”在匯率紅利刺激之下的熙熙攘攘。文中所附“鐘敬文留學日本行略”是學術規(guī)范體例的行實錄,而后附上的“尋訪鐘敬文的東京住所”札記,則又將讀者拉回到散文小品的語境中,敘寫尋跡途中的因緣巧合,兼具學理與意趣。
此書構思的精巧之處還在于,鄭振鐸的見或不見、魯迅的寫或不寫,都能成為走近歷史人物的關捩點。書名采用日本神道教“狐貍窗”手訣,用意亦在于此,透過發(fā)掘新史料,營造新角度,見到原來被某些成見遮蔽而“未見”“未寫”之物。
《朱自清備課用書的東流經歷》一文中,作者并不糾結于朱自清手批的《吳歌甲集》是如何漂洋過海出現(xiàn)在東大教授仁井田陞的書架上(或許也無跡可尋),也不強求俞平伯為朱自清暗自墊付買書差價的文獻依據,而將關注點放在仁井田陞是如何利用這部書,及其所代表的東京學派重視實學文獻的學術潮流上。從對《吳歌甲集》封底所貼價簽的考索,擴大到在整個仁井田文庫找尋同樣的蛛絲馬跡,作者宛如偵探查案般細密追查。文章至此,證據鏈、敘事點已頗為完整,沒想到下文又接連探討了一九四三年日偽時期的北平舊書業(yè)情況,還拈出一段俞平伯與朱自清知己間的默契往事。筆者觀之,對此間情愫心馳神往,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精彩寫作浮一大白。
記鄭振鐸先生的兩篇文章,聚焦鄭氏留守上海“孤島”期間搶救古籍善本的貢獻,最見學術寫作中的春秋筆法。《一九四O年,見鄭振鐸一面有多難?》講述一位來自日本的學術“追星族”與他仰望的偶像鄭振鐸擦肩而過的遺憾。當然,如果以后見之明的全知視角觀之,鄭振鐸的避而不見,冥冥之中為搶購“暖紅室”和“嘉業(yè)堂”藏書爭取了時間,也是一種斗爭策略。鄭振鐸當年曾在上海“主演”過一段類似于京劇“三岔口”的奪書之事,若不是作者借助日本學者的日記,其中的乾坤騰挪,恐怕連鄭氏本人都不知道。《鄭振鐸與中日文獻爭奪戰(zhàn)》一文,將戰(zhàn)時未曾謀面的鄭振鐸與長澤規(guī)矩也二人的“隔空打斗”,寫得驚心動魄,刀光劍影。鄭氏留守上海孤島,保守古籍視同性命,經與多方斡旋追索,終使三萬四千九百七十冊古籍歷經劫難全部回歸故土。此事的意義絕不僅限于為中國留住珍貴的文獻,更在于索還劫物關涉國運興衰和民族精神的凝聚。此外,文章發(fā)掘了以鄭振鐸為代表的文獻保存同志會此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如何評價爭奪戰(zhàn)的當事人,尤其是原來躲在幕后的日本學者,怎樣書寫不只是國家層面的,還有學者個體層面的中日文獻爭奪戰(zhàn),均值得深味之。
年鑒學派史學家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將史料分成“有意”和“無意”兩大類,“有意史料”指的是歷史著述、回憶錄和公開的報道等,“無意史料”包括檔案、私人信件等。單靠有意文獻,可能陷入原作者“有意”以自己的文字左右時人和后人視聽的危險。捕捉時代的真實質感,還要依靠陳年檔案、私人日記、書信、報告等大量當時無意間留下的證據。作者發(fā)現(xiàn)了被鄭振鐸搶救的古籍在戰(zhàn)后的日本所經歷的磨難,主要依據的便是日本防衛(wèi)省、國會圖書館等日方機構保存的檔案資料,以及鄭振鐸搶救珍稀文獻的書信日記,并根據這些“有意史料”和“無意文獻”的互補對讀,以堅實的史料基礎做支撐,逼近歷史的真相。
以鄭振鐸、長澤規(guī)矩也、仁井田陞為中心,可以串聯(lián)起中日兩國多位書店老板與學者的過從往事。不論是來薰閣主人陳濟川、文奎堂的趙殿成,還是文求堂的田中慶太郎,本書捕捉到他們的共同特點——在中日學者的成長中起到了一定的培養(yǎng)作用。書中提到四十年代的日本學者“在舊書店讀懂中國”的說法,乍一看有些夸張,但細味之下,的確是愛書者和研究者的一種有效視角。侵華戰(zhàn)爭時期,滿鐵調查部為了解鄉(xiāng)土中國,展開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作為華北農村慣行調查員的內田智雄,通過北平舊書店的河北籍伙計,得到不少地方風俗資料。對于當時只是從古典文學中接觸中國的日本學人來說,中國舊書店也是他們的“狐貍窗”。
書人書事中被仰望或被遺忘的細節(jié),正可以加深對中日文化交流的認識。說到底,所謂的“狐貍窗”是借由“祛魅”的手段,直抵豐富的歷史細節(jié),去鉤沉一個個真實的歷史場景。透過作者的“狐貍窗”,被封存的歷史記憶得以清晰顯現(xiàn),如同一面鏡子;狐貍窗外,攬鏡自照的人們得魚忘筌,在正被遺忘的現(xiàn)實中看清當下。
(《勘破狐貍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與書事》,吳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二0一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