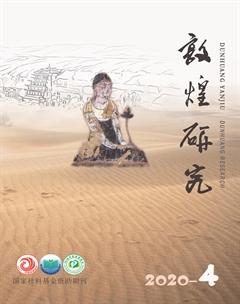隋唐琵琶源流考



內容摘要:琵琶是中國中古時期的重要樂器,但是其形制演變與時空傳播長期存在雜亂混淆。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琵琶發展的關鍵階段,對于考察琵琶發展和傳播的源流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佛教石窟寺中的琵琶圖像為中心,利用考古類型學方法,系統梳理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地區石窟寺中所見琵琶圖像的發展演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一件樂器的變化背后往往蘊含著文化的交融,展現著時代的開放。
關鍵詞:琵琶圖像;敦煌莫高窟;龜茲石窟;隋唐
中圖分類號:K87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0)04-0064-10
Abstract: The pipa was an important musical instrument in medieval China, and also one of the cultural ties that connected various regions along the Silk Road, but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hape and its dissemination through China and the regions connected to the Silk Road has been a source of confusion for a long tim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ere a crucial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ipa in ancient China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is instrument. Focusing on the images of pipa in Buddhist cave temples, and by using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images in the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and in the cave temples of Xinjiang. On the basis of this research,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musical instruments is ultimately reflective of the cultural openness and blending of the time.
Keywords: images of pipa;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Qiuci Grottoes; Gaochang Grottoes;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在中國音樂史上,琵琶類樂器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類彈撥樂器曾在東漢與北朝先后兩次從域外傳入,分別形成了“外來”和“本土”兩大系統,并在隋唐時期趨于定型。敦煌和新疆地區的石窟壁畫跨度時間長、樂舞內容豐富,為我們提供了從長時段角度考察琵琶發展變化的絕好材料。以下我們首先通過考古類型學方法對其形制與分期進行討論。
一 形制與分期
琵琶類樂器分為隋唐時期典型琵琶和其他相關樂器兩部分,前一部分以敦煌莫高窟與新疆地區石窟壁畫圖像為基礎,后一部分則討論阮咸及其他相關的琵琶類樂器。
(一)敦煌莫高窟所見琵琶圖像的型式與分期
1. 型式分析
敦煌壁畫中的琵琶圖像汗牛充棟。此前,鄭汝中先生曾選取了敦煌石窟壁畫中50余幅琵琶圖像進行排列以觀察其演變規律[1]。他選取的圖像具有典型性,不過,通過考古類型學的系統梳理,還可以進一步對其系統化。
根據已出版的報告及圖錄,我們從敦煌莫高窟中選出形制較為清晰的琵琶圖像共65例進行討論。綜合其特點,我們首先以弦的數量為標準,將其分為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
四弦琵琶。對應文獻中的“琵琶”。其下按照項的特點劃分為三型:
A型,直項。其下按照琴身的形狀特征又將其劃分為兩亞型,每一亞型下各為一式:
Aa型,梨形琴身。其琴頸部內弧明顯,向琴頭處逐漸變細,長短不一。以第98、112、156窟中所見圖像為代表(圖1-1)。
Ab型,葫蘆形琴身。琴頸部與Aa型相似,但是琴身形如葫蘆。以第332、423等窟中所見圖像為代表。
B型,曲項。其下按照琴身的形狀特征又將其劃分為兩亞型:
Ba型,梨形琴身。除項部外琴體形狀與Aa型類似。按照有無捍撥將其分為三式:
Ⅰ式,無捍撥。以第272、299、435等窟所見圖像為代表(圖1-2)。
Ⅱ式,有捍撥。以第55、98、112、138、156、201、331、397、398、445等窟所見圖像為代表(圖1-3)。
Ⅲ 式,捍撥消失。以第465窟所見圖像為代表。
Bb型,柳葉形琴身。其琴頸與琴體分界不明顯,琴體較為狹長,形如柳葉(圖1-4)。按照有無捍撥將其分為兩式:
Ⅰ式,無捍撥。以第266、394等窟所見圖像為代表。
Ⅱ式,有捍撥。分別見于第392、398等窟所見圖像為代表。
C型,風首形項。琴頭為風首造型,琴頭向下。僅一例,見于第392窟中。
五弦琵琶。對應文獻中的“五弦”。其下按照項的特點劃分為兩型(圖1-3):
A型,直項。其下按照琴身的形狀特征又將其劃分為三亞型:
Aa型,梨形琴身。除弦外其他特征均與四弦琵琶Aa型相似,皆有捍撥。以第156、201、264、301、331等窟所見圖像為代表(圖1-5)。
Ab型,柳葉形琴身。琴體形狀與四弦琵琶Bb型類似。以第285、322、398等窟所見圖像為代表(圖1-7)。
Ac型,葫蘆形琴身。除弦外其他特征均與四弦琵琶Ab型類似。以第262窟所見圖像為代表(圖1-8)。
B型,曲項。其下按照琴身的形狀特征又將其劃分為兩亞型,每一亞型下各為一式:
Ba型,柳葉形琴身。除項外與Aa型相似。有兩例,皆見于第260窟(圖1-6)。
Bb型,葫蘆形琴身。除項外與Ac型類似。僅一例,見于第220窟。
綜上,我們可大致將莫高窟壁畫所見琵琶圖像分為5大類共10個小類。從中可見,無論是四弦琵琶,還是五弦琵琶,其琴體形狀均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其琴頸亦有“直項”和“曲項”之分。其中的直項四弦琵琶既有寬闊的梨形音箱,也有狹長的柳葉形音箱,甚至是特殊的葫蘆形音箱。其琴身一些細節部位,如捍撥、音孔等在不同時期也有所變化。此外,琴首部分還有“尖頭”和“方頭”之別。此前有學者指出,琵琶琴首的這種“尖”“方”之分始于唐代[2]。從目前所見材料看,這種認識是成立的。
2.分期研究
在型式分析基礎上,我們進行分期研究。下表反映了各種類型的琵琶在不同時期發展變化狀況(表1)。據此,我們可將其分為五期:
第一期為十六國至北魏時期。該時期的圖像相對較少,種類也較單一,以四弦曲項琵琶Ba型為主,也有柳葉形琵琶,但是弦或項的特點不明,故不作討論。我們不妨將這一階段概括為傳入發展期。
第二期為西魏至初唐時期。該時期有兩大特點:一是隨著梨形琵琶的持續發展,五弦圖像的大量出現,呈四弦曲項琵琶和五弦并列的局面;二是從西魏開始出現了柳葉形琵琶和五弦,進入唐代后逐漸消失。其中,在隋代還出現了柳葉形和鳳首形的特殊類型。從這一時期開始,琵琶琴腹上出現捍撥。另外,在隋代出現了四弦琵琶Bb型Ⅰ式和Bb型Ⅱ式短暫共存的局面。這一時期由于政局相對動蕩與對外交流頻繁,琵琶圖像也反映出了豐富多彩的盛況。我們不妨將這一時期概括為融合繁盛期。
第三期為盛唐至中唐時期。該時期的琵琶和五弦,無論直項還是曲項,其形狀大多為梨形,柳葉形較少見,琵琶整體形制走向固定和統。與此同時,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四弦Aa型琵琶,并在敦煌一地石窟寺圖像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我們不妨將這一時期概括為統一定型期。
第四期為晚唐至五代時期。該時期琵琶的類型較之前再度增多,但總體而言,琵琶的種類和數量已經開始衰減。我們不妨將這一階段概括為反復期。
第五期為五代以降至宋元時期。該時期琵琶數量和種類皆大幅衰減,圖像中的琵琶也多是作為法器而非樂器出現。五弦琵琶已經徹底消失,而四弦琵琶也僅有Ba型延續下來,直至發展成今日的形態。我們不妨將這一時期概括為衰落期。
(二)新疆地區石窟壁畫所見琵琶圖像的型式與分期
新疆地區出現琵琶圖像的石窟壁畫,主要分布在龜茲和高昌兩個地區。這兩個地區分別是絲綢之路的南路和中路要沖,其中龜茲地區作為佛教入華的前沿地帶,不僅佛教發展繁榮,而且“管弦伎樂,特善諸國”[3]。目前所見龜茲地區石窟壁畫以克孜爾石窟為主,時間跨度上從4世紀至9世紀延續數百年,其中樂舞圖像大量出現,而琵琶類樂器成為了樂舞圖像中配器的主導;高昌地區石窟壁畫較龜茲地區出現晚,其樂隊設置既有本土色彩,又有鮮明的中原特征。綜合敦煌石窟壁畫琵琶圖像和歷史文獻可見,關于隋唐琵琶諸多端倪皆與龜茲有關。因此,對于這一地區所見的琵琶圖像,應予以關注和考察。
1.型式分析
王子初、霍旭初先生主編《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新疆卷》[4]對新疆地區石窟壁畫中的樂舞圖像進行了集中的收錄。參考其中相關資料和年代,并結合《新疆克孜爾石窟考古報告》第1卷,我們從中選出了22例圖像較為清晰、形制和年代較為明確的琵琶圖像進行梳理。首先,還是以弦的數量為標準將所示琵琶劃分為四弦琵琶和五弦琵琶。
四弦琵琶。按照項的特點劃分為三型:
A型,直項。僅一例,見于庫木吐喇第68窟(圖2-1)。
B型,曲項。其下按照琴身的形狀特征又將其劃分為兩亞型:
Ba型,梨形琴身,琴面闊。以庫木吐喇第13窟、柏孜克里克第16窟等所見為代表(圖2-2)。
Bb型,柳葉形琴身。其琴頸與琴體分界不明顯,琴體較為狹長,形如柳葉。以庫木吐喇第46與58窟、克孜爾尕哈第30窟、克孜爾第60窟等所見為代表(圖2-3)。
五弦琵琶。皆柳葉形琴身、直項。以克孜爾第8、38等窟所見為代表(圖2-4)。
在型式分析基礎上,我們大致可將其分為4個小類,其中四弦琵琶既有直項也有曲項,而曲項居多;五弦成為琵琶類圖像的主導,其整體形狀較穩定,但是琴體長度和比例有所不同。淩廷堪、牛龍菲等學者在對琵琶進行分類時,將四弦曲項琵琶命名為龜茲琵琶。不過,根據龜茲壁畫中的琵琶圖像,這一地區五弦琵琶居大宗,四弦曲項琵琶相對較少,因此這樣的命名是否合理亦待商榷。
2. 分期研究
型式分析基礎上,我們對其進行分期研究。
上表反映了新疆地區石窟壁畫中琵琶的形制變化(表二)。據此,我們將其分為四期:
第一期為4~5世紀,即中原地區三國至十六國時期。四弦琵琶Bb型Ⅰ式、五弦Ⅰ式皆有出現,但數量相對較少。同時,該時期佛教在新疆地區業已興盛,故筆者將其概括為佛教傳播背景下琵琶的傳入發展期。
第二期為6世紀,即中原地區北魏至隋時期。該時期的顯著特點是五弦琵琶占據主導,且相對穩定,我們不妨將其概括為穩定期。值得關注的是,該時期本地四弦曲項琵琶缺失的同時,敦煌地區四弦曲項琵琶恰恰開始興起。
第三期為7~8世紀,即初唐至中唐時期,這一時期五弦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五弦琵琶Ⅱ式;四弦琵琶B型大量出現;同時,在8世紀四弦琵琶A型Ⅰ式首次出現。這一時期五弦的主導地位被撼動,琵琶的具體類型大大增加,這應當與當時西北政局與社會族群的變遷有關,我們不妨將其概括為嬗變期。
第四期為9世紀以后,即中晚唐以降。該時期該地區琵琶的種類大幅衰減,僅有四弦琵琶Ba型Ⅰ式得以延續,出現了與敦煌地區衰落期相似的面貌,我們不妨將其概括為新疆地區琵琶的衰落期。
(三)與琵琶相關的其他彈撥樂器
結合文獻對琵琶圖像材料進行長時段的梳理之后,我們對典型琵琶的基本形態和發展演變有了一定把握,此時再來反觀隋唐時期與琵琶相關的其他多弦彈撥樂器。
1. 阮咸
阮咸,通常是指圓形琴身、細長頸的四弦彈撥樂器。自東漢時傳入,在魏晉時實現本土化,并在南北朝時期流行于士人階層,進而與古琴一道被塑造成為一種高雅符號。又因魏晉時期的竹林高士阮咸善彈此琴,后人即以“阮咸”為其命名[5]。
魏晉南北朝時期,禮樂文化中出現了“雅俗分野”的潮流,在胡漢之爭的時代語境下,為與西域“胡琵琶”相對比,人們將本土化后的阮咸作為華夏傳統樂器,并命名為“秦琵琶”,以表示其文化來源。此種樂器圖像,出現在魏晉十六國及南北朝時期的河西地區與東南地區墓葬壁畫及器物裝飾上[6]。在莫高窟壁畫中,阮咸種類繁復,直項、曲項皆有。其中圓形四弦直項阮咸發展穩定,延續時間較長,是各種圖像和實物所見阮咸的基本形態。曲項阮咸則雜糅了大量四弦曲項琵琶的因素,我們認為此種阮咸并非中原所制,當體現出西域風格。其他各種異型,如花瓣形阮咸,是融合了多種文化因素的產物,亦有可能是畫工的想象與創造。
新疆石窟壁畫中的阮咸,大體上有直項與曲項兩種。在直項阮咸中,除了中原阮咸,新疆當地也有多種梨形琴身的彈撥樂器,例如今天所見的熱瓦普就與新疆石窟壁畫上的具有細長型指板的阮咸十分類似,而今天新疆地區的彈布爾則與新疆石窟壁畫上具有寬矩形指板的阮咸類似。因此,至少在隋唐時期,類似于阮咸這種圓形長頸的彈撥樂器的來源有兩個方向,在敦煌與新疆地區的發展實際上體現了一種胡漢系統的融合。
2. 三弦彈撥樂器
在克孜爾第77窟后室正壁繪有一幅琵琶圖像,《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新疆卷》將其釋為五弦,實際可見三弦,其年代約為4世紀。此圖像可能是表面顏料剝落所致弦軫不明。但是無獨有偶,這類三弦彈撥樂器在新疆和田達瑪溝佛寺遺址中曾經出土(圖4-1)。這件樂器在形制上與敦煌及新疆地區石窟寺壁畫所見的柳葉形琵琶十分相似。此外,日本學者田邊尚雄在其《中國音樂史》中提及一件來自埃及的彈撥樂器,亦是三弦(圖4-2)。此類型以往出現較少,但其出現在絲綢之路南線的和田,則對琵琶傳入的路線有了新的提示。
3. 其他多弦彈撥樂器
除上述樂器,一些圖像材料中還可見到其他多弦彈撥樂器,如渾源圓覺寺塔伎樂磚雕中可見六弦曲項彈撥樂器(圖4-5);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中出土六弦直項彈撥樂器(圖4-3);西安俾矢十囊墓出土伎樂俑中有彈奏二弦彈撥樂器的(圖4-6),這件樂器與拉薩大昭寺藏一件7世紀的彈撥樂器相似(圖4-4)。這些彈撥樂器與典型的琵琶、阮咸等樂器相異,但是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二 琵琶在中國的傳播及相關問題
上述分析基本勾勒出了我國明代以前琵琶的發展脈絡。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經歷了南北朝混亂時期后,琵琶在隋唐時期走向定制。該時期琵琶主要有兩大系統,一是以四弦曲項琵琶、五弦琵琶、四弦直項琵琶三種基本類型為代表的外來系統,其琴身皆為較為展寬的梨形,琴身上有捍撥,直項或曲項,有四至五柱;二是以阮咸為代表的本土系統,皆有圓形琴身,上有捍撥,直項。與這種形制上的定制相對應的是樂制改革。《通典》中所謂“平其散濫,以為折中”[7]正是對這種定制化的概括。通過分期不難看出,琵琶在唐朝時形成形制上的定制與樂律上形成定制在時間上是一致的。十六國北朝以來,伴隨著族群和文化的融合,各類樂器如同百花齊放一般不斷涌現出新的型式。正因如此,在唐朝大一統的局面下,才有了“折中”的前提。對于這個折中的過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首先,在敦煌地區,四弦柳葉形琵琶及五弦琵琶首見于西魏,并涌現于隋代,入唐后消失。新疆地區4~5世紀的石窟壁畫上,四弦柳葉形琵琶及五弦琵琶恰好可以實現其年代上限的續接。這直接表明這類琵琶應是由新疆地區流入敦煌地區的。其出現年代不早于4世紀,亦即北魏前后。《北史·西域傳》記載了宋云等人在北魏時西行取經之事[8],這一事件在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中更有詳細記錄。宋云走出去的道路,與琵琶走進來的道路是一致的。琵琶在佛教世界既是樂器同時也充當著法器。此類型琵琶和五弦琵琶的消亡,在敦煌地區至遲在初唐時期已經不得延續,然而,它們在新疆地區卻一直延續到了8世紀左右。由此可見,這類樂器在新疆地區的主導性和影響性要大于河西地區乃至內地。
第二,關于五弦琵琶,日本學者林謙三、岸邊成雄等先生認為其起源于印度,經過中亞以龜茲為媒介傳入中國。中國學者趙維平先生根據公元2世紀印度阿瑪拉瓦蒂石雕中的五弦圖像,同樣認為五弦琵琶起源于印度[9]。周菁葆認為五弦琵琶應當源自地中海地區,并隨著亞歷山大東征而帶入印度[10]。五弦琵琶在敦煌壁畫中,首見于西魏,新疆地區壁畫中五弦琵琶的出現大致在4世紀左右。此外,從河西走廊到內地不同時期的琵琶圖像層出不窮。酒泉文殊山石窟北涼時期壁畫、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石雕柱礎、安陽北齊范粹墓中所出扁壺裝飾圖像中均有演奏五弦琵琶的樂伎形象(圖5)。此外,結合《隋書·康國傳》中對于五弦的記載[11],我們認為五弦乃是經過龜茲而至敦煌,進而傳入中原。五弦琵琶的圖像在五代時開始衰落,僅在這一時期敦煌壁畫中可以見到,或在詩文中有所提及,至宋之后則徹底不見。
從不同地區的圖像看,四弦曲項琵琶與五弦琵琶時而分別單獨出現,時而作為固定組合出現。從分期看,雖然在敦煌地區五弦琵琶的出現要晚于四弦曲項琵琶,但是新疆地區石窟壁畫中,五弦琵琶的出現并不晚于四弦曲項琵琶,甚至在一定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因此,五弦琵琶派生自四弦曲項琵琶的說法值得商榷。綜觀敦煌與新疆兩個地區的壁畫圖像,梨形四弦曲項琵琶最早見于敦煌地區壁畫應是十六國時期,見于新疆地區石窟卻是在8世紀前后即中唐以后,而見于中原內地墓葬壁畫則是在北齊、北周時期。新疆地區特別是龜茲地區作為琵琶的初傳之地,其壁畫中梨形四弦曲項琵琶的出現較河西地區和內地晚。
這種早晚關系揭示出,四弦曲項琵琶的傳入應有兩種途徑:首先是民間途徑。四弦曲項琵琶源自西亞,并經由中亞傳入,粟特人充當了其傳播的媒介,這在入華粟特人后裔的石質葬具圖像上屢見不鮮(圖6-3)。四弦曲項琵琶由粟特人經過河西走廊帶入中原,并在中原的各個階層流行開來。其二是官方途徑,則或與呂光破龜茲有關。不過,龜茲地區石窟壁畫之所以在一段時期不見四弦曲項琵琶而多見五弦琵琶,可能與佛教儀式有關。在傳入本地后,由于工匠傳統的延續性,其壁畫的圖像表達形式尚未改變。直到中原攻破高昌控制這一地區并建立安西都護府之后,其影響力真正滲透于這一地區,才終于導致五弦琵琶圖像的消失,四弦曲項琵琶成為主導。
與新疆地區壁畫不同,中原內地墓葬壁畫樂舞圖像在其穩定期后,五弦琵琶與四弦曲項琵琶常常是相伴而出的。從兩地的分期統計表來看,這種組合形式自隋代中原內地開始,其后在經歷唐代初年走向定制后,復又經過河西走廊而重新影響到西域地區。不過,這些是五弦與四弦曲項琵琶于4世紀傳入新疆地區之后的情形。再往前追,則不得不參考印度和中亞地區的資料。筆者在山西省博物館看到一件來自印度的大約4世紀的乾達婆奏樂雕像,演奏的是四弦曲項琵琶(圖6-2)。這件雕像表明四弦曲項琵琶于4世紀時如果不是印度本土的樂器,則在4世紀業已進入印度地區。不過,印度地區4世紀之前的圖像與實物中皆不見四弦曲項,由此來看,對于印度而言,這件雕像中的四弦曲項琵琶亦應是外來的。岸邊成雄先生在其兩系統說的基礎上,指出來自印度的五弦與來自中亞的四弦曲項琵琶在中亞坎達拉(今阿富汗)相遇而開始融合[12]。筆者在德國柏林佩加蒙博物館見到一件來自西亞約公元前19~17世紀的泥塑,表現彈奏琉特的伎樂形象,其琴頸恰是曲項結構(圖6-1)。由此,我們較為支持四弦曲項琵琶來自西亞,經中亞和西域傳入中國內地,五弦琵琶更大可能是出于印度系統。
第三,敦煌壁畫中隋代的琵琶在類型上呈現出歷朝歷代最為繁盛的局面,這一時期應當是對南北朝音樂繁復無序局面的一種整合,同時也將開啟唐代琵琶形制統一固定化的先河。
四弦曲項琵琶源自西域,在正史中有記載[11]378。至隋代時,此類琵琶對于中原音樂的音律校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即所謂“龜茲蘇祗婆七調”。向達先生考證該調源自印度,淩廷堪則更直接地認為唐代燕樂即源自蘇祗婆琵琶,并以琵琶四弦定四均二十八調[13]。由此可見,四弦曲項琵琶的出現奠定了整個隋唐燕樂系統的基礎。
從前文的梳理還可看出,琵琶從隋代開始出現捍撥,即在琴箱中部弦下方施加的一層用于保護琴體的覆面。其上常常繪有彩色圖案,這在唐代琵琶定型之后傳入日本的正倉院所藏琵琶中可以得到證實(圖7)。
捍撥在北朝尚未出現。北魏時期,從一些伎樂石雕中可見其琴身表面往往裝飾有圓形花狀圖案(圖8-1),北齊徐顯秀墓壁畫圖像中的琵琶則是通體素面(圖8-2)。在隋唐之后,從河北宣化遼代張世卿墓壁畫中可見,捍撥仍是存在的(圖8-3)。捍撥的再次消失應當是在元代,敦煌莫高窟第465窟的元代琵琶通身施以碎花,與文獻是相符的。不過琵琶在境外的發展情況卻不同。伊朗馬贊德省出土舞蹈紋銀碗所見的琵琶圖像表面即沒有將捍撥表現出來,演奏方式為手彈(圖8-5)。筆者在德國佩加蒙博物館見到一件出土于伊朗、年代約為11~12世紀的黃釉瓷碗。其內壁圖像表現為彈奏五弦琵琶的樂伎,其演奏方式亦為手彈(圖8-4),均與中原地區用撥演奏的方式不同。今天所見的琵琶已無捍撥,但已有二十四柱,顯然已與隋唐琵琶大不相同。
第四,從莫高窟壁畫琵琶圖像分期表可見,在敦煌地區從盛唐開始出現四弦琵琶Aa型,即梨形四弦直項琵琶。這種類型一直延續到五代、中晚唐時期大量出現。
正倉院藏唐代琵琶(圖7)中并無此類型實物,由此推斷該類型應當不是盛唐中原琵琶定型后所傳入。中晚唐時期,敦煌曾一度被吐蕃占領,許多壁畫題材多具有吐蕃藝術的風格,其壁畫中的琵琶圖像來自于吐蕃粉本,自然也會或多或少帶有吐蕃因素。在青海都蘭吐蕃墓M3中所出彩繪木箱狀木器構件上,可見繪有彈奏直項琵琶的人物圖像,其所繪琵琶圖像與敦煌莫高窟壁畫中Aa型琵琶圖像如出一轍。由此推斷,這類四弦直項琵琶很可能是由中原唐朝輸入的琵琶在吐蕃地區完成本土化后所形成的,敦煌第156窟所繪《張議潮統軍出行圖》上的琵琶圖像中直項琵琶亦即此種類型。在庫木吐喇石窟第68窟壁畫圖像上可見一件與上述類型相同的四弦直項琵琶圖像,時代大約在8世紀。這個時期大約是盛唐至中唐時期之間,此類型的琵琶出現似乎在暗示著吐蕃對龜茲地區的影響。琵琶圖像呈現出吐蕃、中原唐朝因素在龜茲、高昌地區的交織出現,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唐朝與吐蕃在西域的爭奪。
三 結 語
綜上所述,琵琶自傳入中國以來,在不同時間段、不同地區的形態和發展是有所變化的。同時,作為彈撥樂器的一類,它與其他類彈撥樂器也較為容易混淆,從而導致文獻對其記載含糊不清。通過對考古材料的全面梳理之后,我們認為隋唐時期的琵琶大體可分上述兩大系統三大類,即以四弦曲項琵琶、四弦直項琵琶、五弦琵琶為代表的外來系統和阮咸琵琶為代表的本土系統。弦和項是區分的核心,琴身的形狀則隨時空分布而略有損益。四弦曲項琵琶源自西亞,并經中亞傳入無疑;五弦琵琶應是在四弦曲項琵琶傳入中國前便已形成。四弦直項琵琶或為吐蕃式琵琶,應當是琵琶自西域輸入吐蕃地區后,又融入中原因素后所成。阮咸之類于東漢時期從西域傳入,經過魏晉南北朝的融合后,隋唐時期業已本土化,文獻中的“秦琵琶”“阮咸琵琶”之稱,當是在胡漢之爭與雅俗分野的時代語境下,與胡樂系統相區別的稱呼。除此之外的其他相關彈撥樂器,均為琵琶的進一步演變發展起到影響作用,因此也不能忽視。不同類型琵琶的發展背后其實是幾個不同文化系統的互動。一件簡單的彈撥樂器的背后,其實是西亞、中亞及東亞幾個系統下文化因素的交流與融合。琵琶在隋唐時期發展至頂峰,更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一時期開放包容的時代特征。
參考文獻:
[1]鄭汝中.敦煌壁畫樂舞研究[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83.
[2]莊壯.敦煌壁畫上的彈撥樂器[J].交響.2004(4):12-21.
[3]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0:54.
[4]王子初,霍旭初.中國音樂文物大系·新疆卷[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
[5]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1363.
[6]周楊.關中地區十六國墓葬出土坐樂俑的時代與來源——十六國時期墓葬制度重建之管窺[C]//西部考古:第14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121.
[7]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3621.
[8]李延壽.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3231.
[9]趙維平.絲綢之路上的琵琶樂器史[J].中國音樂學.2003(4):41-43.
[10]周菁葆.絲綢之路上的五弦琵琶研究[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1(3):122-128.
[11]魏徵,等.隋書·卷八三[M].北京:中華書局,1973:1849.
[12](日)岸邊成雄.古代絲綢之路的音樂[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8:13.
[13]淩廷堪.燕樂考原[M].燕樂三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