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的閃光詩句
電影《詩》里有一個報名參加“寫詩培訓班”的老婦人,常常焦慮地發問:“怎樣才能寫出詩呢?”她刻意尋找可入詩的材料,張開手臂迎接隨時會降臨的詩意,卻總是事與愿違。詩的匱乏不是因為她沒有才情,恰恰相反,是因為情到深處的無言。當世界把巨大的殘酷推到她眼前時,她才開始試著寫下一些辭不達意的“詩句”。及至影片最后,她寫下生命中的第一首,或許也是最后一首詩,獻給被自己唯一的親人傷害的女孩:你在那里好嗎?還是那么美嗎?夕陽是否依然紅彤彤?鳥兒是否還在樹林里唱歌?你能收到我沒寄出的信嗎?我能傳達自己不敢坦白的懺悔嗎?時間會流逝嗎?玫瑰會凋零嗎?
《鋼琴課》 [新西蘭/澳大利亞/法國] 簡·坎皮恩

女主角艾達六歲失聲,活在沉默的世界里,直到她學會了彈琴。父親將她遠嫁給荒島上一個素未謀面的男子,可那個人把她心愛的鋼琴留在了海灘上。艾達求助于島上居民貝恩帶她去海灘上彈琴。貝恩被她感動,用土地從艾達丈夫那里換來鋼琴,而艾達也被貝恩古怪而真摯的愛情打動。影片尾聲,暴怒的丈夫砍下艾達的一根手指。艾達得以與貝恩遠走重洋。在海上,她忽然執意將鋼琴扔進海里,卻不慎被繩子一同拽入水中。片刻的恍惚與猶豫之后,艾達掙脫繩索,奮力游回了水面。英國詩人托馬斯·胡德的小詩《寂靜》出現在旁白中:“夜深人靜之時,我就想起我那葬在海底的鋼琴。有時,好像自己就飄在它的上面。海底寂靜無聲,催人入睡,那是一種怪異的催眠曲,是我的催眠曲。有一種寂靜沒有聲音,有一種寂靜沒有聲音,就像在冰冷的墓穴里,在冰冷的墓穴,在深深的海底。”
《竊聽風暴》 [德] 弗洛里安·亨克爾·馮·多納斯馬爾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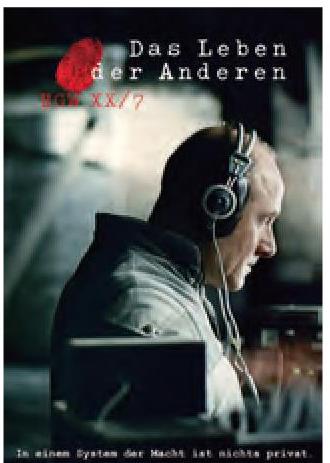
《竊聽風暴》講述1984年的東德,秘密警察威斯勒奉命監聽劇作家德萊曼和他女友的生活。 一次,威斯勒潛入德萊曼家,像飛鳥帶走一根樹枝那樣,拿走了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一本詩文集,回到家中他躺在沙發上翻看其中的詩篇,一種從未有過的暖意慢慢浮現在他毫無表情的面孔之上。這首軟化了威斯勒的心,進而改變他和德萊曼命運的詩是《回憶瑪麗·安》,是布萊希特于1920年2月21日在去往柏林的火車上寫在筆記本上的一首歌頌過去愛情的詩歌,描述了一種愛的經驗。人要如何向善?這是貫穿布萊希特詩歌和戲劇的主題。而正是藝術作品的力量,在影片里完美地展現了引人向善的功能,同時也是善良與希望的隱喻。
《007:大破天幕危機》[英]薩姆·門德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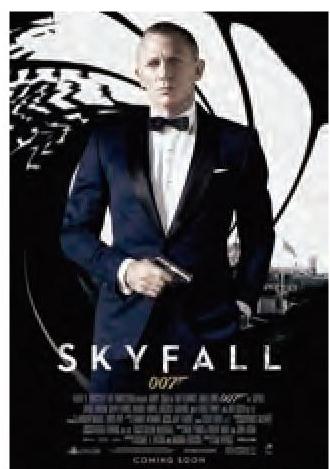
2012年是007系列誕生五十周年,當年上映的《007:大破天幕危機》是007系列的第23部,影片試圖在商業片的框架內給出答案——面對極速變化的時代,邦德們該何去何從?片中的邦德一反過去從容瀟灑的人設,主要因為對他的前傳的描述——在壯闊的蘇格蘭高地,埋葬著他的父母,他痛苦的往昔,他時不時表現出的幼稚和狼狽有了合理的解釋,邦德的一生也得以完整。而最讓人難忘的,是在本片中徹底退出007系列的M女士,或者可以說,她才是這部電影真正的邦女郎。正是因為她的這場告別演出,這部商業片中仿佛又套嵌了一部莎士比亞式的戲劇,通過M的一生,完成了對間諜世界的反思。在聽證會上,M念出英國詩人丁尼生的《尤利西斯》,那是所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詠嘆調——時光與命運消磨了我們,但意志猶健;抗爭,求索,追尋,而絕不屈服。
——為鋼琴獨奏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