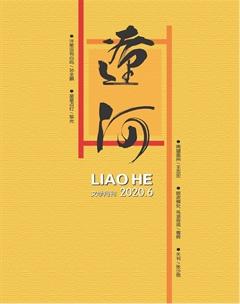南望蓋州
王志宏


一座城,與“關”相關,多年以前,當我置身其間,并未覺得你有什么不同,若干年后,當離你日遠,卻發現與你相關的一切,不經意間都已在記憶中鮮活如初。
東關,西關,南關,北關,便是你的城池,以此向四周伸展,漫延,這就是你——蓋州。“關”,作為古代在險要地方或國界設立的守衛處所:關口;關隘;關卡;關塞。如此等等。如今,城里雖已不見明顯的隘口或者關塞,“關”的稱謂卻讓古城山川多了一份厚重。當我告別少年時光,也便告別了你,離家漂泊,但終究并未走得太遠,太久。
一
一只抽屜里,靜靜地躺著一枚校徽——蓋州高中,當年的全稱是——蓋縣蓋州高級中學。在前樓向往了兩年之后,那棟二層歇山式青磚青瓦小木樓,終于有了我們文科高三·八班的一間教室。《蓋平縣志·藝文志·碑記》記載的《中學校落成記》說,母校校址在縣城西關外。
西關!后來,當我南望1990年蓋州高中小木樓,寫下散文《高三的玫瑰》,那些青蔥歲月,那些曾經在廊柱下仰望芙蓉如蓋的似水年華,那些在課間一次次踏響木樓梯的同窗們,是否還記得是誰曾經在畢業留言冊上寫下“不能相逢是人生的真諦”?
在等候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日子,定居哈爾濱的四姨爺和四姨奶回蓋州探親。四姨爺是一位詩人,當年從暖泉走出去的五舅爺大學畢業后分配到哈爾濱公路勘查設計院,把美麗溫婉的四姨奶許給了他。
那時我還沉浸在為賦新詩強說愁的青澀中,四姨爺對我這個晚輩有一點知音之感。我和姑媽家的娟表妹陪伴四姨爺開啟了三人行的采風之旅,首站去的就是南關,尋訪鐘鼓樓。
幾年后,我曾在一首題為《走出雨季》的詩歌里寫下這樣的詩句,那是鐘鼓樓第一次作為意象走進我的文字:
依然如往的是/鐘鼓樓上的風鈴/似水流年/搖落一個又一個晨昏/流盡所有的故事/悠長而憂傷/古城 有/明清時的磚 青蒼蒼/蝕我韶華/仿佛 亙古的心事/覆滿苔蘚……
2019年一個夏日午后,我陪同母親登臨鐘鼓樓。鐘鼓樓位于蓋州古城的中軸線上,明代洪武五年至九年(1372—1376年)蓋州指揮使吳玉擴南城時,將舊南門改建為鐘鼓樓。鐘鼓樓樓座正中為券頂門洞,是城內南北方向上的交通要道。時隔近三十年,鐘鼓樓上青磚依舊,遠眺古城,繁華之中,依然尚存的一些明清民居,給古城平添了歷史的厚重感。只是,目之所及,不知哪里是1942年正月的八寶胡同,那是父親的出生地,據說就在鐘鼓樓下。
1989年,由兩岸三地影人聯合制作的電影《滾滾紅塵》在蓋州古城拍攝,主要取景地點就在鐘鼓樓及南關明清一條街。《滾滾紅塵》的拍攝在當年的蓋州是一件盛事,這部影片由著名作家三毛作品改編,著名導演嚴浩執導,林青霞、秦漢、張曼玉、吳耀漢主演,次年11月上映。還記得一天午后第一節課前,一位姓趙的男生滿頭大汗跑進教室,熱烈地向同學們敘述去南關鐘鼓樓看林青霞拍電影的所見所聞。有同學問,隔那么多人,你看到林青霞了嗎?他揪起身上的白襯衫傲嬌地說,“當然!看,這白汗衫就是林青霞送我的。”引起全班同學一陣哄笑。
后來,聽說現場一些圍觀的老人、大人和孩子們被邀請當了臨時演員卻是真的,他們換上劇組提供的民國時代的服飾,新奇、興奮地玩了一把穿越。而林青霞十分喜歡蓋州的蘋果和烤紅薯據說也是真的。
《滾滾紅塵》中,鐘鼓樓上的風鈴還依舊嗎?它是否能夠聽到普濟寺的暮鼓晨鐘?2001年4月的一個黃昏,那時還在蓋州工作的我,走過明清一條街,明清城墻,走進慕名已久的普濟寺,并以花占卜一段姻緣。在散文《花讖》中,我記錄下相關那天的一些回憶:沿著那條著名的明清小街漫行。古意濃冽的舊居、灰瓦縫中抖瑟的陳草傍著我穿過鐘鼓樓清揚的鳴音,且不斷回首。不知誰家的迎春高過墻頭,讓我寂寂地比較校園西墻下的花樹,記憶中去年不曾開過……《花讖》中的人在那年晚秋成了我的先生。
二
從姑媽家所在的北關東行十余里,即可抵達青石關。傳說中清代名人王爾烈所書的“古青石關”石碑已湮沒在歷史的時空中,現在碑石上的“古青石關”四個大字是著名書法家沈延毅先生1986年書寫的。沈延毅先生是母校蓋州高中走出的文化名人。蓋高一位同窗家里與沈延毅先生有些淵源,在同學們的想象中,這位同窗家定然收藏著先生的海量墨寶,言辭間頗有羨意。
世事變遷,陪同四姨爺青石關采風的一次偶然,當時并不曾想象過,未來的一年年,我將在四季中若干個時間節點數次經行青石關,在蓋州與大石橋兩市間穿行,回去,回來;抑或回來,回去。
在青石關下的一處山坳里,我和表妹發現一片建筑群,背靠青山,繁華肅穆,不同于周圍民居。后來,才知曉原來那里是殯儀館。2001年和2012年,我相繼在那里送別親愛的外婆和外公。當我離開蓋州,一次次途經那里,匆匆一瞥間,常常會生出莫名的心痛,萬千滋味,有時,那種情緒只一瞬間就會讓我淚流滿面。我深知,有一天,我終將與在蓋州定居的親人們擦肩而過,作為一個不再擁有蓋州戶籍的人,我終將會錯過那里。而寫下這些文字的這一刻,左眼的淚滴先于右眼的奔涌而出。
三
我第一個工作單位在東關下,我在那里度過近3600個日子。我在月季花暗香浮動的黃昏練習小提琴,吹奏單簧管,彈撥柳琴,也打過總是慢半拍的大鈸。那些日子,我為進步緩慢流過淚,也曾為成績優異流過淚。
西行,去北關的姑媽家和西關的舅舅家,東行40華里可以回家,我的暖泉小鎮,我的村莊,一個三面環山的狹長山谷。安享她冬日慵懶的朝陽,夏日滿山的蔥蘢,秋日絢爛的野菊,春日枯瘦的那一抹溪水,以及那一場場暮雨和朝雪。
棗木溝,就是她的芳名,幾乎家家遍植棗樹。我現在所住小區的庭園中,芳鄰也植了三株棗樹。我經常佇立窗前,生出今夕何夕,此地何地的疑惑。棗樹已經發芽,枝頭猶掛舊年的果實,這種似曾相識的情景總情不自禁地讓我想起我家的后園,不知那些棗樹現在已高過屋檐和炊煙幾許,那些棗兒們當年枝頭搖曳的樣子,初雪中的樣子,躺在草地上的樣子……多么令人懷想!也忘記了是夏天,還是秋日,棗樹旁,桃樹上結成的一枚琥珀,不知把誰裹進了時光深處。
我的先祖王泌兄弟二人自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攜妻挈子從山東萊州府高密縣遷徙至蓋平縣城東正紅旗界今日之棗木溝,繁衍生息,如今已是272年,傳承十二代。我喜歡坐在梧桐樹下的青石板上聽父親追憶從前——
我的伯父,作為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天之驕子,離開棗木溝,過暖泉橋,出東關奔西關,乘坐綠皮火車去省城求學,赴貴州支援三線建設,他以高原作物取的筆名延用至遼寧。
我的祖父,五十年前的農歷四月初十,他英勇地拖住飛馳的驚馬,從車輪下救出十幾個稚嫩如蓓蕾的生命,他以壯年之軀舍生取義,祖父犧牲時年僅五十周歲,那是被授予烈士稱號的祖父所擁有的全部人生。祖父生前,曾趕著馬車去趕海,他伴著噠噠的馬蹄聲往返百余里。去時,拉著滿車柞木柴,歸來時,木柴已變成兩大桶黃花魚。我的高氏曾祖母和陳氏祖母把魚一一清洗干凈,用大粒海鹽腌制好,晾曬在大敞筐里,待魚半干,拿出線板,把魚穿起來掛在窗欞上。大雪封山,和白菜、土豆、酸菜、蘿卜、豆腐一起調濟著有滋有味的日子。
1990年7月,我去看過祖父曾趕海的那一片海。那年結束高考,我和幾名同窗受一位團山籍同學之邀,去她家里作客。那是我第一次看海,在沙灘上和同窗們留下18歲的青春,在落日余暉中追想祖父的背影……
25年后,我第二次走進那里,這片河海交匯處的海域已發展成為遼寧北海國家級海洋公園,擁有中國北部僅有、規模最大且歷經18億年形成的海蝕地貌奇景,向世人展示著她的瑰麗和傳奇。
四
“東柞蠶,西漁鹽,南產蘋果,北產棉。”這是蓋州古城物華天寶,物阜民豐的一個民間例證。
我家所在的暖泉鎮,就以蘋果和柞蠶聞名遠近。當父親厭倦了施工員的漂泊不定,在知天命之年帶著走南闖北的故事回歸田園,在再次遠離村莊之前,守著幾畝責任田、房前屋后的自留地、兩片果園和山場,和母親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父親的主持下,我家也曾有過幾場蠶事,假期的我和那些被穿成長串兒的兩千繭種共處一室,見證過一只繭成蛾成卵成蠶以至作繭自縛的一生。
那樣的一些日子,父親和母親從山上歸來,時時帶給我們驚喜。有時是幾串藍紫色的山葡萄,有時是幾朵紅紅白白的山芍藥,還有串龍骨、紫術、玉竺、豬苓、石柱花、八卦牛、白頭翁、藍蓬籽、徐長卿等中草藥。擔了井水,把它們洗干凈,放在陽臺上晾曬,積攢起來,出售給那些沿街收購草藥的小商販兒。父親認識的中草藥多達幾十種,他還認得家鄉群山中以蕨菜為主的多種野菜。
我的曾祖父,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在方圓數里樹立良好的口碑。他為我的父輩們取名“祥奎顯耀(中)華”,那是曾祖父作為鄉村士紳樸素而高貴的美好愿景,他心中的家國模樣。
初中二年級的秋天,每天放學路上,我都要在距家五里路的四壟棉田小駐,讓我的紅色“駿馬”牌折疊坤車靠在地頭兒,幫母親撿棉花。我喜歡棉花,雪白的棉朵讓人感到安適而溫暖。當我載著母親一天的勞作騎行在回家的路上,那些隱沒了夕陽的黃昏總感覺格外匆促,少年時光卻似乎因為這些記憶的枝枝杈杈而顯得格外漫長。
五
在十二歲之前,對于暖泉,我并非一個全程的參與者,我與她共度的只是一些散碎的時光,因為缺席的那部分被留在了外婆家——蓋州旺興仁鄉(2002年并入梁屯鎮)劉堡村。
“枯水的河灘,河灘上的黃昏,黃昏里的說書人,露天電影,皮影戲。”那是我在散文《劉堡的黃昏和夜晚》中經過克制的回憶。高中時代,我曾陪伴在師范學校就讀的好友,去拜訪過素有“東北皮影張”之稱的張勇夫先生,近距離欣賞那些璀璨的“影人”,感受“一口道盡千年事,雙手對舞百萬兵”的皮影藝術。
正月里的高蹺秧歌,鳳冠霞帔,男扮女裝的演員讓我心懷好奇和猜想,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外婆家的親戚,我遵命叫他姑姥爺,然而,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殺年豬的民間高手。臘八過后,外婆帶我去綿延村邀請這位姑姥爺來家幫忙,因為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干凈人”。時隔多年,我仍記得他把冒著熱氣的“燈籠掛”(豬的內臟)掛到院子里枝葉干枯的蘋果樹上的情景,記得他仰頭張掛時平和滿意的笑容。
姑姥爺家的小姨和舅舅帶我去看綿羊頂,長大后我才知道,那是遼南第二高峰,海拔近1046米。那座山上有一種果子叫圓棗,口感類似獼猴桃,不知為何會記得清楚。
旺興仁西北連接暖泉鎮(請原諒我的記憶總是停留在過去),我幾乎熟知兩個小鎮間所有的山嶺:古老的只通行人的背古嶺,緊張得要屏住呼吸的七盤嶺,送外婆回鄉歸葬的義爾嶺,以及戴峪嶺崎嶇險峻的前世和莊蓋高速涵洞連接的今生。從四歲至十二歲,我相繼在雙親和二姨的懷抱里、在外婆溫暖的背上、在舅舅顫悠悠的挑筐以及后來他所擁有的各種汽車中,至少一年兩次經行那些山嶺,就像一只候鳥,在外婆與我家之間按時遷徙。
上世紀九十年代后,外婆舉家外遷至西關附近,隨舅舅一起生活,我和劉堡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少。但外婆家檐下長長的冰凌,后山坡上柔滑的苫房草,和老姨一起扒烏米的時光,紫色的毛骨朵花,山腳下的花椒樹,香甜軟糯的梨坨,南山的松傘蘑,以及那樣一群小伙伴,他們的乳名叫大燕子、小敏子、三胖子、連喜子……以及那些雪后空寂的街巷,我的班主任老師背著我,我披著他的棉袍,“咯吱,咯吱”踩在雪地上的聲音,連同他頭上蒸騰的霧氣,也都在我的記憶里駐扎下來。
六
前幾日,父親給我發來幾張圖片,《蓋州古城簡介》《蓋州古城微縮景觀》(明清時期),厚重的歷史感從青瓦、城墻中撲面而來,讓我頓感莊嚴和鄭重。
父輩口中的三江會館,好友筆下生生不息的鶴陽山,曾經與三四友人流連其間的轉山湖,三霄娘娘出走的煙筒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上帝廟(玄貞觀),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石棚……這樣一些集合,凝結融合成了古城蓋州,我的出生地,而立前生活、成長的地方。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曾經并將還要填寫多少份履歷?在鍵盤上用五筆輸入法敲下UGYT四個字母所對應的“蓋州”二字,或者在紙質表格上一筆一劃虔敬工整地手書上去。那一張張履歷表真實無虛地記錄著我的來處。
回到蓋州,經過之處,我習慣性地以東關、西關、南關、北關來判定所處位置,就像用經緯判斷坐標。離開蓋州,我常常在你眾多的別名中南望于你。就連下鄉,走過西部的水田,東部的山巒,也禁不住去對照你的山水,田園,風物,村莊。路遇兩市間的城際客車,擋風玻璃上的“蓋州”標牌,也會長久地駐留在我的眼里。
又是春天,南望遠方家園,墻邊紅藥,遠山杜鵑,棗樹新芽并舊日的棗兒又該兀自風中搖曳。至蓋州六十里,經北關至故園四十里。
提筆匆匆記下上述句子,心生微瀾。當左手離開這半頁A4紙,食指仿佛被什么凝滯住,原來,幾點淚痕堆疊處,指腹大的一粒紙,宛若一幅掀起的簾,“颯”的一聲,粘破一個小小的空洞。我知道,那就是思念的聲音,思念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