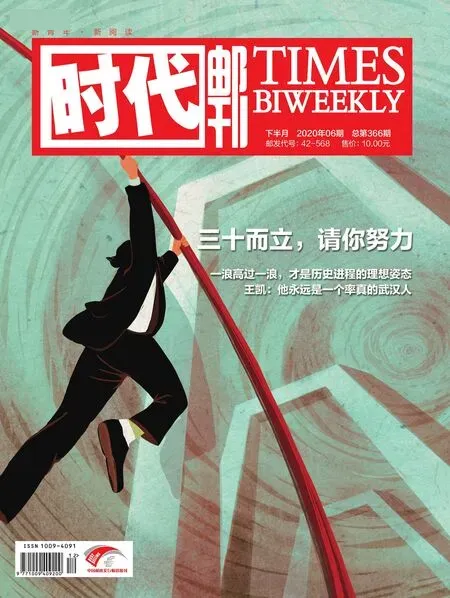王澍:我要用建筑搶救中國傳統文化

2012年5月,王澍在人民大會堂接受普利茲克獎章,他的獲獎感言頗有幾分悲壯色彩:“獲得這個獎對我來說多少有些不期而至的感覺,在多年孤獨的堅持之后,對一個在獲獎之前沒有出版過任何作品集的建筑師,對于一個只在中國做過建筑的建筑師,一位自稱為業余的建筑師,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驚喜。”
作為第一位獲得建筑界“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作為曾被嘲笑批判的反面教材,他對過去的際遇一笑置之:“多一些異類,對中國的發展肯定是好的。”
打開中國建筑與世界的精神共鳴
上世紀80年代,在大學里研究中國山水畫的王澍成了眾人眼里的異類:“那個年代學校里面沒有人看這個,大家都特別狂熱地學習西方的東西,很多人覺得我這樣像個怪物。”
好在時任校長錢鐘韓,文學家錢鍾書的堂弟,給了他力量:“你們不要迷信老師,你要認真準備的話,用三個問題一定會問到他臺上下不來的。”王澍也一直帶著這種批判思維去反思和自學。
1992年,新一輪改革開放,無數中外建筑師在中國大地掘金,王澍卻選擇與妻子陸文宇搬到杭州山林間隱居,遠離商業喧囂,整日看書研畫,把知識領域擴大到歷史、哲學、文學甚至是人類學,與工匠同吃同工,觸摸最真實的建造。
在“游山玩水”的日子里,王澍曾數次造訪蘇州園林,中國傳統的文人情趣令他著迷。一座假山,自下而上,雖有兩三條道路,互不交互,但都可到達頂端,“循環往復就是人生”的道理油然而生。
見一山便是見人生,建一房便是建世界,中國古代文人的山水意境也讓王澍頓悟:“從自然中獲取靈感,在人工與自然之間有所創造發展,這是中華文明最厲害的地方。”
后來,這一獨特的“文人哲匠”理念一直貫穿于他的創作中,山脈、水流等傳統元素在他的建筑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如寧波歷史博物館的設計思路就源自于他某次途經華山所見到“拔地而起”的壯闊景象,這些作品也讓王澍獲得世界權威的肯定。
2012年,普利茲克獎頒獎典禮現場,評審委員會主席帕倫博勛爵在祝詞中說道:“王澍的設計根植于中國傳統和文化,他的建筑語言如同其他偉大的建筑體系一樣指引人們的內心,在他的作品中首次看到了中國當代建筑的價值。”
執行委員會更是不吝夸贊:“中國建筑師與普利茲克獎的疏離在于精神層面,這一次王澍打開了中國建筑與世界的精神共鳴。”
建筑師與上帝同責
作為第一位獲得世界建筑界最高榮譽的中國人,王澍在成名前卻始終是建筑界的邊緣人。因為崇尚向自然學習,提倡以傳統為基礎創作,導致他的作品經常被大眾評價“又土又丑”,其中最受詬病的實屬他的代表作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

王澍設計的富陽文村
2000年,王澍“出關”,來到中國美術學院任教,恰逢新建校區,需要建筑師設計,但因造價只有同規模工程的一半,無人敢接。
王澍站了出來,對院長說:“你定這么低的造價標準,還要達到國際水準,這些我都能做得到,但我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徹底的自由。”
4年的自由創作后,象山美院一期工程完工,贊美與批評之聲接踵而至。前者在離校園一百米開外,便已開始備受震撼。入口是一堵墻,而不是門,讓人有縱身一躍、奔向自然的沖動。制墻用的800萬片舊磚瓦是特地從全省各處拆遷工地上挖來的,每一片都飽含記憶,在此地迎來新生。800畝土地上散落著整整30多棟樓房,像極了一個村落。學生們在樹蔭下看書,學者在夜燈下談話,儼然一處學術可以自由發生的“世外桃源”。用評論家的話說:“最妙的是在一個院子里,一回頭,透過那個大門框,竟然能看到《溪山行旅圖》的景象。”更有人說:“自從王澍的象山校區建成后,才有了象山。”
但批評者則認為這些摒棄現代審美的建筑很丑,材料看起來“臟臟的”“舊舊的”,甚至有業內著名建筑師毫不留情地批評:“要找杭州市里最難看的建筑,那就去象山吧!”
8年后,王澍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爭議才終于停止。2013年,王澍入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全世界100位最有影響力人物,并被評價“掀起了國際建筑舞臺上的中國熱潮。”
對于此前的際遇,他卻始終想得很開:“我們正好碰到了中國乃至世界非常少見的短時間之內如此巨大規模的快速建設,在這個時間之內,建筑師不是一個普通的角色,建筑師的所作所為直接改天換地,影響到幾乎所有人的生活,就像在做上帝的事兒。”
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筑都應該超越個人
成名之后,王澍仍舊在中國美術學院建筑學院里低調任職,直到2016年才帶著“富春山居村”再次回歸。原來這消失的四年,除了本職工作,他都躲在農村里搶救中國文化:“中國的城市如果談傳統文化的恢復或者平衡的恢復,我個人認為幾乎沒有可能,但是中國的鄉村,那個文化還有可能搶救。你如果不搶救,十年之內全部消失。”
富陽文村是王澍在被專家列為保護名錄的古村之外挑選的,被他戲稱為“半殘村”。首次進村,他便一眼注意到村口小賣部,幾位老奶奶坐在門口聊天、曬太陽,這樣生活狀態讓王澍回想起兒時與母親一起下農田的場景。
2016年春節,村民們沒有等來想象中的“美國大都市”,24棟新房子看上去比以前更舊。黑灰的外表看上去很臟,是王澍用當地山上的杭灰石與夯土制作的,可謂就地取材。他還堅持一屋一院,并特地把廚房建得很大。“第一批分新房,我們給了13戶村民優先挑選權,最終只有一戶選擇自建。”對于村民的理解與接受,王澍很感激。
完工后,他經常回到文村,沒人會找他合影、要簽名,這里如同“透明人”般的生活讓他享受。他看著村民按照自己設想,自發用回土灶,建起雙堂屋祭拜祖宗,當年坐在村口聊天的老太太現在仍坐在那里:“這種平靜如水的生活,大家在那里依舊很高興、美好的狀態,讓我非常開心。”
如今,王澍已收起年少輕狂,變得平和許多。“最偉大的建筑往往是那些匿名的、不知道設計師是誰的建筑,世上最偉大的建筑都應該超越建筑師個人,人們看到我的建筑不知道是我做的,這是我最期望的事。”說完這句話,王澍頑皮地笑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