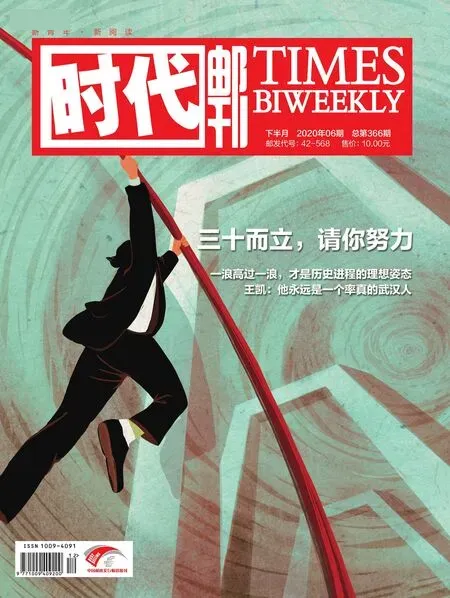《過昭關》:專注凝視鄉村人的精神世界



《過昭關》是部優秀的文藝片,而且尤為難得的是一部鄉村題材,導演霍猛僅僅花了40萬元就完成了它,院線上映雖然票房不高,但卻榮獲多個獎項,受到文藝片愛好者的青睞。在國內,得到了第2屆平遙國際電影展的最佳導演榮譽,也在第22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電影頻道傳媒大獎上斬獲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霍猛在賈樟柯主導的平遙電影節獲獎,更加讓人覺得他們兩位在電影品位上趨同。
《過昭關》的故事很簡單:老人李福長意外得知多年前幫助過自己的老友因病將逝,于是帶上放暑假的孫子開著一輛三輪車千里迢迢去看望老友,一路上披星戴月,在如詩如畫的鄉村田野中穿行,遇到過危險,也與人交換過信任與暖意,這一路走下來,淡定的老人用緩慢的話語,給孫子灌輸了不少人生的哲理。
“我好比哀哀長空雁,我好比龍游在淺沙灘,我好比魚兒吞了鉤線,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舟船……”這是戲曲《過昭關》的唱詞,《過昭關》里的老人把過往自己的一道道難關都藏在了背影與聲音的后面,他說話的時候雖然有千帆過后的平靜,但觀眾很輕易能從他的語調中聽出苦難的痕跡。
老友相見,本該雙手緊握,淚流成行,可這只是觀眾的一種想當然,在老人帶著他的孫子千辛萬苦到了醫院見到老友之后,他們平靜得根本不像幾十年沒見過,霍猛導演在處理這個情節的時候,用了極簡的方式,兩位老人之間一共只發生了三次對話,第一次是剛進門時說的:“吃飯了沒?”“吃了。”第二次準備告別時:“留下來吃飯吧!”“走了。”第三次是告別后老友的兒子打開窗戶喊住老人,轉告了父親的一句話,“他說讓你‘慢點走’。”
整部影片的平淡風格,至此到了更為平淡如水的時刻,但對于有過過去時代生活經歷的中年觀眾來說,以這三次對話為標志,影片的情緒醞釀到了一個高峰,讓人有潸然淚下的沖動。在漫長的農耕時代,“吃”和“走”無疑是最難實現安穩的事情,餓肚子與行路難,給無數鄉村人留下了深深的記憶,這種記憶是由傷痕與痛楚構成的。
《過昭關》鏡頭里的鄉村與田野很美,這種美是帶有“濾鏡”效果的,用這么美的鏡頭、這么舒緩的節奏、這么淡定的人物來表現鄉村,在國產電影中是不多見的,也是近年來剛出現的新表達形式。過去電影里的農民,很多時候是夸張的、失真的,經常讓人聯想到貧窮與落后,但《過昭關》不一樣,它讓觀眾感受到了一份詩意,這份詩意來自于我們的歷史與文化深處,擁有著一份穿過時光般的優雅。年輕的電影人,在用這份獨特的眼光,來重新幫助中國的鄉村、農民來立傳,并且堅決地切割掉對苦難的“景觀化”表達,專注凝視鄉村人的精神世界。
這部電影,不由讓我想到:人活在大地上,無論什么身份,無論面對什么,都要有一份淡定、優雅的態度,在這份態度面前,苦難也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