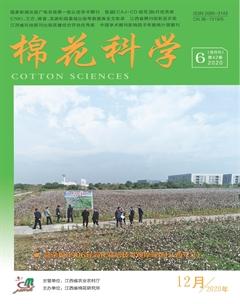五種除草劑對棉田雜草防效及棉花產量的影響
韓冰 王宏棟 韓雙 王汝明 劉文海 李冬剛



摘要:為探索安全高效的棉田雜草化學防除技術,選用5種化學除草劑防治棉田雜草進行田間藥效試驗,以期篩選出對棉田雜草防效好,對棉花安全的藥劑和適宜用量。結果表明,該5種藥劑對棉田雜草的防治效果由高到低依次為精異丙甲草胺>仲丁靈>二甲戊靈>乙草胺>丙炔氟草胺。各藥劑均能夠有效地防除棉田雜草,并對棉花具有較好的安全性。960 g/L精異丙甲草胺乳油為首選藥劑。
關鍵詞:除草劑;棉田雜草;防效;棉花產量
中圖分類號:S562. S451?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2095-3143(2020)06-0041-04
DOI:10.3969/j.issn.2095-3143.2020.06.009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safe and efficient chemical control techniques for weeds in cotton fields, five chemical herbicides were selected to control weeds in cotton fields for field efficacy traitsand its appropriate dosag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controlling weeds in cotton fields and safe for cott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rol effects of the five pesticides on weeds in cotton fields from high to low were metolachlor>sec-butyryl > pendimethalin>acetochlor>flumioxazin. All medicaments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weeds in cotton fields and have good safety to cotton. 960 g/L refined metolachlor EC is the first choice.
Key words:? Herbicide; Cotton field weeds; Control efficiency; Cotton yield
0? 引言
棉花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作物和國家戰略物質,也是山東省的主要經濟作物,其生產量和消費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在我國已有2000余年的種植歷史[1-2]。
雜草一直是困擾棉花生產及全程機械化的大問題,其發生危害導致棉花減產,品質下降[3]。隨著經濟的發展,種植棉花的成本快速上升,棉田雜草的防除成本不斷增加[4]。目前,我國在棉田雜草防除中主要采取人工防除、農業防除、化學防除、物理防除、生物生態防除和植物檢疫6種方法[5],其中化學防除成為目前棉田雜草防除的主要措施。近幾年,除草劑登記品種越來越多,篩選高效、低毒且對棉花安全的除草劑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6]。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試驗選用的5種除草劑是330 g/L二甲戊靈乳油、300 g/L丙炔氟草胺懸浮劑、815 g/L乙草胺乳油、360 g/L仲丁靈懸浮劑和960 g/L精異丙甲草胺乳油,分別以1~5為處理編號。
供試棉花品種為魯棉研28號。施藥采用土壤噴霧的方式,施藥后立即混土,再播種,最后覆膜。防除雜草對象主要是雙子葉雜草的馬齒莧(Portulaca oleracea L.)和反枝莧(Amaranthus retroflexus)、單子葉雜草的牛筋草(Eleusine indica (L.) Gaertn.)和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L.) Scop.)[7]。
1.2? 試驗條件及方法
試驗設在德州市黃河涯鎮黃河涯村(37°27N,116°18E),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該田為壤土類型,土壤基本理化性質是有機質含量11.3 g/kg,全氮0.74 g/kg,速效氮64 mg/kg,速效磷8.06 mg/kg,速效鉀95 mg/kg,pH值7.1,土壤肥力中等,地勢平坦,水肥條件好,為棉花一熟連作田。
試驗田面積20000 m2,設6個處理,分別是前述5種除草劑,以空白為對照(處理6),5種藥劑具體用量見表1。每個處理4次重復,小區隨機排列,小區面積20 m2。于2019年4月28日用WS-16型手動壓縮噴霧器進行田間噴霧,噴嘴圓錐型,每分鐘流量為700 ml,用水量600 L/hm2。2019年4月29日按行距0.75 m進行棉花點播,棉花播種后不進行任何病蟲害、雜草防治措施。其他管理措施同常規大田。
1.3? 取樣調查與統計方法
1.3.1? 對雜草防效調查
施藥后進行2次調查,第一次在施藥后20天,調查雜草株數,計算株數防效;第二次在施藥后40天, 調查雜草株數和鮮重,計算株數防效和鮮重防效。采用絕對值調查法,即每小區4點取樣,每點查0.25 m2(0.5 m×0.5 m),計1 m2內殘留雜草的種類、株數和鮮重,計算株數和鮮重防效。其計算公式如下。
株數防效(%)=[(對照區雜草株數-處理區雜草株數)/對照區雜草株數]×100
鮮重防效(%)=[(對照區雜草鮮重-處理區雜草鮮重)/對照區雜草鮮重]×100
1.3.2? 對棉花安全性和產量調查
施藥后10天以及藥效調查同時,目測調查藥劑對作物安全性。主要觀察施藥后對作物有無枯斑、黃化、畸形、死苗等藥害癥狀,按5級藥害分級方法(1級為生長正常,無任何受害癥狀;2級為輕微藥害,受害少于10%;3級為中等藥害,以后能恢復,不影響產量;4級為藥害較重,難以恢復,造成減產;5級為藥害嚴重,不能恢復,造成明顯減產或絕產)進行評判。
各小區籽棉分別單獨收獲,累計各小區霜前籽棉產量。
1.3.3? 統計分析
依據《農藥田間藥效試驗準則》計算防治效果,田間試驗數據均采用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除草效果
2.1.1? 藥后20 d株防效
藥后20 d,各藥劑處理對棉田雜草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其中,精異丙甲草對馬齒莧、反枝莧、牛筋草、馬唐等為主的棉田雜草總體株防效最高,為80.00%,仲丁靈對這四種雜草的總體株防效其次,為79.26%,二甲戊靈和乙草胺的總體株防效分別為75.71%和73.68%,丙炔氟草胺的總體株防效最低,為68.96%(見表2)。
2.1.2? 藥后40 d株防效
藥后40 d,各藥劑處理對雜草的防治效果進一步加強,對四種雜草總體株防效比藥后20 d的防效均有了提高。其中,精異丙甲草胺提高了8.89個百分點,仲丁靈提高了5.59個百分點,二甲戊靈和乙草胺分別提高了5.2和5.7個百分點,丙炔氟草胺提高了6.34個百分點(見表3)。
2.1.3? 藥后40 d鮮重防效
藥后40 d,5個藥劑處理的雜草總體鮮重防效與株數防效基本一致,防治效果由高到低依次為精異丙甲草胺>仲丁靈>二甲戊靈>乙草胺>丙炔氟草胺(見表3)。
2.2? 棉花產量
棉花成熟時測產,統計霜前籽棉累計產量。結果表明,各藥劑防除棉田雜草后,均有不同程度的增產效果。其中,精異丙甲草胺比空白對照增產12.73%,仲丁靈和乙草胺比空白對照增產均為11.93%,二甲戊靈比空白對照增產11.80%,丙炔氟草胺比空白對照增產11.66%(見表4)。
2.3? 殺草譜
精異丙甲草胺和仲丁靈對雙子葉雜草的馬齒莧、反枝莧,單子葉雜草的牛筋草、馬唐的防治效果較優。二甲戊靈和乙草胺對雙子葉雜草的馬齒莧、反枝莧,單子葉雜草的牛筋草、馬唐的防治效果較好。丙炔氟草胺對各種雜草的防治效果均較差。
2.4? 安全性
施藥后觀察,空白對照區雜草生長正常,藥劑處理區雜草吸收藥劑后停止生長,葉片褪綠枯黃,逐漸整株死亡。施藥區棉花無枯斑、黃化、矮化等藥害癥狀。
3? 結論與討論
330 g/L 二甲戊靈乳油、300 g/L 丙炔氟草胺懸浮劑、815 g/L 乙草胺乳油、360 g/L 仲丁靈懸浮劑和960 g/L精異丙甲草胺乳油對棉田雜草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防治效果由高到低依次為精異丙甲草胺、仲丁靈、二甲戊靈、乙草胺和丙炔氟草胺,其中以精異丙甲草胺最好,仲丁靈其次,丙炔氟草胺略差些。這些藥劑在試驗推薦劑量內,對棉花安全性高,能夠提高棉花產量,建議在播前進行土壤噴霧處理。
化學防治技術在我國雜草防治工作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其適用范圍廣、見效快、方便簡單,深受廣大農民喜愛,但存在的毒性高、影響對農作物生長、嚴重污染自然環境、易使雜草產生抗藥性等問題也不容小覷。因此,農田雜草的防治仍要采用機械除草、物理除草、生物除草和化學除草相結合的方式,科學地使用化學農藥防治[8],多采用一些毒性較低的化學試劑。對于本試驗采用的幾種藥劑,其復配藥劑對棉花田雜草的防效、棉花產量的影響是下一步研究的重點。
參考文獻
[1] 史加亮,趙文超,董靈艷,等. 不同種植模式對棉花產量及品質的影響[J]. 山東農業科學,2020,52(05):42-46.
[2] 連玉朱,王金信,李浙江,等. 幾種棉田除草劑大田防除效果及其對棉花的安全性測定[J]. 農藥,2006(04):270-271.
[3] 朱玉永,趙冰梅,田英,等. 4種助劑對棉田除草劑的減量效果及對苗期棉花的安全性[J]. 中國植保導刊,2020,40(08):72-74.
[4]趙文超,史加亮,李鳳瑞,等. 黃河流域棉區棉花與辣椒間作種植模式的可行性研究[J]. 棉花科學, 2020,42(02):22-27.
[5] 馬小艷,馬艷,彭軍,等. 我國棉田雜草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勢[J]. 棉花學報,2012,22(4):372-380.
[6] 邢茂德,耿軍,遲歸兵,等.? 24種除草劑對棉花植株的安全性及棉田雜草防除的研究[J]. 農業科技通訊,2015(01):63-67.
[7]齊洪鑫,馬燕,韓冰, 等. 魯西北地區5種除草劑防除玉米田雜草的田間藥效[J]. 安徽農業科學,2017,45(33):160-162.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7.33.053.
[8] 李學敏. 無公害馬鈴薯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J]. 安徽農學通報(下半月刊),2011,17(16):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