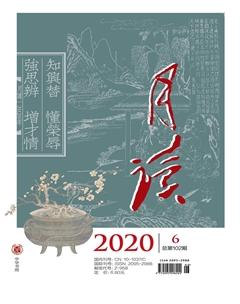《史通》:中國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
鐘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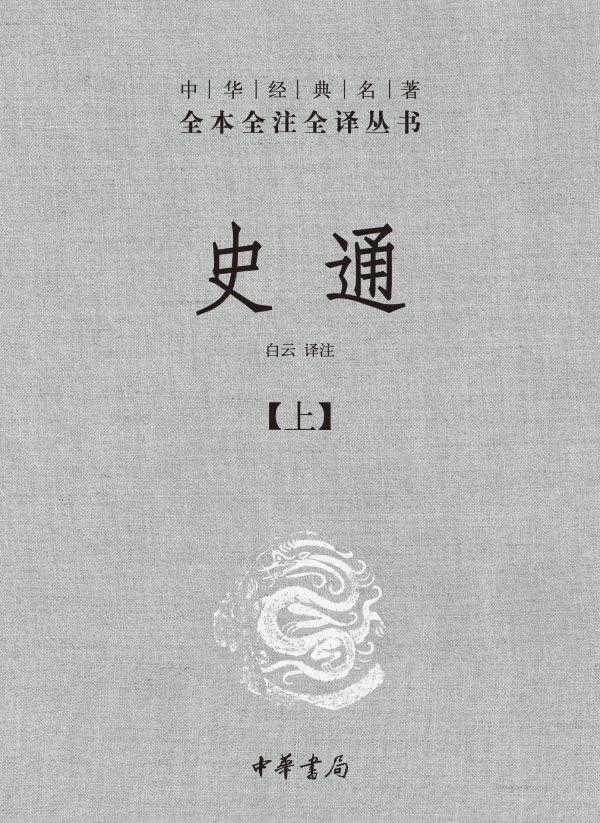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說道:“中國于各種學問,唯史學最為發達;史學在世界各國中,唯中國為最發達。”中國史籍范圍之廣、種類之多、內容之富、材料之詳、史料價值之高,是舉世罕見的。像《論語》《老子》《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重要典籍。細究起來,我國有著近三千年的史書編纂史,而且綿延不斷。然而,關于史學理論的反思和系統總結,卻直到唐代才真正出現,這就是劉知幾(jī)的《史通》。
《史通》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學史,它首次對初唐以前的史學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總結和批評,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
史學家劉知幾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生于唐高宗時期,卒于唐玄宗時期,一生經歷了唐高宗、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個皇帝,主要活動是在武則天時代。劉知幾生活的年代正好介于“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之間,政治制度的日趨完善,經濟的發展,以及文化的繁榮,給劉知幾的寫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劉知幾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之家,家學淵源深厚。從祖父劉胤之是知名學者和很有素養的史學家,他與唐初著名史家李百藥是至交好友,李百藥就是“二十四史”之一《北齊書》的作者。劉胤之在唐高祖武德年間任信都令,有良好的政聲。唐高宗時期,調任著作郎,與當時著名史學家、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等共同修撰國史和《貞觀實錄》。劉知幾的父親劉藏器是一位正直賢能、才華出眾的官員兼學者,擅長文章辭賦,文學、經學的造詣都很深厚,《全唐文》中收錄了他的《恤刑》《刑法得失》和《往代為刑是非》等三篇對策,對政治得失頗有見解。劉知幾的長兄知柔、次兄知章也對他影響極大。尤其是長兄知柔,性格內向,勤儉樸實,喜清靜,善辭章,擔任過州長史、刺史、戶部侍郎、國子司業、東都留守等職,死后追贈太子少保,謚號日文,他成為劉知幾治學、做人的榜樣。
祖輩父輩的教誨,兄長的感召,以及整個家庭氛圍的感染,使劉知幾自幼便喜歡詩賦,有很好的文筆。大約十一歲時,父親便給他講授《尚書》,希望他能精通此部經典,成為名家。但《尚書》的內容多為春秋以前史官記錄的政府文件以及政治論文,語言深澀,枯燥難懂。劉知幾對此毫無興趣,雖然父親嚴格督教,仍沒有什么長進。然而,當父親給兄長們講授《左傳》時,劉知幾卻很感興趣,因而常常放下《尚書》去偷聽;他被《左傳》中精彩的歷史故事和父親的生動講述所深深吸引,暗自記下來許多內容。在父親講解后,劉知幾常常將自己記下的精彩情節描述給兄長們聽,這件事引起了父親的注意。父親知道這個兒子志不在《尚書》,便轉而為他講授《左傳》。劉知幾進步飛快,僅僅一年時間,講解記誦就全部完成了。
少年時,劉知幾便開始廣泛接觸歷史典籍,增長了知識,拓寬了視野,激發了求知欲,加深了對歷史的了解和對史學的興趣,同時也養成了一定的批判精神。高宗永隆元年(680),二十歲的劉知幾中了進士,出任獲嘉縣(今屬河南)主簿,負責掌管文書檔案。劉知幾做此官,不求升遷,公務之余,一心研究史學。他常往來于長安、洛陽之間,借閱公私藏書,盡情閱覽;官位雖未提升,但學術成就卻越來越大。武后圣歷二年(699),三十九歲的劉知幾被調到京城長安,任定王府倉曹,參與編纂《三教珠英》,這是一部大型的詩歌選集。后出任著作佐郎,正式成為史官,掌修史之事。
然而,當時史館的大權掌握在依靠武則天且不學無術的武三思手中,且內部互相排擠,劉知幾提出的編修史書的正確意見和建議都不被采納,在種種碰壁和左右為難后,他只得“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這里的“志”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借厘定群史、商榷史篇,獨創一家之學;另一層是追求史家的“實錄”精神,不受權貴的左右。終于,在景龍四年(710),五十歲的劉知幾撰成《史通》,對初唐以前史學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總結,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
此后,劉知幾聲名鵲起,升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加銀青光祿大夫。唐玄宗時,又遷左散騎常侍,仍參與修史。
不料,開元九年(721),劉知幾的長子觸犯法律而被治罪流放。劉知幾替子申辯,觸怒了皇帝唐玄宗,被貶為安州都督府別駕(安州在今湖北安陸,別駕為正四品下,屬于副職或虛職)。時年六十一歲的劉知幾從長安出發,長途跋涉去安州任職,由于旅途勞累,心情苦悶,到安州不久便去世了。
劉知幾從十一歲開始直至去世,都在學習和研究歷史,加之長期擔任史官,能夠接觸大量珍貴史料,使他具有很高的史學造詣。《史通》之所以能得到后世的肯定,與劉知幾深厚的學養是分不開的。
《史通》的體例和主要內容
《史通》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章,今存四十九章,分為內、外兩篇,內篇為主,外篇為輔。其中內篇十卷,本為三十九章,今存三十六章,亡佚三章,即《體統》《紕繆》《弛張》僅存篇目。外篇十卷,共十三章。全書正文八萬三千多字,原注九千多字,總計九萬余字。
概括地說,“內篇”主要講歷史編纂學,是《史通》的主要內容、主要貢獻。各篇之間聯系緊密,內部形成了一個有機的系統。“外篇”主要講史官和史書的沿革,雜評過去史書的優劣得失。各篇之間沒有關聯,沒有系統,很像雜論。
具體而言,《史通》的基本內容大體可分為五個方面:一是厘清史學發展的歷史。其中《六家》《二體》,從史書的內容和形式上闡述了史學的起源;《史官設置》《古今正史》,勾勒出史學發展的大勢;《雜述》概括史學的多途發展。二是討論史書表現形式的基本理論,其中以紀傳體史書的結構、體例為主,包括《載言》《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等。三是關于史書編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論,包括《采撰》《載文》《補注》《敘事》等。四是關于歷史認識和撰述原則的理論,包括《品藻》《直書》《曲筆》《鑒識》《人物》等。五是闡述作者經歷、撰述旨趣和史學的社會功用,包括《辨職》《自敘》《忤時》三章。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內篇的第一章《六家》,是劉知幾對隋唐以前史書體裁體例的全面總結,也是全書開宗明義的總綱。劉知幾認為,古代史學是發展變化的,史書的體裁和體例也在不斷演進。他把古代史籍分為記言體(《尚書》家)、記事體(《春秋》家)、編年體(《左傳》家)、國別體(《國語》家)、通代紀傳體(《史記》家)、斷代紀傳體(《漢書》家)六家,并一一考鏡源流、發展、宗旨、利弊得失。并指出,這六家已經窮盡了古往今來的史籍。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只剩下兩家了,于是專門立《二體》章詳加討論。《二體》比較了編年體和紀傳體的優劣,其后又以多章文字著重對“二體”中的紀傳體體例和結構做了深入細致的剖析。而“六家”“二體”經過發展演變,大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出現了“十流”。因此,劉知幾又設《雜述》章來詳細論述“十流”,將其視為“史氏流別”,歸入“雜史”。
由“六家”到“二體”,再到“十流”,集中反映了劉知幾的“通識”觀念和“通變”意識,反映了《史通》內篇的結構嚴謹、秩序井然、體系完整,構成了《史通》在宏觀方面的史書體裁的理論體系,是我們研讀這部書的一條主線。
從總體上看,《史通》第一次對中國古代史學作了比較全面而詳盡的理論總結,不僅評論初唐以前歷史著作的優劣得失,對史官建置、史書源流、史學性質、史書體裁、史學功能、修史態度、歷史文學等各方面作出了評論和總結,而且提出了史家的任務和史學的發展方向,特別強調史家的素養。《史通》這部書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國史學理論發展的最高峰。
講到這里,讀者或許會有一個疑問,“史通”二字如何解釋呢?作者劉知幾在《史通·原序》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當年漢代眾多儒生,集中在一起討論經傳的異同,定稿于白虎觀,所以書名就叫《白虎通》。我既然在史館完成此書,所以就以《史通》為書名了。而且,漢代尋求司馬遷的后代,封為史通子,由此可知史之稱通,由來已久。我廣采眾人的意見,定下了這個書名。
《文心雕龍》對《史通》的影響
《史通》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史學理論著作,這讓我們不由得想起我國第一部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劉勰的《文心雕龍》。其實,劉知幾早就注意到了這部書,而且進行了借鑒。
劉知幾在《自敘》中說,偉大作品的產生均為了救世之積弊,而從揚雄、王充、應劭、劉劭到劉勰,他們擔當起社會批評家的職責,以富于理性的精神撰寫子書,無不具有理性主義精神。劉知幾表示,自己與這些先輩一脈相承,秉承了他們的思維方式。
劉勰認為,文章的源頭固然是經書,然而,由于距離圣人的時代已經很久遠了,文章的內容逐漸敗壞,作者們追求新奇、浮夸、怪異的文辭,這離文章的主旨已非常遙遠,幾乎達到訛濫的程度。在這種背景下,劉勰要對文學發展的歷史進行一番梳理,對文學現狀進行批判,其目的是要“標心于萬古之上,送懷于千載之下”。而劉知幾的《史通》也有類似的表述:“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也就是說,劉知幾對歷代史書體例以及史家的史學實踐及觀念不太滿意,于是發憤著述,意圖重新探究史學發展源流、社會功用、撰述目的等諸多現實問題與理論問題。
在結構體例方面,《史通》對《文心雕龍》也有所借鑒。學者一般將《文心雕龍》的體例結構分為總論、文體論、創作論及文學評論四部分。分析《史通》的體例,也包含與此相似的四個部分,如《六家》《二體》《古今正史》及《史官建置》,近乎史學總論,近乎劉勰“文之樞紐”;內篇中的《載言》到《稱謂》十二章分別論述史書各種體裁的起源及得失,近乎劉勰之文體論;內篇中的《采撰》到《煩省》十九章,主要論述史學家的修養和作史方法,近乎劉勰之創作論;外篇中從《疑古》到《暗惑》十章就經史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大膽的批判,從而揭示了史學批評的方法及標準,近乎劉勰之文學評論;而最后的《自序》則是子書寫作的一般體例,也與劉勰的《序志》篇相對應。
當代著名學者傅振倫先生在《劉知畿年譜》中對《史通》借鑒《文心雕龍》的學術思想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他說,《文心雕龍》為文史類之書,然《史傳》一篇則論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態度,實為史評之先河。《史通》一書更就《文心雕龍·史傳》篇意推廣而成,其全書亦就“《史傳》篇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諸義,而詳加發揮。《史通》各篇,亦多仿《文心》,一論文學,一論史學,并具卓識。《文心雕龍·史傳》以“宗經矩圣”作為史學的指導原則,以經書和圣人作為評價的標準,對史學“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的社會功能進行認識,主張秉筆直書,提倡信史等。這些觀點均為《史通》所吸收借鑒。
《史通》的現代價值
《史通》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歷史學方面,其中包含著以史為鑒的思想。
首先,書中提出要“博采善擇”,這是劉知幾關于歷史撰述方法的理論。他認為,撰寫歷史著作必須“博采”,做到“征求異說,采摭群言”,這樣才能成“一家之言”,流傳千古。《左傳》之所以能夠廣包各國史事,記載詳細,是因為當時有各國歷史資料供左丘明廣泛搜集和采用。《史記》《漢書》之所以“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成為千古名著,是因為“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以后,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這都是博采史料的緣故。
然而,僅僅“博采”是不行的,還必須“善擇”。“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對于“博采”得來的資料,必須“別加研核”,“練其得失,明其真偽”,擇善而從。如果不認真鑒別、辨明,不擇善而從,許多訛言、傳聞、鬼怪、虛美之辭就會被當作實錄而寫進史書中,導致“是非無定”。今天看來,“慎擇”“善擇”確實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強調對材料和觀點要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就是來源于此。首先必須“博采”,其次要“擇善而從”,二者缺一不可。博采是基礎,無博采便無善擇;善擇是關鍵,無善擇,博采就失去了方向。
其次是“直書與曲筆”,這是劉知畿關于史書撰述原則的理論。劉知幾“貴直賤曲”,專立《直書》《曲筆》二章詳加論述。強調“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明確指出“善惡必書”才稱得上是實錄,而只有“實錄直書”才稱得上是良史。在劉知殘看來,史書要發揮借鑒、垂訓的作用,那么,直書不隱就不可或缺。他還要求史家要擺脫個人主觀情感的干擾,客觀真實地記載歷史,不虛美、不隱惡,他痛斥史家曲從權貴而修史,這在當時是很有勇氣和批判精神的。他一再提醒史書的功用是“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劉知畿“貴直賤曲”“實錄直書”的精神和理論,對中國史學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受到后世學者的普遍重視。
第三,書中論述了“史家三長——才、學、識”,這是劉知幾關于史家修養的理論。《史通》里沒有明確提出“史家三長”的話語,但“史家三長”的思想貫穿了《史通》全書,是劉知幾史學理論的靈魂和精華。所謂“才”,是組織史料和表達的能力,包括對文獻的駕馭能力,對史書體裁、體例運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能力等;“學”是指讀書搜集史料的學問,以及淵博的學識;“識”是見解,即對史事的鑒別、判斷、評價能力。劉知幾認為,作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才、學、識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個史學家掌握了豐富的歷史知識、具有很大的學問(有“學”),但卻缺乏運用這些知識來研究歷史的能力(缺“才”),是不可能撰寫出有價值的歷史著作的,就像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筐,卻交給一個愚笨的人去經營管理,那是不可能生財的。同樣,一個史學家有淵博的學問(有“學”),又具有很強的能力(有“才”),但如果缺乏“正直、善惡必書”的治史精神(無“識”),也不可能寫出真實可信的歷史著作。劉知幾的這一理論影響深遠,清代章學誠在“三長”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史德”,使這一理論更趨完善,成為“史家四長”。
最后,書中提出“生人之急務,國家之要道”,這是劉知幾關于史學功用的認識。他在《直書》《辨職》《自敘》《史官建置》等章中都講到了史學功用的問題。比如,《直書》中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劉知幾認為,如果沒有史書,又缺乏史官,那么像堯、舜這樣的圣人,像夏桀、商紂這樣的暴君,在他們死了以后,就會善惡難分、美丑難辨了。反之,因為有了史官和史書,古人雖早已離去,但其事猶在。人們坐在家中翻閱史書,就可以窮覽千載,進而產生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的啟迪和教育作用。所以,劉知幾感嘆道:“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這就是以史為鑒的思想,也是今人讀史、談史、論史的主要目的。
總之,劉知幾的《史通》構建了一套較完整的史學理論體系,劉知幾本人則是一位史學批評大師。他在史書內容、撰述方法、體裁體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則、史學功能、史家修養、史學批評的范疇和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見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