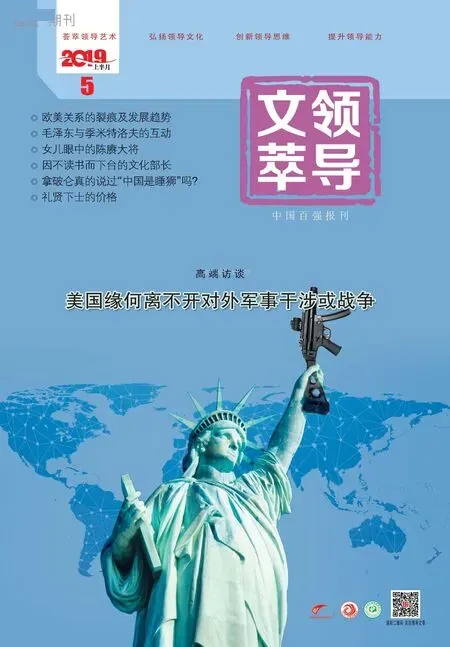如何看中東地區的“美退俄進”
牛新春

2019年10月普京旋風式訪問沙特、阿聯酋兩個中東國家,受到帝王般的款待,16匹漂亮的阿伯拉寶馬護衛著總統車隊,真是風光無限。而與此同時,美國軍隊倉皇撤出敘利亞北部,俄羅斯軍隊迅速補位,特朗普因此被國內反對者批得灰頭土臉。在中東,美國的“戰略收縮”和俄羅斯的“戰略躍進”是客觀事實,但在可預見的將來,俄在中東的存在和影響都是有限、局部和戰術性的,美國的影響仍將是最強、全面和戰略性的,遠沒有達到“易位”的程度。
美國的中東戰略在“收縮”什么
冷戰結束后,失去了蘇聯制衡的美國一家獨大,再也不用擔心自己因干預中東事務而被卷入超級大國之間的戰爭了。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前,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投了贊成票,給美國軍事打擊伊拉克開了綠燈。“9·11”事件后,美國的中東戰略進入新的擴張期,2003年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派出16.5萬名戰斗人員,總共使用了505個軍事基地。同時,冷戰結束后,美國的意識形態自信極度膨脹,想利用“單極時刻”把西方價值和制度推向全球。美國通過各種手段教導、壓迫相關國家接受“華盛頓共識”,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2004年小布什政府推出“大中東民主計劃”,全面介入中東國家內部事務,試圖對中東進行全方位民主改造。
2011年美國從伊拉克全面撤軍,象征著“大規模直接干預”戰略的結束。此后,受國內金融危機、伊拉克戰爭困境、能源獨立、“大中東民主計劃”失敗等影響,美國的中東戰略開始收縮。這輪戰略收縮是對前20年大規模直接干預的回調,一定程度上是回到“離岸平衡”的“常態”。不再直接參與大規模地面作戰、不再大規模推動“民主改造”,是美國戰略收縮的兩大顯著特征。由于軍事干預和“民主改造”撞了南墻,特朗普曾猛烈抨擊過去幾屆美國政府的中東政策,稱美國在中東花了7萬億美元,死了數千人,卻什么也沒得著。2006年以來,美國熱情支持的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伊拉克、也門等國的民主選舉,直接導致后來“阿拉伯之春”的發生,但除突尼斯外幾乎全部是災難性的結果。在血的教訓面前,美國在中東大規模推動“民主化”的時代也結束了。
美國的中東戰略有哪些內容沒有變
除上述兩點變化外,美國中東戰略的大部分內容沒有實質性變化。首先,在中東的利益沒有太大變化。保證能源供應、保護盟國安全、打擊恐怖主義、遏制敵對國家崛起仍是主要利益,中東對美國依然重要。美國是否還需要中東石油,是當前關于美國中東戰略的討論的核心爭議點。
然而,中東每天仍生產石油3000多萬桶,占全球日產量的30%以上,石油凈出口占全球交易的40%以上,至少未來數十年內還將繼續是世界最主要的能源供應地。美國雖不再高度依賴中東石油供應,但畢竟還是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費國。石油價格是全球聯動的,如果中東動蕩、國際油價上漲,所有消費國都會受影響,更何況美國的盟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仍然很高。有美國學者指出,美國介入中東事務的根本原因是要履行自己作為全球領導者的責任,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果美國不打算放棄自己的全球領導地位,就必須為中東石油的穩定供應承擔責任,也必須繼續介入中東事務。
其次,美國仍是參與中東事務最頻繁、最廣泛、最有影響的外部力量,只不過干預的方式有所變化。軍事上,美國綜合使用空中打擊、軍事威懾、軍售軍援、結盟互助等手段,頻繁介入中東熱點問題。美國在中東的存在和投入也沒有明顯變化。軍事上,常年維持著6萬~8萬駐軍,保證兩個航空母艦戰斗群在中東附近游弋,2019年下半年向中東增兵14000人,國防部正在討論繼續增兵14000人。巴林、埃及、以色列、約旦、科威特、摩洛哥、突尼斯等7個中東北非國家是美國的“非北約重要盟國”,而這個級別上的美國盟國在全球只有17個。經濟上,美國是中東最大的直接投資來源國,2018年直接投資存量達730億美元,美國與中東的年貿易額達2000億美元以上,中東還是接受美國對外援助最多的地區。
可見,戰略收縮主要是心理和感覺上的,還沒有充分體現到實物層面。對很多中東國家來講,美國的存在是地區安全格局中最重要的支柱,美國稍有風吹草動,中東就有狂風暴雨。美國的盟友和敵人都明白,美國不會再為中東國家打一場大規模地面戰爭了,僅此一點就能在中東激起巨大變化。
俄羅斯“躍進”到哪兒了
2015年俄羅斯出兵敘利亞是其在中東“戰略躍進”的標志性事件。冷戰時期,美蘇曾經在中東平分秋色,蘇聯影響力曾一度超過美國。冷戰結束后,俄逐漸淡出中東,喪失了戰略大國地位。2015年俄出兵敘利亞,改變了戰場格局,保住了阿薩德政權,使自己成為敘利亞局勢的最大玩家,甚至贏家。以敘利亞為支點,俄羅斯調動了自己同伊朗、敘利亞、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等中東大國的關系,再度回到中東戰略舞臺的中心。
其實,俄羅斯在中東的戰略目標非常有限,但迄今為止運作態勢良好。“伊斯蘭國”被鏟除立足地之后,俄羅斯把伊斯蘭極端勢力擋在了國門之外。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復活后,俄保住了在中東的唯一軍事基地(塔爾圖斯軍港)。同中東主要國家建立良好合作關系后,俄羅斯部分突破了美國的經濟圍堵。高調介入中東危機后,俄至少在形象上恢復了自己的大國地位。俄羅斯還同土耳其、沙特、埃及等國家簽署了一系列經濟、軍售合同,獲取到經濟利益。中東市場占俄羅斯對外軍售的20%,俄在敘利亞戰爭展示實力后,其在中東的軍售額可能會增長數十億美元,土耳其已經購買俄羅斯S-400導彈,伊朗、沙特也都有興趣。對俄來說唯一的遺憾是,其本想通過敘利亞問題調動同歐洲、美國關系,但這一目標迄今沒能實現。
事實上,制約俄羅斯雄心的并非美國,而是俄羅斯自己的實力,更是中東問題的深不可測。俄羅斯2018年的名義GDP只有1.5萬億美元,排在世界第12位,這樣的經濟規模對全球性戰略的支撐力是不夠的。在敘利亞問題上,盡管俄羅斯風頭很勁,但敘利亞國內目前仍然存在阿薩德政府、反對派、庫爾德人三派武裝,伊朗、土耳其、以色列都深度卷入,解決這些問題遠比參與戰爭困難,恐怕也不是俄羅斯能單獨挑得起來的。
俄羅斯重返中東是真實、客觀的趨勢,但目標非常克制、有限,行動也比較謹慎。俄羅斯在中東跟誰都交朋友,每件事都不缺席,但跟誰都不死綁在一起,也從不大包大攬,而是游走于各方之間。2019年7月俄羅斯正式提出自己的“海灣和平倡議”,但未能在國際上引起太大反響。俄羅斯一位專家坦率地說,俄在中東是一支“被高估了的股票”。
美俄可有交集?
俄羅斯樂意在中東給美國找點麻煩,手里拿點同美國交易的籌碼,但是沒打算同美國展開全面的“你走我留”式的戰略競爭,更不想打“中東小冷戰”。美國搞戰略收縮,俄羅斯目標有限,因此中東并沒有出現所謂的“美俄戰略大博弈”。相反,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爭四年來,俄美兩國軍隊之間沒發生過一起擦槍走火事件,說明雙方有著非常順暢的溝通協調和風險管控機制。總的看,美俄似乎都對中東不是特別熱心,想象中的“大博弈”沒有出場,根本原因在于中東問題的性質變了。
同時,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美俄要“離開中東”,這是因為中東大國關系的性質也變了。大國在中東的競爭從利益平衡、權力制衡向“威脅平衡”轉變。冷戰前,歐美俄紛紛進入中東,爭奪商業、能源利益,塑造對自己有益的利益格局。冷戰期間,中東是美蘇爭霸的焦點,安全利益、意識形態利益成為競爭目標。現在,中東能夠提供的利益、權力不多,但主要大國也都不敢一走了之,因為中東可以“提供威脅”,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在場,別人就會利用你留下的“真空”制造出對你的威脅,就像一位美國學者指出的,“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你就會在菜單上”。
(摘自《世界知識》)